核心提示:刁亦男,1968年12月6日生于西安,因为父亲在西影厂工作,小时候看内参片《黄土地》开始喜欢电影;喜欢文艺小说和数学不好从而考了中戏;曾认为戏剧是最爱的情人,可是跟孟京辉合作的《阿Q同志》被禁演受打击;由于电影的隐蔽或者自由,2000年进入新世纪给自己许愿做导演;后来用了12年的时间拍了自编自导的三部电影,自称“第六代”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谈创作他说自己并不像外界猜想的那样迷恋人物“身份”,《制服》和《夜车》都是想要表达一个人内心的疯狂和隐秘被点燃,而《白日焰火》更像一场合谋;感慨获得柏林金熊奖只是一个小插曲,作为一个导演生涯的成功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但是最重要和最迷人的是“等待戈多”的过程。

《 白日焰火》海报
文︱凤凰网文化 吕美静
小时候在西影厂看内参片《黄土地》开始喜欢电影
凤凰网文化:我看网上写的很乱,你是生于1968年还是1969年呢?
刁亦男:1968年12月6号生人。生于西安。
凤凰网文化:你父亲在西影厂做文学工作?
刁亦男:我的父亲是西影厂文学部的编辑,给他们做文字编辑。
凤凰网文化:最早就是在西影厂接触的电影吗?
刁亦男:上高中的时候,正好那个时期也是中国电影复兴的一段时期,我记得那时候吴天明刚刚到西影厂当厂长,吸纳了一批特别年轻的有才华的导演,包括陈凯歌,张艺谋,黄建新,何平,颜学恕,我常常能在西影厂里碰到这些人,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进口电影,不公映的,但是每周会传来传去,在全国的制片厂循映。
凤凰网文化: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经历?
刁亦男: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去看,那天还下着雪,去了门口不让我进,说这个电影有儿童不宜的镜头,我父亲就说你在门口等一等,我就只能等了,就一直在雪地里自己玩,等了整个一部电影,中间也趴在门缝去偷看了一点,细节也没什么东西,但是那次对我印象蛮深的,就是他们拒绝我看电影,是因为一些儿童不宜的镜头。
还有一次是高中的时候,也是看过路片,开演之前突然说,吴天明厂长要讲几句话,然后突然间就见到吴厂长大步流星走到舞台上,站在荧幕前开始讲话,讲着讲着就开始骂了,骂西影厂的一些人在外面招摇撞骗,打着西影厂的旗号去骗企业的钱什么的,说这些人是猪,骂得很难听,我那一次对吴天明印象特别深,全场大家要看电影,他上去开了这么一个映前发布会一样的东西。
凤凰网文化: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电影?
刁亦男: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黄土地》,晚上十点钟的时候突然说要放映《黄土地》,一个小小的黑白的黄河电视,就看得特别激动眼睛一眨不眨地把片子看完了,觉得里面的画面特别有特点,有冲击力,说不上来的一种力量。第二天我父亲就把登在场刊上的电影剧本拿过来给我看,编剧的名字叫张子良,我记得是陕北人,剧本的名字叫《深谷回声》,完全不是“黄土地”那么生猛,那么简洁有力的名字。
我当时就把场刊上的剧本看了一下,觉得电影和剧本不一样。剧本是一个特别有故事情节的,讲一个爱情故事的电影,八路军和当地的老百姓叫翠翠,产生了爱情如何如何,但是电影给我的感觉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电影可以和剧本拍得不一样。这是让我喜欢上电影的一部电影。
与孟京辉合作的戏剧《阿Q同志》被禁演受打击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后来考了中戏的戏文系?
刁亦男:考中戏的戏文系是喜欢看文艺的小说。另外考艺术院校,因为数学也不好。
凤凰网文化:其实是因为数学不好所以考中戏?
刁亦男:差不多,你可以这样理解。文科生嘛。
凤凰网文化:1989年12月,你和张杨、孟京辉、蔡尚君、施润玖等等中戏同学企图在学校煤堆表演《等待戈多》,未遂。然后自己开了个会,张杨说,排是牛逼,也是傻逼;不排是傻逼,也是牛逼。
刁亦男:有这个事。
凤凰网文化:我采访孟京辉的时候跟他说,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时开会的人,除了他还在做戏剧,其他的人都在拍电影。
刁亦男:大家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各自表达。
凤凰网文化:你是因为想要表达才拍电影,还是因为热爱电影,想成为电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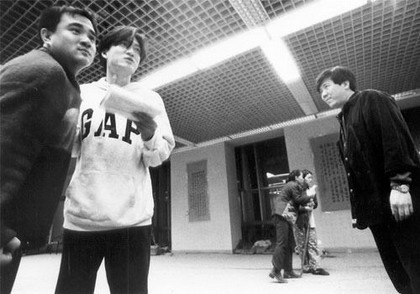
1996年《阿Q同志》工作照
刁亦男:我也特别喜欢戏剧,我给孟京辉写《阿Q同志》的时候,我们觉得戏剧绝对是情人,是必须最爱的一个永远的情人,但是当时《阿Q同志》被禁演了。这件事也挺打击我的,大家辛辛苦苦排练了一个月,我写剧本也花了一个月,到最后说不能演,一点办法,一点招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想,如果是一个电影的话,怎么着也能存留下来,哪怕是一个DVD,它有一个传播的形式,话剧就是要靠活人,一个班子来演,不让你演,你就没法传播,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戏剧在这方面稍显弱了,不像电影那么隐蔽或者自由。
凤凰网文化:戏剧和电影有一个共同点,大家在黑暗的场所共同观看。
刁亦男:都是在黑暗当中被大家观看的,集体窥视一个行为,集体做梦的一个行为。
电影是很神圣的理想 每一次都当成最后一次
凤凰网文化:其实我想问你,《白日焰火》获得柏林金熊奖,票房也不错,如果1989年那时是等待的话,你觉得你现在等到戈多了吗?
刁亦男:我觉得这就是等待过程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我觉得戈多不是那么容易来的,戈多是更重要的,更需要耐心去等的,也许戈多一辈子都等不来,但是我觉得等本身挺好的,等来等不来都不重要,等的过程发生各种小插曲,就足以了,就挺好的。
凤凰网文化:有电影追求的终极目标吗?
刁亦男:没有,就是一部一部地拍,如果有机会的话,每一次都认真对待,每一次都当成最后一次拍电影。
凤凰网文化:你把电影当做很神圣的东西?
刁亦男:是的,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生活手段,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很神圣的理想,我们拍摄的整个工作状态也都是很理想主义的状态,所有的主创人员都像在一个乌托邦里面生活了一段时间。
2000年进入新世纪给自己许愿做导演
凤凰网文化: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做第一个自己导演的剧本?
刁亦男:2000年,进入新世纪,我给自己许的愿就是自己做导演,自己写剧本,花了两年时间,拍了自己第一个处女作,叫《制服》,是在2002年夏天拍摄的。之后就进入了自己做导演的步调里面,用了12年时间,到了2014年拍完了《白日焰火》,这12年我一共拍了三部电影,都是自己编剧的。
凤凰网文化:我想插一句,2002年你主演了余力为的电影《明日天涯》,做演员的感受怎么样?
刁亦男:挺有意思的一种经历,因为那个剧本故事情节比较松散,前后也没有一定的逻辑,戏剧性也不是很强,所以演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具体在做什么,心理的动机,依托是什么,完全是听导演要我完成什么动作,就去完成什么,让你笑,让你难受,让你没有表情,都是一些简单的指令。挺愉快的一次经历,非常有趣,非常新鲜,觉得做演员真的也挺幸福的。在镜头前,灯光下,所有剧组的工作人员都围绕着电影最终的呈现者,那种享受也是无与伦比的。
《制服》是初恋讲一个人内心的疯狂被点燃
凤凰网文化:《制服》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刁亦男:像初恋一样,自己特别喜爱的一个追求目标,曾经向它投入满腔热情,把它拍摄出来,有痛,有温暖,也有青涩,但是很美,很美好,无论多少痛,无论多少青涩和初出茅庐的苦恼,但是我觉得都是美好的记忆,那就像初恋的感觉一样。
也是在一种自由状态下进行的创作,没有过多的干预,也没有特别商业性的束缚,之前的两部电影都是完整地表达了自我,这也是独立电影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自由的表达,自由的抒发,独立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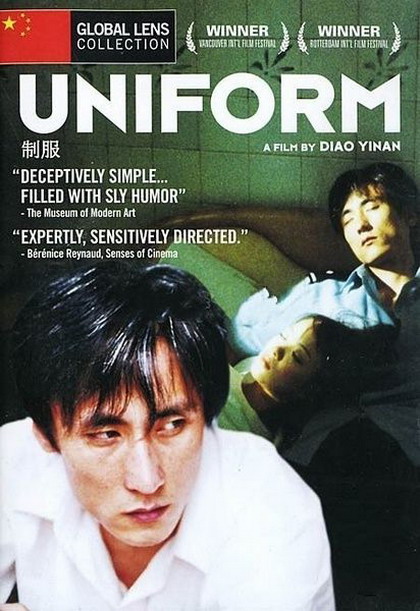
《制服》
凤凰网文化:你怎么总结《制服》?
刁亦男:《制服》写了一个小裁缝,偷渡了自己的人生一样,诈骗生活,欺骗一个女孩儿,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他是裁缝,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交警。当然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权利在中国社会里的重要性,一个人的身份在中国社会生活里的重要性。但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疯狂被点燃了,因为下了一场雨,换了那件警察的衣服,所以他就开始进入了一段冒险的旅程,过双重的生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曾经暗藏在心中的一些冲动,只是没有点燃的契机,而他被点燃了,这是这部电影最重要表达的东西。当然也有很多的社会性因素在里面,但是我觉得那个是辅助的,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人生在那一个夏天曾经特别明亮和美好过。
凤凰网文化:但是那个被欺骗的女孩儿也有另一种身份,同时也欺骗了他。
刁亦男:对,有意思就在于他们两个人同时面对这种问题,所以感觉上比较对称,他们都有各自的苦恼,都在生活当中扮演着貌似平庸的角色,但是在他们心里可能都有各自的秘密。
凤凰网文化: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观众可能会猜,万一他暴露了就会怎么样,结果两个人知道对方的秘密之后并没有怎么样。
刁亦男:对,他们也不揭穿对方,就这样子过平静的下午,甚至去卡拉OK唱歌,生活就是这样的,很多秘密我们不一定要揭开,很多话不能直说。
《夜车》是恐惧和希望、欲望和暴力的并存
凤凰网文化:《夜车》讲的像是一个人的欲望,或者是他的暴力被点燃。
刁亦男:你说的很对。她偷偷地坐着火车去旁边小城的婚姻介绍所去寻找情和爱,排解自己的焦虑和欲望,其实这也是一个隐秘的行动,不是跟几个好闺蜜做一个正常的婚姻介绍,她去那样的小城,去潜入到生活的另外一个层面里,所以蛮像《制服》里的小裁缝,穿上警服,进入生活另外一个层面。所以她的内心隐秘也是被点燃,最终去面对恐惧和希望,尤其是在恐惧和希望并存的那一刻,她的那种状态,可能给观影的人都会带来启发或者触动。
凤凰网文化:影片后面三分之一,女法警和被她执行死刑的女犯的丈夫相遇交手之后,节奏似乎加快了,它的暴力更强,还是欲望更强?
刁亦男:应该差不多,我觉得一半一半,欲望更多。我觉得欲望和暴力,像咖啡和香烟一样,是分不开的。没有欲望的暴力,那个暴力没有什么意思,很干,暴力也不会形成所谓的美学,暴力之美;同样,如果欲望,情欲离开了暴力,好象情欲也不是那么让人痛和刻骨铭心,往往就是这样子。

《夜车》
凤凰网文化:所以她一定要坐着夜车去很远的地方相亲?
刁亦男:不是很远的地方,比如说从咱们这儿坐一个短途火车到密云,或者南口,不是很远,不能解读成很远。但是一定要离开这个空间去另外一站,那个心里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身份”兴趣不大 迷恋人内心潜藏的危险种子
凤凰网文化:你曾说《白日焰火》最开始的灵感来自霍桑的小说《威克菲尔德》,这个小说的最后一段是这样:“一个人只要离开自己的位置一步,哪怕一刹那,都会面临永远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就像这位威克菲尔德,他可能被,事实上也的确被这个世界所抛弃。”它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刁亦男:就像佛教里面老讲的念头,一旦动了念,这个念头呈现出来,真的一步一步的,甚至会改变你的人生。威克菲尔德他不经意地说离家出差,想做一个恶作剧,和妻子开这么一个玩笑,结果一去就是二十年,中间还偷窥自己妻子,两个人在地铁上见面了,都不认识,这种游戏太疯狂了。我觉得人往往在内心都潜藏着这种危险的种子,这是人性当中必不可少的因子,他挖掘得太深了,而且是用极其简单的方法,就把人性内心最隐秘的疯狂阐释出来,这个故事本身就特别吸引我,所以我当时想把它变成一个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爱情故事。
凤凰网文化:这个小说里讲离家二十年,我觉得二十年实在太吸引人了,因为它足够长,我看你之前有一个采访也说,《白日焰火》之前也是时隔二十年。
刁亦男:中间有一个版本是二十年,但是演员不太好把控,因为那个跨度从造型上来讲就比较难,弄不好就很假,所以还是五年吧。
凤凰网文化:我看到很多人解读说,你对“身份”很感兴趣,但是听你说却是对疯狂更感兴趣。
刁亦男:我对身份的确兴趣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大,只是作为编剧的技巧,来让它更容易呈现故事。当然我觉得人如果把自己的生命活得更加丰富,不仅仅是在一个空间里面生活,而是可以给自己开掘不同的生命空间。如果说人生就这一次的话,那完全可以让人生或者生活变得更加的多元一点,就像一个电影,可以满足你平时不能实现的梦想,于是这个电影就伴随着你,像你生命中一个小的平行宇宙一样,实际上那也是你的一个梦的空间。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可以经历不同的生活,冒险也好,爱情也好,总之,因为不同的经历,你的生活空间会被打开很多。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是我所排斥和拒绝的,我愿意让自己的生命更开放一些,而不是既定在一个轨迹上。
拍电影本身就是冒险 《白日焰火》是一场合谋
凤凰网文化:你更喜欢当导演,用电影做梦,还是更喜欢亲身冒险?
刁亦男:我觉得当一个好的导演跟去冒险,这个不矛盾,因为拍电影本身就是冒险,写剧本本身也是像赴一个约会一样,每天你不知道剧情发展成为什么样子,都是某种未知,所以都是很有意思的,生活应该是在未知当中的,要把自己特别坦然的交给未知,去体会,领受未知带给你的新鲜,而不要拒斥它,排斥它。当人有了内心生活,并且开始丰富起来的时候,这个人一定会比没有这样的人,更加的赋有生活的质感,更加的有趣和有意思。

《白日焰火》
凤凰网文化:《白日焰火》是想表现冒险吗?
刁亦男:对,他本来是保卫科的干部,为了破这个案,他去欺骗楚楚可怜的女子,假戏真做,自己也不知道是用了真情还是假意,渐渐他们之间产生了某种情愫,两个人都在冒险。可以这么说,爱情本身也是一种冒险,把你自己交给一个人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你就是把生命交给他了,如果你真的对他投入感情的话,一旦他不在了,等于他会把你的另外一半带走,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的人物好像都是在冒险,都是在经历内心的冲动,都是心灵的阴暗面的火种被点燃,呈现出某种光彩来,去进入生活当中平时不为人探知的另外一面。只不过这一次男女主人公好像合谋一起在冒险,两个人就像在打赌一样,之前两部还是其中一个主人公相对被动一些,这次我觉得像是一次合谋一样,更加放开,肆无忌惮,更加主动。双方也都像下了赌注一样,决绝地看着对方,等待对方出牌,最终有胜利者,有失败者,但是从人性、情感、道德上来讲,失败和胜利又做了一次反转,好像女人,这个凶手,反而是真正的胜利者,她能让那个男人做出最后这种疯狂的举动来,也算是对她小小的慰藉吧。
经历痛苦是主流 电影能实现人性的冲动和秘密
凤凰网文化:你说桂纶镁表演得楚楚可怜,但是我觉得在那一段,廖凡跟她说我不会滑冰,桂纶镁说我教你,我觉得她那段特别性感。你有故意想让她性感吗?
刁亦男:没有,你说她特别性感也有可能,因为性感是一个特别复杂和丰富的感受。就像别人说我的《制服》很性感一样,其实《制服》拍得很含蓄,但有些人就会说它很性感。但是《夜车》反而演员有脱的戏什么的,可能并不是性感,可能是残酷。你说的那段可能有性感,决绝的感觉。你能解释一下吗?
凤凰网文化:因为我觉得她从那时候主动开始接受了挑战,没有一直在拒绝。
刁亦男:明白,你说的这个逻辑是对的,至少她那个时候接受了他的挑战,而且很有挑衅意味地回应了他,就是把自己交给了悬崖,他们都在经历一些疯狂的事情。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种疯狂的事情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四平八稳的,把自己包装得很好,包裹得很好,一些疯狂的想法可能是在晚上难以入睡的时候,在心里面像电影一样,演一演而已,所以生活现在相对是很平淡和稳定的。
凤凰网文化:只能看电影。
刁亦男:对,也许有一个什么机会把它点燃,也未尝不是没有可能,我只能说平时大家都是很平静的,但是内心里面可能都有某种冲动和秘密。人性的潜力,人的潜力巨大。
凤凰网文化:我觉得中国人可能受佛家的影响多一点,比较相信缘分,所以就会显得比较被动。
刁亦男:也可能吧。
凤凰网文化:你有宗教信仰吗?
刁亦男:我对这个不敏感,也没有过多地去想过这些事,就比较随意,随性生活和工作。
凤凰网文化:美国有另外一种有意思的问法,他不会直接问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他问你觉得人生经历痛苦是有意义的吗?如果你说是有意义的,就说明你有宗教性。
刁亦男:我认为是有意义的,一定有,至少说这句话会安抚很多经历痛苦的人,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毕竟失败者居多,成功的就是那么几个,大家曾经的理想都会渐渐被磨平,都会被生活的浊流通过,都会变得平庸,但是内心还是会有一些种子在里面存活的,而且大部分人也都经历过痛苦,这都很正常。经历痛苦是主流,而经历痛苦绝对是有意义的。

导演刁亦男在柏林电影节颁奖现场
只想靠作品说话 获奖离我认可的成功还非常遥远
凤凰网文化:你觉得你算成功者吗?
刁亦男:如果是别人给我的评价,我没权去干预别人怎么评价我,如果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给你几公斤重的熊,你的电影得到了标志性的奖励,是对电影的认可。但是作为他一辈子要拍电影的导演来讲,我觉得离我认可的成功还非常遥远。成功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就像你说的戈多永远也不会到来一样,但是最迷人的是,你一直走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这个是特别让人心里坦然的事,你将永远有目标,有理想,那多幸福。所以等待成功或者通往成功的路上去享受获取成功的过程,这个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凤凰网文化:你怎么看待名声?
刁亦男:你现在如果说这个东西对你没有什么帮助,那也是扯,有点太装了,但是这个东西你得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它给你信心,继续往下走;另一方面,很轻易得到一些机会,你对作品的质量可能就不像以前那样要求那么严,会往下掉,因为以前你没有被大家知道的时候,你只有靠剧本和电影去说话,那个是硬碰硬的,现在有了这个的话,有可能受这个影响,所以说我不愿意太多接受采访,还是让自己回到过去那种相对平静的状态重新开始。
凤凰网文化:如果没得这个奖呢?
刁亦男:也没什么影响,去了柏林本身已经很开心了,得了这个奖锦上添花,但是这个奖最重大的一个意义,对宣发帮助太大了,它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如果没得这个奖无法比拟的,的确是这样子的,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市场上被认知,被感兴趣的程度完全不一样。
凤凰网文化:对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刁亦男:那个倒没有影响。
凤凰网文化:你有没有最低谷的时候?
刁亦男:没有太明显的时候,我的低谷一般两三天调整过来了。
《白日焰火》没有受东野圭吾的影响 最喜欢布努埃尔
凤凰网文化:网上有一些人评论《白日焰火》像日本电影,或是劳伦斯·布洛克,你怎么看?
刁亦男:劳伦斯·布洛克我倒是挺喜欢的,我受到他的影响也许有,但是《白夜行》,东野圭吾是完全没有的。你说我受哈米特的影响也有可能有,文学的影响很复杂,但是确实没有东野圭吾,只能说他们没看懂。
凤凰网文化:你个人比较喜欢哪些电影呢?
刁亦男:布努埃尔,这一个就够了,他是我最喜欢的导演。我喜欢布努埃尔,安东尼奥尼,我老说我受黑色电影影响,我要说一个黑色电影,新好莱坞,像科恩兄弟,像默片时代F·W·茂瑙、弗里茨·朗等等。
凤凰网文化:《创世纪》里古天乐演的反派名字也是“张自力”,《花样年华》中,张曼玉扮演的叫“苏丽珍”,与张自力前妻“苏丽娟”一字之差。起名字的时候有过这些联想吗?
刁亦男:张自力我完全没有想过古天乐,张自力是小时候我们院儿的一个人,我就给挪过来了。最早看《阿飞正传》时脑子里有苏丽珍的名字,挺好听的,然后我就改了一个字,因为起名字怎么方便怎么来,这个是有苏丽珍的影子。
“拾荒者丢失的马”只是隐喻生活中隐形的暴力
凤凰网文化:网上有段对电影中拾荒者丢失的马的解读:“马是男性力量的象征,居委会大妈说是拾荒者留下的,而洗衣店老板就是看吴志贞可怜收留她的拾荒者,他丢了他的马即男性的性能力,所以才有后来卡车内的换裙游戏,也是梁志军不杀他的原因。”
刁亦男:太牵强了,过渡的阐释,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个拾荒者的马就是人找不到了,马在那个小区里面转悠,会让人感觉到很不安,会对人的生命产生某种联想,反观我们的生活,其实这都是间接的暴力,或者隐形的暴力。一个人的失踪,你不会想到他去邻家,或者串门,或者回乡下,你想到的是他的生命是不是被剥夺了,这是我们大部分人,至少是我第一本能的联想。这样的联想会让我们去反观我们的生活,到底这里面存在多少暴力。其实暴力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日常当中,而且非常具有突然性,说来就来。这一个案件虽然是碎尸案,但是在调查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生活中的很多细节都会让人不安,或者充满着危险。
这个想法是我之前看我的一个朋友赵亮,他拍了一个纪录片《罪与罚》,里面有一个片警,东北的,老是去小区巡视,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拾荒者的老头不见了,但是他的马车一直在小区里溜达,他就找这个人,找不到。当时我看到这儿就觉得很不安,后来就把它移植到我的电影里了。他那个里面的老头是一个酒鬼,喝多了,躺在一个什么犄角旮旯里睡了三天,所以警察没找到他,但是我就感觉他被人器官移植了也未尝不可,这种危险分分钟都存在,甚至我们那时候在网上还流传着器官移植更可怕的段子,你突然睡醒以后发现自己躺在浴缸里。很可怕的描述,那个太恐怖了,就是说到处都有这种让人揪心的暴力,在日常生活当中充斥着,我就是想表达社会生活的不安一面。
凤凰网文化:最近好像特别多的导演都在拍跟社会新闻有点关系的东西,贾樟柯的《天注定》、赵大勇的《鬼日子》、甚至宁浩的《无人区》。
刁亦男:刺激我的可能不是这种直接的社会新闻,刺激我的还是我内心的感受,或者自己体悟到的感受,把它变成自己创作的动力。社会新闻的刺激,或者因为一个社会新闻而拍一部电影,对我来讲可能比较少,但是我会把它作为我电影里的材料。
凤凰网文化:因为可能最近二十年或者十年,有一个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的现象。
刁亦男:对,就是刺激的频率更多了,像以前传播度不广的时候,可能刺激的频率少,可能很久才会知道发生一个什么事情,重大的或者奇怪的,离奇的新闻,现在更多了。但不是说那时候没有,现在才有,只有频率密集了。密集了可能这种感受反而变得司空见惯,如果这些事情没有,我反而觉得今天怎么没有出什么事,我们是不是还活在世界上,或者我们进入到梦里面也有可能。
觉得马是忧伤的东西 喜欢在作品里对动物做关照
凤凰网文化:《夜车》里也有一匹马,你对马有偏好吗?
刁亦男:有偏好,因为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的一幕是我在托儿所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个马拉了一车砖,这个马被车夫在用鞭子抽打,居然把它的眼泪打出来了,那个马特别的可怜,小时候看到这一幕,就觉得马是一种忧伤的东西,对马施暴的人肯定都是坏人。
凤凰网文化:乔麦写了一个影评,称你说拍这一段是受卡佛的影响。
刁亦男:应该没有,卡佛的小说当然也有一些动物的运用,什么孔雀,马也有吧,但是确实没有联想到卡佛,只能是巧合。但是我喜欢在我的作品里面对动物做一些关照,动物作为一个元素,让你的电影更加有一些神奇的色彩,和说不上来的一种味道,包括床单上的虫子,也算是一个昆虫,一个死尸,虫子的尸体。
电影是让人体验的 好的东西是气味根本抓不住
凤凰网文化:还有一种阐释,说冰刀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象征王学兵的杀手角色没有性能力。
刁亦男:这个里面也很容易让人用通俗的弗洛伊德的理论去图解这些东西,也好吧,至少比看不懂的人强。还有一批小朋友看不懂。
凤凰网文化:布努埃尔的电影就是符号化的运用很多总是让人过度阐释,也许有些人就是想把一部电影完完全全看明白。
刁亦男:不,电影是让人体验的,不是让人去把它说的那么清楚的,其实很多东西是要感受的,它是气味,你要去闻的,它根本抓不住的,好的东西去体验更重要。这些过度阐释完全不精彩,我看到的有意思的一篇影评,叫《东北貂文化的离骚》。
凤凰网文化:我也觉得那个很逗,还把你的名字化进去--“貂亦难”。
刁亦男:那个无所谓,只要他能自圆其说都没有问题,很轻松,很放松,我们都应该轻松放松地看待一些东西,体验更重要。
希望死后埋在松树下 生命可以进行一次转换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把骨灰埋在树下?
刁亦男:是因为骨灰和土壤分解以后,会被树吸收,她看见那棵树好像就能看见他的丈夫,好像他还活着一样,每天都能看见他,如果一定要这么解释的话。我死了以后也想埋在一棵树下,埋在一棵松树下,你的生命可以进行一次转换。
凤凰网文化:能说明桂纶镁对这个人有感情吗?
刁亦男: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原来有一场戏,那个警察小王下车以后走过去,到他跟前问你在干什么,她说这是粱志军的骨灰,小王说这是什么意思,桂纶镁就回答说,我把他埋在树底下,这样好像我每天都能看见他,他还活着一样。她当然要跟警察这么回答,哪怕这是一个谎言。
凤凰网文化:《白日焰火》和《夜车》里都是女主角在一个关键点涂口红。
刁亦男:对,这个是女人化妆一个特别常见的动作,也有一些暗示在里面。
凤凰网文化:张献民老师也写了影评,“人物体态和肢体动作是唯一的,它不是假象,它与内心是一致的,直接表达着拒绝或渴望。这是20世纪前半期舞蹈或一些其他舞台艺术对身体的认识,符合当时电影的通俗论断‘动作即电影’”。是故意这样安排吗?
刁亦男:对,故意的,这种设计我们尽量让演员减少对白,尽量让他们用身体,用肢体,用动作来说话。
凤凰网文化:被流出的一个工作版里,发廊枪战和王学兵冰刀杀警察,两场都只是一个长镜头,为什么后来把镜头剪碎?
刁亦男:就是让它的节奏变快,时间变短,院线也要求电影的时间不要超过一百分钟,这也是为了排片更加方便,为了让观众观影更顺利,把它剪得商业一点,节奏快一点。
最不喜欢拍阳光灿烂 风格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错误
凤凰网文化:冰场滑冰那场戏,摄影师也在滑冰吗?
刁亦男:对,我们是在很矮的雪橇上,机器也在雪橇上,演员也在雪橇上,有的镜头是演员和机器同在雪橇上,他们只是在做动作,所以看起来很梦幻。
凤凰网文化:听说一些夜戏没有打灯?
刁亦男:现在低照度已经非常敏感了,可以到1600,所以基本上夜景不用专门做灯,如果当时自然光的气氛好的话就直接用了,但这种时候不太多,还是多多少少要做一些光。而且现在的后期技术非常强大,DI技术,相对有一些偏差的话都可以纠正回来。
凤凰网文化:包括“白日焰火”那个霓虹灯也是做的。
刁亦男:“白日焰火”的门头,霓红灯,对,那是后期的特效,那个要真花钱做的话就太贵了。摩天轮也是做的,因为冬天摩天轮是不运转的,太冷了,零下三四十度,摩天轮没法运转,所以那个是停下来以后在舱室里拍的,后期做的运动,这些特效都是做得非常好,这个特效公司也是相当厉害的特效公司,我的一个好朋友开的。
凤凰网文化:调色师也是《杀人回忆》的调色师?
刁亦男:当然,韩国所有你能说到的好电影都是他做的,李先生非常厉害。跟他合作非常愉快开心,而且他给我们很多启发,比如说对反差的认识,我们也曾经问过反差是什么。他说反差实际上就是现场给你的感受,你到了这个现场,他会自然的传达出光的信息,给你直接的感受,你把这个东西保留下来,呈现出来就很好了,不要特别刻意,人为的做一些反差,就是尊重现场。
凤凰网文化:你特别喜欢拍夜戏、雨戏、雪戏?
刁亦男:夜戏喜欢拍,雨戏也喜欢拍,雪戏现在有点心有余悸了,太冷了。我唯一不喜欢拍的是阳光灿烂的那种天,连我的摄影都说,这个简直成了你的宿命了,他说你为什么不能拍一拍有阳光,光影很强烈的日景呢,但是我总是回避这些东西。
凤凰网文化:有人说可能你的电影风格已经形成了,你觉得是吗?
刁亦男:也许吧。我也觉得我的电影有自己的一些既定的规律,和一些选择原则,慢慢的在固定化和本能化。我觉得风格实际上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错误,就是跟常规不太一样,特别有自己的自我气息的选择原则。

[视频]导演刁亦男:用电影表达人性最隐秘的疯狂
http://culture.ifeng.com/niandaifang/special/diaoyinan/interview/detail_2014_03/31/35307640_6.shtml
创作者靠想象力吃饭 第六代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凤凰网文化:第六代导演很多都拍了自己的经历,你的片子好像都是想象的故事,有想拍自己或者身边的想法吗?
刁亦男:我觉得如果你是创作者的话,你的记忆肯定对你影响深远,而且我觉得记忆本身就是一场演出,所有经历和记忆肯定都会影响一个创作者的整个作品的质感。在我的电影里面,有我的很多经历和记忆带给我的资源,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创作者最终是靠想象力吃饭的,不能说你仅仅是用经历和身体来创作,那没几次就用光了,走得更远的是要靠想象力,以及通过这种想象力控制题材、故事、文本的能力。
凤凰网文化:你怎么看第六代?
刁亦男:确实没想过怎么看他们,都挺好的,平时大家也都是朋友。确实我们可能身在其中,都不知道怎么去评判,我觉得第六代都是理想主义者,至少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觉得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如果有第七代的话,肯定不会是这样子的。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以后不会有?
刁亦男:我感觉,我也不能说肯定没有,大家像一盘散沙一样,不像一代了。
人性喜欢垃圾 艺术电影被接受程度跟社会文明有关
凤凰网文化:目前国内的艺术电影必须进商业院线跟商业片竞争,你会倡导开艺术院线吗?
刁亦男:作为工业电影的基础越来越丰厚,会慢慢细化出艺术院线的,这个在国外已经有了,但是艺术院线永远是少数,这个也是肯定的,不可能说有一天大家都看艺术电影,而商业片在一个小众小范围的环境,这是不可能的。就跟大家永远爱喝可乐,不会喝矿泉水一样,可乐永远是饮料界的票房冠军,但是可乐是垃圾,可是好东西他就是不爱喝,这跟人性有关,人性就是趋近于简单,刺激,迅速能够刺激感官的东西。可乐也是这样的,口味重,有刺激,但它就是垃圾,人就喜欢垃圾,你说怎么办。
所以艺术电影被接受的程度和被关注的程度的确跟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有关系,现在的水平就是看《爸爸去哪儿》,咱们到电影院看电视。市场上将来不一定这么单一,也可以有《爸爸去哪儿》,也可以有文艺电影,但我们也别奢望《爸爸去哪儿》突然消失了,所以也不用紧张和焦虑,慢慢来,都很正常。
凤凰网文化:《制服》和《夜车》都参加了中国独立影像展,说说独立电影好吗?
刁亦男:对,所有想拍电影的人,可能都要经历成长的这一步。独立电影的经历就像是一个青春日记,用影像把它记录下来一样,我觉得独立电影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会让一代电影人都经历一个拍电影的入门平台,门槛儿也没有那么高,所以你只要去做,都可以实现,而且独立电影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们的制片人文晏拍的电影《水印街》反响非常好,是这几年中国少有的佳作。
凤凰网文化:《白日焰火》之后有什么新计划吗?
刁亦男:目前没有,目前先休息一段时间。
凤凰网文化: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电影是什么?
刁亦男:电影就是你生活当中做不了的事,完成不了的幻想,通过它来实现。比如说你生活当中犯不了罪,你在电影里就可以犯罪,比如说生活当中你爱不了这个女孩儿,你在电影里就可以爱他,比如你生活中是一个懦夫,你在电影里就是一个英雄。电影就是白日梦。
(感谢王宏伟、泥巴。)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