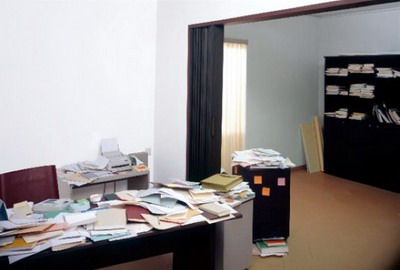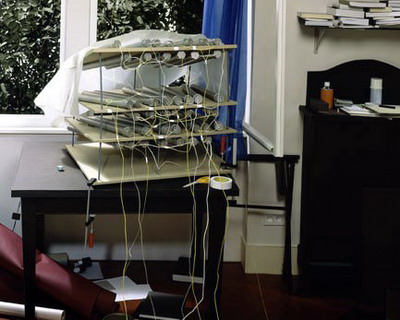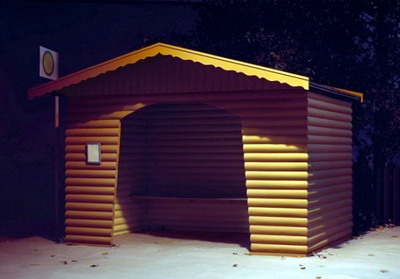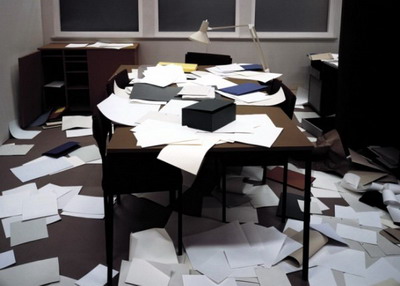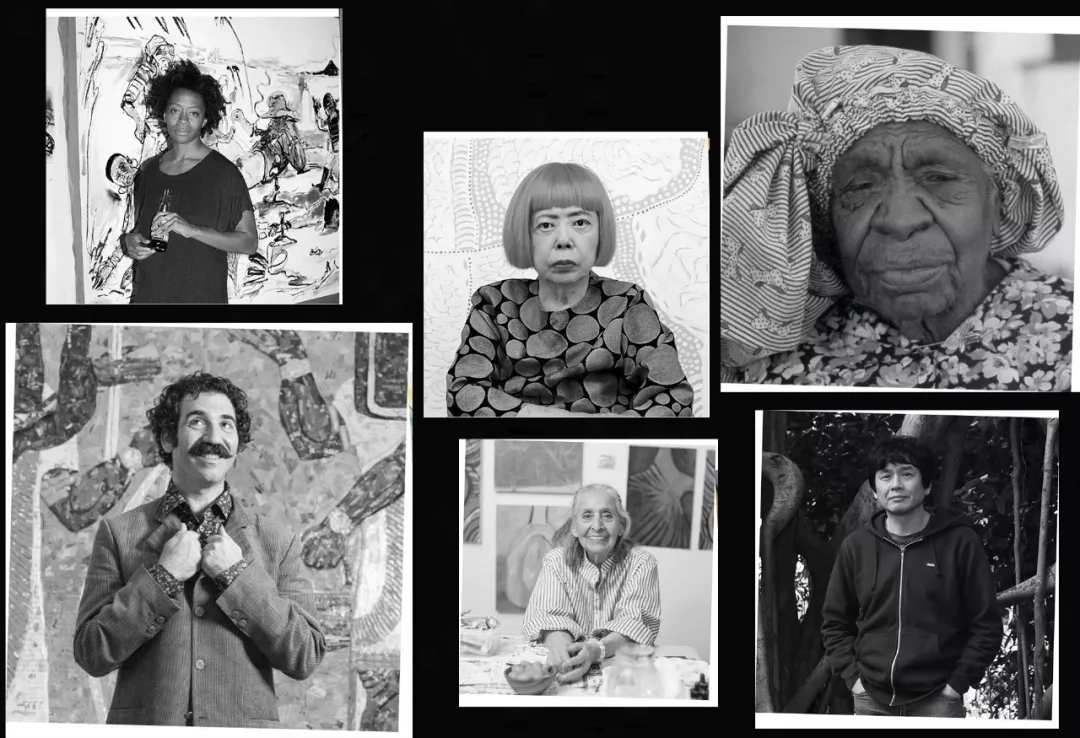文︱段炼
历史由人写,有哲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也说一切历史都是统治者的历史,类似于中文“成者为王败者寇”。
在德国看画,我想到欧洲艺术的历史。言及欧洲的古代艺术,人们通常都讲古希腊罗马,而中世纪艺术则讲意大利和法国,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更是意大利一家独大,之后的三百多年,则是意大利、弗兰德斯、荷兰、法国的天下。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出现,英国艺术崛起,德国是小字辈,直到十九世纪中期现实主义登台,德国艺术才有机会上场。
历史是由人讲述的故事,即便是同一故事,不同的人所讲也不同。英文中的历史一词为history,对应法文histoire,但法文的意思不仅是历史,也是小说,即虚构的故事。实际上,德国绘画在文艺复兴后期因杜勒(Albrecht Durer)而异军突起,到十八世纪末更因浪漫主义而兴盛,成为欧洲艺术史的不同故事。
今春德国行,看遍了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的美术馆,有机会思考德国绘画。在法兰克福的歌德故居,我看到一幅歌德像,他身着白袍,斜坐在断垣残壁的荒野中,一脸思考状,很哲学。这是德国浪漫派画家提希拜茵(Johann H.W. Tischbein)的名画《古罗马废墟上的歌德》,作于1787年。歌德是德国浪漫派的大诗人,与席勒并称“狂飙突进”的先锋,写有诗剧《浮士德》和散文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都是文学名著。德国浪漫派大画家弗雷德里希(Friedrich)专绘荒野中的古罗马废墟,歌德故居就陈列着他的废墟风景,与歌德画像相呼应,其画给人忧伤、神秘、敬畏和崇高感,昭示着哲理之美。
哲学乃智慧,西方主要语言中的“历史”一词,本义为“知识”和“智慧”,在古希腊语中为histor,指有知识和智慧的人,其词源是动词“看”和“了解”。换言之,洞悉真相的人就是哲学家。
到德国看画,不敢说了解,只敢说思考了、长见识了。在法兰克福国立美术馆,我见到一幅《峡谷废墟》的风景,悬崖边矗立着破败的古堡。这是一幅十九世纪前期的绘画,卡尔·莱辛(Carl Lessing)作,与浪漫派那诗意美化的废墟很不同,是自然主义的写实,但悲怆与感伤的情调仍在,哲学味不减。十九世纪中期,自然主义转入新古典。在慕尼黑的国立美术馆旧馆,我看到大画家费尔巴赫(Anselm Feuerbach)描绘希腊神话的巨作《美狄亚》。画中的美狄亚坐在海滩岩石上正与两个孩子永诀,后面沉思的黑衣人如死神般象征着鬼魅与恐怖。远方的背景中有一群船夫将船推入大海,呼应了圣经所言: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英语中“历史”一词的演变很有意思,含义为“探索知识”和“记录探索”,也就是纪实和叙事。叙事性是现实主义绘画的一大特征,而十九世纪后期德国现实主义绘画成就非凡。在法兰克福国立美术馆,我看到了威廉·莱伯尔(Wilhelm Leibl)的名画《不相称的婚姻》,描绘一位老乡绅和乡下少女,实为老夫少妻的肖像。画中老者眼露得意之色,而农家少女则一脸淳朴。有人说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我宁愿说这是写实主义的杰作,因为画家在不经意的嘲讽中,如实再现了乡下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
同一时期的大画家门采尔(Adolph von Menzel)更有现实主义特征。在慕尼黑国立美术馆的老馆,有他为其妹所作的肖像,此画一如写生,平易、亲近、直接,画中依着门框的少女羞涩腼腆,对门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这种写生式绘画很有象征意味,影响到后人。在慕尼黑国立美术馆的新馆,我看到费迪南·何德勒(Ferdinand Holdler)画于1892年的《厌倦了生活》,描绘五个人横排坐在教堂长凳上低头沉思。中间一人象是赎罪者,两边四人皆为教士,但他们看来反倒被罪人教化了,五人都因悟到生活的虚无而满心失落。这幅画既是叙述人生故事,也是探索生命哲学。如此这般将故事融入写生的象征方法,也见于法兰克福国立美术馆理伯曼的《参孙与达丽拉》,作于1902年,借圣经题材来描绘双人体。
的确,历史是由人讲述的故事,德国画家自有一套讲法,所以著名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才把自己的艺术史名著称作《艺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