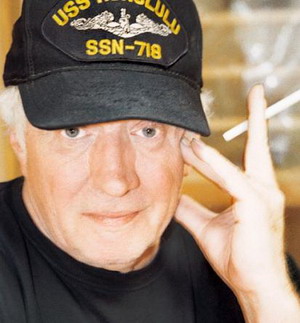
戴夫·希基(Dave Hickey)
引子:看得出来,美国批评家希基对国内读者显然是个新人,他的文章不曾被翻译过。即使我现在愿意来作一点翻译介绍,能被接受多少却是个问题。比如,这里翻译的一篇文章,叫做“摇滚乐的妙处”。 一个美术批评家,却来写“摇滚乐的妙处”,这就奇怪,而希基的这篇文字其实谈的是美术,不过他是运用自己对于摇滚乐的理解和比附来说明艺术中的现象。 这正是希基这位出格的艺术批评家出其不意的地方。而要领会希基的文字,必须能够在不同领域中“跳跃”,而且必须对美国的流行文化非常熟悉才行-希基太能东拉西扯了,从流行音乐说到电影,电视剧,电视剧里的主角,或者主角说的某句台词。即使我长年住美国,在读他的文章时也必须坐在电脑前,不断地上网查询他在文中提到的某个爵士乐手,电视片名,演员名,哲学家名等等等等。虽然他的文字如此地“麻烦”人,可我也愿意被他麻烦,因为他的文字中有真意—真性情和真思考。他能在美国享有盛名,正因为此。美国人可不傻,他们最知道什么是好东西。
希基的介绍上了博客之后,我收到张保琪先生的电邮。保琪是艺术家,我们20多年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是同窗,他现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任教。而希基如今已经被新墨西哥大学从拉斯维加斯大学“挖”走,因此,保琪和希基是同事。保琪的电邮是这么写的:
看了你在艺术国际里介绍Hickey的文章,很好。国内需要这种不同的声音。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在你接着的介绍翻译中可以强调一下:
一,应强调一下当时美国艺术的大背景,这样有利于对他的理解,也可能减少一些国内人的误解。Hickey的书是在观念艺术在美国最巅峰时写的,当时美国的学院派主流是以观念,政治内容为主的艺术。Hickey 是反学院派的(可他最后还是回到学院),他认为艺术最终应是感性的(也许也包括艺术批评),在当时是对艺术潮流的逆叛。现在他的观点似乎很容易被接受,但在当时他是艺术批评界的“坏孩子”。
二,我觉得也许应谈谈现在介绍他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意义。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有着与当时美国当代艺术完全不同的环境和背景,Hickey 的意义在哪里。这可能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回信对他说,第一点应该不难做到,而难的是第二点。我近来好事,总在谈论西方当代艺术批评家,心里就是想让他们对中国贡献点“意义”什么的玩意儿才好。这个工作国内许多优秀的理论工作者们都在做,而且做了很久,叫人敬佩。眼下人人知道,中国艺术批评亟需建构,介绍引进西方的艺术理论是大有必要的。可是我做的出发点却有点不同,我想要做的是解构。明眼人应该看得出,我热衷介绍杜尚,热衷谈论贝尔廷,丹托,因为他们都是在做“解构”的人-杜尚解构了艺术的定义,丹托,贝尔廷解构了现代主义的理论标准。(我也因此最躲着格林伯格,因为这个人最拿手的就是把人的思想围住,框住。)我这么做倒不是个人兴趣什么的,实在是因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当代艺术)的“进化”,最关键的步骤正是“解构”,这个解构不完成,我们就会被卡在那里,一直卡在那里!卡在那里既不好受,也不好玩,是吧?
我看中希基,就是因为他亦善“解构”,解构主流话语的权威。我一直以为,解构理论也是要用新的理论来替换前一种理论的-这显然是我自己思路的局限,而希基却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态度上把这种“解构”完成了。这就是说,希基的艺术主张是个什么倒不重要,我们不见得就得同意他艺术的核心是美之类的说法,同时也不是自己手上拿着个艺术是“不美”的说法。重要的是我们得看看希基看事情,做事情的心态:那么放松,亲切,自在,平等。原来,这种心态是可以被带进做理论的过程里的,这个实在太棒了。这恐怕值得我们中国人来学习,我们是否也可以学会放下我们一直看重的西方艺术理论的主流话语体系呢?这种包袱连美国人自己都不愿意背,我们这群外国人却要背着抱着。这倒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了解西方,了解和抱着是不同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思想上紧抱着一个西方权威,我们就会完全不再去注意自己贴身的感觉,会觉得那些琐细感觉不值得关注,结果,导致了我们的艺术理论是无法贴心的,无法有说服力的,西方人也瞧不上的。(我们古人可没有这个问题哦。)
希基等于是给了一个榜样,这个人从头开始就不理会权威,他完全在个人体验里生长起他对于艺术的看法。那么,我们每个人不是也可以在自己的切身体验里生长起我们自己对艺术的看法吗,我们每个国家不是也可以在自己的土壤和生长环境里生长起我们的艺术理论标准吗。这就是希基给我的启发。我从他那里还看到,说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才不那么容易呢。我以为自己研究了这些年的杜尚,大概可以不那么不堪了罢,希基的出现又吓了自己一跳,分明看到思想上的教条还稳稳地盘踞在那里—要改正自己习气真难。杜尚曾领我走了一段路,希基或许现在也能来领我走一段路,他们教给我做的是同一个功课:放下,放下,再放下。
这里原该照了保琪兄的吩咐,说说中国当代艺术什么的,可是还是说到自己身上了。这可不是自恋什么的,而是,这些年来的经验让我看到:别以为你能改变什么,你什么都改变不了,你唯一能改变的只是你自己。你能先把自己改变了,就很有能耐了,就够你这一辈子忙活了,别的且再说罢。
(刚收到保琪电邮,他说:"补充一点,Hickey 在拉斯维加斯时是在英文系教书,他的东西不但是美术理论批评,而且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理论与批评应该是门让人感受的艺术。")
摇滚乐的妙处 [美] 希基
在1960年代中期,我正在德克萨斯大学读书。周四的晚上是在一个叫Y 的地方有“地下电影”(指小投资的实验电影-译者注)的活动,电影通常是定在晚上7点开始放,但放映员都是些铁杆的革命家,他们不按时放映电影,非得等到那批新左派的阴谋家们散了他们的会之后,过到这边来看电影,他们才肯放呢。就这么着,在花了一下午热烈地讨论如何去损害资产阶级的社会之后,这个电影活动成了这批激进分子们的夜生活。想像一下看,《神秘科学剧院3000》(美国的一部从1988-1999年流行电视剧-译者注)在德州的布景中上演的情形:放映机在闪着幽光的暗夜中咔咔有声,香烟在银色的氛围中旋回缭绕,昆虫唧唧,观众席上喃喃出声的不客气的评论……诸如此类,就像这个样子。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一个晚上我所体验的电影主题的转换,那是开始放映贝克汉格的电影了。(Stan Brakhage 1933-2003 美国电影人,以拍摄非故事性的试验电影而著名-译者注)我记不住电影的名字了,但都是些让人不安的,被认为是电影本体的电影。我能记得的是,其中有很多的撞击,流淌,移动,呼啸-很多很多的爆炸,(电影本体好像是着了火似的),此外还有出人意料的蒙太奇。我前面坐着一位年轻女子,以手腕为轴心,微弱地摇晃着手上的香烟,用最乏味的声音不停地叨念到:天哪,天哪,天哪,天哪。
她说得在理。我能想得出来,这种电影现在已毫无价值,如今该换上极少主义的动作片一类的东西了。回到那个时期,还有同样的那时的神启之物-激越的行动绘画,说到这个,人们肯定就得提波洛克了。反正,这就是那个电影活动后半部分开始放映的东西,而我们却在想,这个贝克汉格真是枯燥得要命!在那种新电影中,摄像机就在一边架着,安排一个家伙在椅子上那么坐着,摄像机从侧面拍摄他,就像惠斯勒母亲肖像的那么个角度,然后是给他理发,就这些。理发师不出现在镜头中,只看得见他的手,剪子,梳子,这些东西在那家伙脑袋上忙活,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他妈的真不敢相信这回事,这太枯燥了。简直是催眠啊,但又不真是能把我们催眠到不叹气,不哭丧,不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的程度。“咔嚓-咔嚓!”我们都盯着银幕,尽管我们知道,五分钟后还是会一样在剪发,可我们还是盯着瞧,“咔嚓-咔嚓!”实在说,这可能还没满5分钟6分钟,可对电影而言,这个时间就够长了,长得可以是西伯利亚的一个冬天。于是我开始捉摸起理论来:剪子的咔嚓声意味着什么,放映机的咔嚓声意味着什么?我寻思,“单纯的声音在真实中和再现中有其相似性吗?那是什么呢?”
然后有事情发生了,坐着让人剪发的家伙把手伸到衣兜里,掏出一盒烟,点了一支!了不起的大动作!鼓掌。这让人足以高兴和大松一口气。可这点高兴应该是挺讽刺的(它实际上就是),而松一口气的感觉却是很真实的。我记得他点烟之时和我忍不住笑起来的时刻,因为这的确是挺逗人发笑的--对于你被人耍了而觉得挺滑稽的那种笑。剪头发还在继续(咔嚓!咔嚓!)而我们却活过来了。15分钟前,我们在贝克汉格的视觉末日中昏昏欲睡,现在我们被这家伙点上一支《幸运击》牌的香烟而欢欣鼓舞。
显然,沃尔霍也进入了这个领域,他做的电影也傻,可是也挺神。他的电影是给一屋子性疯狂的成人革命家们测试最小范围的感受方式。那是恢复到呼吸和触感诸如此类的事情上,然后在瞬间给我们一点冲击,突然之间的--我对此毫不怀疑。我们当然都知道,在一件艺术作品中发生的事情会在最大的或最小的方面跟我们有关,但我们的身体却把这一点忘记了。我们的身体已经只习惯剧烈的动作了。加强非常细微的个人感受,是需要重新塑造的,而《剪发》这电影做的就是这个事。当电影结束,剧场的灯亮起,我们都给换了一双新的眼睛互相瞧着彼此。
“这其中肯定有政治性的作用”, 放映员对我说。我们在结束后,灌下了一瓶啤酒,站在走廊上时他这么说的。对这一点我有怀疑,但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想多看一些沃尔霍的片子。我恐怕一旦批评机制中的辩证啦什么的对《剪发》开放出来,它会让人太清楚地看出,沃尔霍电影是要把历史性和故事性稀释到微不足道的琐屑之中,变得更复杂和更互相关连。对我们而言,那时节没有不带历史的政治,政治就是历史,反过来也一样。然而,实在的,我发现比起贝克汉格片子的政治主题,自己更中意沃尔霍片子的政治主题,他的东西更悲哀些,也更滑稽些。
今天我知道这对贝克汉格并不公平,但在他存在的那个时节,表现主义主张自由的花言巧语到了不得不收场转弯的程度,因为那种所谓自由的主张是不管用的。我觉得我的猜测应该不错:贝克汉格的实践只是个深刻的悲剧,他的电影试图努力达到电影的自由和自治--只在意电影本身,只为了电影具有的材质,实际上却不可能最终把这些电影自身的元素从文化的大图像中抽象出来。艺术家同样如此,所有他觉得是来自他自身特色的偶然即兴,其实他根本不可能把自己做的事情从炮制绘画的历史时段中解放出来。因此,无论你有多欣赏贝克汉格的电动鸟蹦蹦跳跳地显得有多自由,你得承认,最终,它的能量是从电线传递的。
沃尔霍的电影是把这个能量转到脑部来,沃尔霍造不出多少供电的电线,也不会使劲地做一个标准化的简单。(贝克汉格的那种)静态的摄像机,静态的对象,傻啦巴叽的叙述机制,委琐无个性的事情(咔嚓-咔嚓!),只是为了把无聊小事和白费劲使之戏剧化,只是为了直接面对在时间中流过的大量傻气无用的形象。这一来,沃尔霍自我克制的策略(指波普艺术中去除自我表现-译者注)却让一个做艺术家的获得解放,也让观众获得解放—叫观众进入了一个全然喜剧的世界。
贝克汉格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作为冷战时期的孩子就已经知道的事:不管我们费多大劲,我们都是不可能自由的,于是,很自相矛盾地, 我们受邀进入的是一个有权威的严格的乌托邦之内而已。沃尔霍的电影,却是告诉我们该知道:不管费多大劲,我们是不可能被规则化的—由于我们是卑微、不工整、有残缺、难以组织的人,我们倒可能就自由了--在很小程度上,不管我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对于走过了过去三十年的人而言,这大概算得上是一种自我肯定吧。(鉴于这个体会)那些在那炎热的德州的晚上放映的电影对我来说就不能算是灾难性的。
你瞧,我说的我和贝克汉格,和沃尔霍前卫作品的相遇,对我而言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对“高级艺术”的体验。我不知道什么是高级艺术--我知道激进的政治家,爵士乐,摇滚乐和语言学,一旦领会到这个,我渐渐变得在民主的意义上不信任“高级艺术”的说法了。我的意思是,高级艺术该像什么样?贵族文化中有高低之分,他们设定了高档的,低档的,结果,制造出一个经社会操纵,无商业气的高级艺术,这个归类就排挤出来低级的玩艺儿。然而,在商业化的民主中,躲开市场的唯一避难处只有学院。因此,我恐怕,是民主人士就得让自己接受商业化,流行艺术--是它们指示出文化, 接受非商业,学院艺术—是它们批评商业化等等等等,并能够心里明白:即使大多数流行艺术在利用着日常的词汇,一些流行艺术是改进优化它们,即使做出来是为了卖钱的。
为得出结论,我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波洛克的画和贝克汉格的电影算是高级艺术吗?是的?好,设若是的,如果没有像Dizzy Gillespie, Charlie Parker 这样的黑人爵士乐的授权,波洛克的艺术和贝克汉格能存在吗?如果没有美国爵士乐文化的上下文的铺垫,没有形式自由的丰富灿烂的比波普爵士乐(bebop),我能领会这种东西吗?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波洛克和贝克汉格,比波普爵士乐能存在吗?你自己去下结论罢。那么,没有沃尔霍,摇滚乐能存在吗?得!没有摇滚乐沃尔霍能存在吗?肯定不会啦。这些回答当然地使得我坚信了自己的立场—把录制的流行音乐认为是美国这个世纪主导性的艺术形式。我的要点是,波洛克和沃尔霍不是利用散漫的日常词汇,而是让它们优化-把它的本意上升到公众的叙事中去。结果,波洛克和沃尔霍的作品,就像荷兰画家伦布朗,或者英国作家狄更斯,或者法国画家大卫,成为最流行的,就像商业艺术能做到的-起到了它能起的最大作用。
现在我想到德州的夜晚,那标志着爵士乐时代的结束和摇滚乐时代的开始—也是那个悲剧性的放电影的剧场在美国流行文化中的结束和喜剧化玩意儿的开始。这两个时代都使得艺术衰落,但其造成的衰落各有不同。爵士乐假设,如果我们乐队中的四个和和气气的混混们,一起来演奏一个复杂的歌曲,有可能多少达到点儿自由和自主。可悲的是,这很少实现得了。在最好的情形中是,我们中间能有一两人达到这个程度了,而别的家伙们却正被电线连着呢。这并不是说没人打算摆脱牵着的电线,很多人都想呢,也有些人多少做到了,如果是那样,就会让人感到有点不像是爵士乐了。音乐滑开了去进入了恒定的形式层次,超越我们的社会考虑。
而摇滚乐是另一种的,它假设我们四个带有创伤的反社会的家伙有可能是在一块儿玩玩的,好家伙,就演奏个简单的曲子好了,把它玩对了,是吧?就只要能这样一次,把它玩得最好。可是我们做不到。歌曲是太简单了,可是我们却太复杂了,太激动了。我们玩了命的试来试去,可是吉他有些变形,音调又是不准的,节拍只管打着,难以察觉地和我们的期待有抵触,可能只因为我们得呼吸,乖乖!到头来,在试图一起演奏这首非常简单的曲子的过程中,我们制造出声音的狂飙,无限复杂的,一堆闪闪烁烁的精致的碎片。
如果你愿意,如今你可以感谢牛逼的80年代,还有数码定序器,向人证明了技术性“完美”的摇滚-就像“自由”的爵士乐,这种摇滚是讨厌的,因为是程序的讨厌。我的意思是,看看滚石乐队,Keith Richards 总是在节拍之前,而Bill Wyman 总是在节拍之后,因为Keith Richards是引领整个乐队的人,于是Charlie Watts是听着他行事的,而Bill Wyman又是听着Charlie Watts来行事的, 因此他们在节拍上会有这样极其微小的错位,而这是说不出的,但你能在身心上感觉到。吟唱颤动着,和着放大器上手指的震动。这就是摇滚乐的妙处,细微处加进了身体的语汇,带有不可避免的不完美,还有互相牵制的团队。这正是它的好处,因为爵士乐想做的是我们想要自由,同时又得在一起。摇滚乐要的是,我们就是一帮子不怎么样的人。这是你能依赖的东西,而这样其实就对了。20世纪拥有的就只是爵士乐和摇滚乐。其余的只是文牍和广告而已。
档案
王瑞芸,江苏无锡人。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同年入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师事吴甲丰先生,专攻西方艺术史,获硕士学位;1988年进入美国俄亥俄州凯斯西方储备大学,获艺术史硕士学位。旅居美国20年,目前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更多阅读
艺术档案 > 人物档案 > 评论家、策展人 > 戴夫·希基(Dave Hickey)
www/10/2011-09/580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