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下午,“时间开始了—2019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在浙江乌镇北栅丝厂开幕,这届展览继续由冯博一任主策展人,王晓松、刘钢共同策划。
《打边炉》在乌镇对冯博一进行了采访,结合他在展览开幕式上的发言以及画册署名文章,我们摘录出10条展览陈述,形成这则“乌镇十谈”。发布前,经过受访人审校。
1 、做第一届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时,陈向宏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说过,凭什么城里人想看艺术展就看艺术展,想听现代戏就能听现代戏,我们乌镇乡下人为什么不能想看艺术展就看艺术展,想听现代戏就听现代戏。作为策展人,我就是想为乌镇的乡下人做一个好看的、精彩的、有国际水准的当代艺术大展!这个展览就在他们家门口,甚至城里人也要专程到乌镇这个乡下来看这个展览!
乌镇是全球化的缩影,她以旅游闻名,来自四方八方的游客在这里汇集,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能够让大家在旅游之余,休闲之余,接触到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60位艺术家的精彩作品,对于策展人来说,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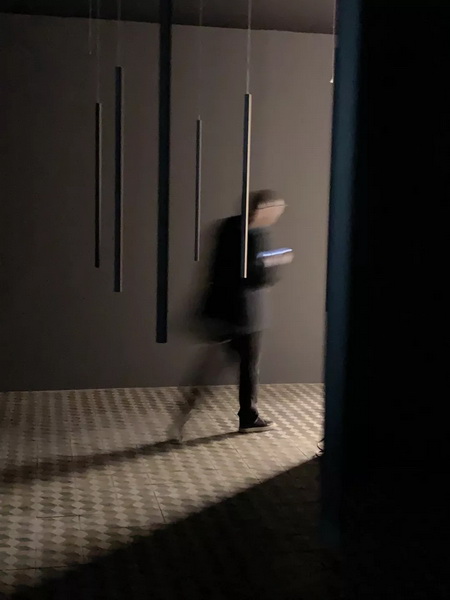
▲ 冯博一在乌镇(摄影:Shirley)
2 、作为再次担任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的策展人,我一直在思考下面四个问题:
如何根据中国和世界局势的新变化而策划具有明确文化针对性的主题性展览?
如何在中国的乡镇汇聚并形成与都市相共生的公共艺术资源,而超越美术馆模式的策展事件?
如何避免受制于旅游经济的嘉年华式节庆活动,调整当代艺术进入乡镇的展览机制?
如何持续2016年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的影响力,寻求艺术乡镇实践方式新的可能?
这些问题也是当下不断扩张的周期性大展所面临和需要反省的一种瓶颈式问题。

▲ 宫殿废墟 | 詹姆斯·贝克特
装置,722cm×350cm×575cm,2016
3 、今年的主题是“时间开始了”,我们思考的是在世界格局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全球化已经走到了令人困惑的境地,甚至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我们以为一个确定的时代结束了,一切坚固的东西已经烟消云散了,但新的时代好像并未开始,起码我们现在所获知的信息,还不具备预测未来的更多条件。
这种由现实导致的不确定性未来,以及暂时难以逾越的边界、限制、阻隔等等障碍,使我们在时间序列的间隙里,陷入了一种混乱不安与迷茫焦虑之中。这是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而发出呼叫的时刻,是对全球化前景犹疑的时刻。
因此,以“时间开始了”作为第二届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的主标题,一方面是对现状做出直白、着力的表述,以回应人们在心底已经产生的共识与感知;另一方面意味着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的时间断裂带上,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一切又皆有可能。

▲ 双眩 | 安尼施·卡普尔
不锈钢,225cmx480cmx60cm+217.8cmx480cmx101.6cm,2012
4 、在主题展上,我们以“就在此时此地”、“震荡的钟摆”、“非常近,非常远”三个单元和“未来有多远”的青年单元,分别呈现于乌镇的北栅丝厂、粮仓、西栅景区内一万多平方米的不同展场空间之中。
与其说这次展览是60位参展艺术家在乌镇营造的一个视觉场域,不如说是一种对现实景观的记录和隐喻。他们面对时代的无力之感所进行的思考、判断、表达,提示出了某种警觉的作用,以抵达艺术介入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诸多危机的问题意识。同时,这些作品赋予了内容和形式方面的视觉效果,于是视觉语言从非现实的层面进入到一个现实的层面,以此来表达他们对生存境遇的忧患意识与深刻关注。
其实,时过境未迁,那些被阻隔在内外边界的和离散在路上族群,离我们并不远。

▲ 另一水面 | 妹岛和世
铸铝、镜面不锈钢,椅子:85cmx85cmx34cm;布局:ø1000cm,2019
5 、有人问我乌镇的艺术展能不能复制到其他地方,我觉得很难。乌镇有财力和文化眼光,具备这两个因素的地方并不多。还很重要的一点是,乌镇是拿旅游的收入来投入做这个展览,而中国很多地方是花纳税人的钱在做,持续投入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并且他们往往总是有很多商业上的诉求,不够纯粹。
乌镇在这方面还是挺纯粹的,不惜成本地把展览做好。做这个大展当然会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但在我这么多年的策展工作当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乌镇这样一种力度的支持和配合。
6 、这一届乌镇艺术展做下来我有一个体会,如今做展览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了,艺术家对设备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艺术家还要带上技术工程师一起工作,我在策展工作中越来越感到困惑,我们的当代艺术会不会被技术主导,成为“技术控”?做作品越来越烧钱?我们是否通过一些新的技术将要自己要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更充分了?
比如1990年代,当时的艺术家都没什么钱,一群东村的艺术家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这个行为作品,完全没有成本,黄永砯做《<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了两分钟》,也谈不上什么技术和成本,但他们的作品非常有力量。如今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条件越来越好,作品的力量感反而弱了,我觉得这个趋势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

▲ 开放的禁锢 |王鲁炎
综合材料,尺寸依场地而定,2019
7 、在创作投入越来越大的时刻,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我们给每个艺术家100块钱,能不能做出有意思的作品?是不是当代艺术一定要花很多钱才能做好,金钱是不是一个关键因素?
有力度和智慧的创作,不应该被金钱捆绑。
8 、如今艺术家越来越职业,貌似和这个系统很合拍,职业化加速了这个艺术系统对个体的规训。越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越是要回过头来思考我们做艺术到底是要干什么,到底想表达什么,做作品的文化针对性是什么。
我们的艺术不应该走向苍白的技术炫耀,艺术要带着问题介入现实,始终保持质疑的态度,艺术只不过就是通过一种视觉化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 510个直流电机、棉球和70x70x70cm纸盒 | Zimoun
电机、纸板、棉、金属、胶带、线缆、电源,尺寸可变,2019
9 、在筹备这一届展览时,我们试着邀请一位在国际上很著名的艺术家参展,他给我回复邮件说,乌镇的艺术展太商业了。我感谢他的坦率和直言,但我也有一个困惑,我们如何来界定所谓的商业展览和学术展览,在城里的美术馆或者艺术中心,或者像798艺术区,他们做的展览就一定学术吗?在乌镇做的展览一定就商业吗?
其实问题的关键,我觉得不在于在哪里举办,也不在于谁来承担这个展览的经费,而在于通过这样一个展览,怎样把来自国际和国内的艺术家集合在乌镇这样一个场域,通过他们的作品来对现在这个复杂多变的局面作出他们的思考和回应,质疑和批判。
做当代艺术,就应该坦然若素地与身处的这个时代狭路相逢。

▲ 白色酷刑 | 格雷戈尔·施耐德
混合媒介,尺寸依场地而定,2006
10 、乌镇在旅游文化和旅游经济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比如乌镇戏剧节连续做了六届,在中国没有哪个城市做戏剧节能够做过乌镇,我当然希望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也能做到这个份上。
乌镇当代艺术邀请展做到第二届,我很难说它在中国乃至全球众多的展览中形成了怎样的一种气质,但要长远发展下去,我希望它能够形成一种模式,就像威尼斯双年展一样,能做一百年甚至更久,并且最主要的宗旨一直没有变。
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未来有太多不确定的东西,比如像华侨城在当代艺术事业上曾经做得风生水起,但由于任克雷退休,投资和影响力都在削弱,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今日的局势永远不会是你昨天所想象的模样,生存的环境往往就在一刹那间遭到摧毁,而我们只是社会变革这个复杂方程式中的一个变数而已。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