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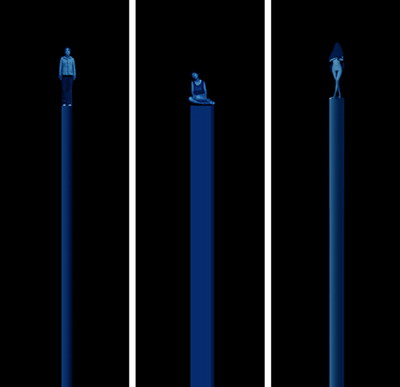

地址Add: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798大山子艺术区,北京8503信箱(100015) The Dashanzi Art District,No.4 Jiuxianqiao Road Chaoyang District,Beijing China P.O.Box 8503 Beijing 100015 China
电话Tel:86-10-84566660, 86-10-81970986
传真Fax:86-10-84566660
电子信箱Email:bjartprojects@yahoo.com.cn
北京新锐艺术计划由加籍华人高巍与艺术家高氏兄弟于2004年底联合创办,该艺术机构下设画廊、影像空间与艺术家工作室,以推介中国当代新锐艺术,促进中外视觉艺术的交流与合作为宗旨。
Beijing New Art Project is a new art organization founded by Chinese Canadian Wiley Gao, artist Gao Brothers at the end of 2004,located in the Dashanzi Art District of Factory 798 in Chaoyang District,Beijing, which manages an exhibition hall,a vedio art space and a studio complex, its objective lies in promoting Chinese contemporary and experimental art and encourag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llaborations in visual arts.
收藏本身才是最有意义的
——乌利·希克(ULI SIGG)访谈
高氏兄弟
时间:2005年2月26日
地点:北京建国饭店
高氏兄弟:大家都知道,1999年在塞曼主持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由于你的大力推荐,中国当代艺术家得以大规模在国际艺术舞台上集体亮相,使中国艺术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在那之前,你还设立了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为国际艺术界了解中国当代艺术提供了一个可延续的平台。请你简单地介绍一下当初设立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的初衷,以及当时的情况。
希克:我在1997年在北京设立了CCAA中国当代艺术大奖,我的初衷有两个,其一是鼓励中国艺术家的创作,其二是为了吸引国际艺术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注意力。我当时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很有自己的特点,有很多很好的艺术家,但是缺少在国际艺术舞台上展示、交流的机会,没有被充分关注。所以,当时我邀请了塞曼先生作为CCAA的评委。这个时候,塞曼已经被任命为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划人。这样,他以双重身份来到了北京,了解了中国艺术正在发生的变化,看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他非常喜欢。因为当时他一直在寻找西方当代艺术主流范畴之外的新鲜的东西,他觉得他在中国找到了!于是,他就决定要邀请中国艺术家参加他策划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看来,我们成功了!当时塞曼希望邀请一些中国艺术家在双年展上现场做一些作品,但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实现。因为塞曼是一月份被任命为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划人,而展览六月份就要开展,时间有些来不及;所以,只好从现有的作品中选择作品。
高氏兄弟:记得当时在艺术圈子里有一种说法:认为参加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都是你的藏品,中国艺术家参展是你和塞曼之间的一种交易。看来你刚才的陈述是有必要的,应当可以帮助人们消除一些误解。
希克:这也是我刚才解释当时的情景的原因,但我想有见地的人是不会有那种想法的。塞曼去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艺术家。他选择作品是看哪些作品适合他的展览。他最后大部分选择了我的藏品,也是因为他觉得他喜欢些作品,这样也就有了一种合作吧。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也是一个好的收藏家和一个差的收藏家的区别:好的收藏家总是可以找到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总之,我觉得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大规模展出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的重要性与将这些作品在一个仅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专题的展览上展出是不同的。
高氏兄弟:记得中国当代艺术家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是在1993年的第45届……
希克;是。但在那一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不仅参展的中国艺术家的人数不如第48届双年展多,而且那一次的意义也不同于这一次。因为在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中国艺术家已经不是作为一种边缘化的地区性的艺术现象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而是被塞曼打碎、分散,完全溶于整体国际艺术之中了。另外,从与受众的接触面和作品的影响面来说,也是非常不同的。1993年的双年展时,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都被集中在一个并非展览主场地的一个“中国厅”里(pavilion)。这显然无法与1999年的第48届双年展相比,后者的受众显然要广阔得多。可以说,那是中国艺术家获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亮相机会。
高氏兄弟:好,我们回过头来再聊聊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这个奖已经设立了好多年了,先后有若干艺术家获得了这个奖项。你认为它是否达到了你当初预期的目的?
希克:从得到国际策展人的关注方面应当说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方有像塞曼,还有PS1的阿兰娜·海斯(ALANNA HEISS),还有侯翰如等这样的著名策划人的关注。当然,他们都对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很了解了,但他们可以通过CCAA这个大奖更直接迅速地了解到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从这个角度,我想,CCAA不仅有了自己比较健全的机制,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们会进一步做出努力,使CCAA产生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具体的讲,中国已经在各个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众对当代艺术的兴趣也越来越强,所以我们要通过CCAA大奖这个渠道,把当代艺术介绍给中国的公众,寻求它在国内公共领域的影响力。
过去我们的财力有限,仅限于我个人的财产。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组织委员会,我们会争取各方面的帮助,把它放在一个更加宽泛的领域进行操作。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参与进来,这个大奖不是我自己的大奖,它最终应当是中国的大奖,我希望它在中国能成为像英国透纳大奖(TURNER PRIZE)一样对公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奖。另外,我还想在CCAA基础上设立一项艺术批评家大奖,因为我觉得在中国艺术批评家的作用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高氏兄弟:这是一个不错的设想!请简要介绍一下CCAA机制的内容及运做方式。
希克:CCAA刚开始的时候是由艺术家本人提供个人的若干作品和资料,然后参加评选。后来慢慢改为由策展人提名,然后经过评委会评选确认哪位艺术家最终获奖。这就更扩大了参评艺术家的范围,并使选择更加合理。CCAA奖每两年评选一次,目的是在过去的两年中找出最优秀的艺术家,授予他大奖。另外,CCAA还有一项特殊贡献奖,奖给那些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起到特殊作用,做出特殊贡献的艺术家。
在1997年刚刚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很低调,因为当时不知道中国政府对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态度。那时整个社会的透明度不高,环境不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的人在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有那么多的展览在做。
高氏兄弟:刚才你提到想在CCAA基础上设立一项艺术批评家大奖,那么,你是否可以谈一下你对中国的艺术批评的看法?
希克:在90年代,有些批评家在从事艺术批评时并不把重点放在艺术家的作品上,而是用很大的篇幅去论述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形势,有些内容和作品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一种官方的说教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并没有达到艺术批评应当起的作用……
高氏兄弟:你不认为艺术作品与你所说的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变化之间有联系吗?
希克:当然我认为艺术作品会和这些有关,这是肯定的,艺术批评家也应当对这些做出必要的反映。但我认为,艺术批评不应当用官方大政策一样的说教来替代,用这些与作品没有多少关系的东西大规模地放在他的文章中填充篇幅。举个有类似逻辑的例子来说:70年代末的时候我在中国有很长时间。有一次我去进行一个谈判,对方路上耽误时间去晚了。在解释为何迟到的原因时,他说都是因为受了“四人帮”的毒害。这种说法就有点像当时有些批评家的对艺术作品进行评论时方式。
高氏兄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好,接下来想请你谈一谈艺术收藏方面的问题。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你收藏某位艺术家的作品依据的标准是什么?
希克:我的收藏标准是在变化的。在我收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之前,我有很长时间在收藏西方的当代艺术作品,我一直在关注西方最新出现的艺术现象,这使我对当代艺术作品具备了一定的鉴赏能力。我来中国之后就很难有关注西方艺术的机会了。于是我开始接触一些中国当代前沿的艺术作品,研究它们和主流之间的区别和发展,当时我知道一些作品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史是很重要的,但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些作品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真正吸引我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家慢慢成长起来,他们在探索之中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这是我感兴趣的。我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时是参照了西方的当代艺术标准的。我并不是觉得这些作品本身和西方当代艺术有多少联系,主要是觉得这些作品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化。后来,也就是到了90年代之后,我的收藏更注重作品本身的能量和它的冲击力,不限于一种类型,各种形式的作品我都在收藏。
高氏兄弟:那么你收藏这些作品,是否也有升值的期待?
希克:从升值角度,我并非太多考虑我自己的收藏,而是期待整体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将来在国际上有一个提高。但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品价格长得太快了一点,这有些令人担忧,对于一些像我一样有兴趣系统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的收藏家来说,要追随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难了。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当代艺术的价格在国际上还是很低的,但现在一下子超过了平均的国际艺术品价位,我觉得有些不太正常。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期待升值和资本的生长,而是不断地充实我的收藏,使我的收藏范围不断地扩大,升值不是我的目的,也非我的兴趣。我觉得收藏本身才是最有意义的,收藏本身才是我的目的。
高氏兄弟: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些中国人在收藏中国的当代艺术品了。而且,从我们的作品被收藏的情况来看,某些中国收藏家的购买力并不比西方收藏家低。
希克:我不太了解这些收藏者是出于什么目的收藏艺术品,我知道有些人只收藏那些已经成功的艺术家,这样不需要冒什么风险,这使得这一部分艺术家的价格飞涨,然后影响了另外一些艺术家。
高氏兄弟:当然,中国人介入当代艺术品的收藏刚刚开始,到目前为止,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的主要买家仍然是西方人,我想这应当是一个暂时现象,需要慢慢改变,从文化生态角度看,中国本土需要有一个健全的收藏机制,这是确保中国当代艺术正常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你作为最早收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西方人,对在中国本土建立这样一种收藏机制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希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很有挑战性。在这方面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其中之一就是要公众看到这些作品,看到了就有可能喜欢,喜欢了才有可能收藏。也就是说,需要对中国公众充分展示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提高公众对当代艺术的认知度。我觉得在这里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问题,首先必须让最上面的顶尖人物有机会能看到并理解和接受甚至喜欢上当代艺术。这些人可以是艺术家、知识分子,或者与艺术有关的人,他们会给更多的人谈论他们对当代艺术的见闻和好恶。这种讨论越来越多,就会慢慢影响“下面”更多公众。
往往收藏者之所以要收藏艺术品,是因为他们的收藏工作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他们并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尊敬,社会地位也因此有所提高。但现在的情况也许并非如此,大家并没有对收藏者表现出这种应有的敬意。另外就是艺术批评必须跟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改变人们对艺术的认知习惯,人们往往习惯于旧的官方化的欣赏习惯,看一件艺术品首先是看漂亮不漂亮,美不美。然而,当代艺术不能仅仅用这种方式来衡量。所以,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讨论不应当仅限于艺术圈子和知识分子圈子,而应当扩展到公众层面,告诉公众对待当代艺术不能用传统的老眼光、老标准。当然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西方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在我的国家也是这样,只是我们西方发生的早一点而已。需要慢慢地改变人们的欣赏习惯。要讨论这个问题,也许要用一本书才能完成。总之,要给收藏者一个收藏的理由。
高氏兄弟:你谈的这些很重要。也许我们应当找机会促成一些有关当代艺术欣赏与收藏方面的交流活动。
希克:具我所知,中央美院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给一些希望收藏当代艺术品的人提供一些信息。他们做这项工作的原因是因为差不多近二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中最重要的作品都让西方人买走了。但自70年代末至今,在中国却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组织或个人做过这项工作。我对中央美院的这项工作有所了解,但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计划,是否系统地在做起来。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也应当讨论一下,就是中国的收藏者应当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可能有些人刚买了房子,觉得屋子里要有东西挂,所以开始收藏艺术品;也可能有些人买艺术品就是为了赚钱。开始当然可以是这种初衷,但要长期进行收藏工作仅仅有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知道一些艺术发展的知识,知道艺术品本身的意义。再重复一下我的意思:收藏者不应当仅仅对艺术表面的东西感兴趣,而应当对背后深层的东西感兴趣。
高氏兄弟:你所指的背后深层的东西是什么?
希克:就是说艺术品的效果是一种表面的东西,深层的东西就是指艺术家为什么创作了它,为什么他(她)用这种方式做而不用那种方式做。一件艺术品的意义是什么?艺术品是一个窗户,通过这个窗户你能看到什么?更重要的是收藏者能从所收藏的作品中持续地感受到什么?最深层的人思想的东西。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我只想再说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收藏者或者收藏家应当找到自己的关注点,也就是自己收藏的范围,找到自己的关注点也就能区别于他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高氏兄弟:好!如果希克先生能写一本关于艺术收藏的书,那会对中国的收藏者大有好处。实际上,你刚才你谈到了一个收藏家的个性问题,收藏家和艺术家是一样的,也要寻求和保持自己的个性特点。那么借此机会,我也想通过这个访谈让更多的人了解你作为资深收藏家的个性特点,比方说你与同样热中于收藏中国艺术品的比利时收藏家尤伦斯在收藏方面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希克:我想说的是,我并不十分了解别人的收藏方式,所以我不好比较。但我自己的特点是我专门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而且我不像其他收藏家一样找一个收藏方面的顾问,比方找一个策展人做中间人,我完全是根据我自己的判断,也就是说我喜欢收藏哪些作品不需要任何其他人充当我的顾问。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因为我愿意通过这种方式认识更多的艺术家,更直接的与艺术家交流,通过与艺术家交流了解作品背后的东西——一个艺术家为什么创作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作品。我想这是我与所有其他收藏家都不同的一点。当然,我这种亲历亲为的方式只能在中国能做到,如果在国际范围这样做是不可想象的。应当强调的是我的兴趣是中国,这是我的初衷。我以不同的方式了解和认识中国。我本身是一个商人,我通过商业活动与中国交流;另外,我还曾经是瑞士驻中国大使,所以,我也通过外交的方式与中国产生交流;但我还是一个收藏家,我更愿通过艺术品对中国有更深的了解和交流。我也想借这个谈话让更多人了解一个收藏家面对的复杂的问题和挑战,事实上一个好的收藏家和一个艺术家、一个批评家一样,时刻要思考,要面临挑战。收藏家所做的就好比把自己的钱放在一个火焰烧烤的炉子上,本来这些钱也是可以用来做点其它事的。

![[空间]唐昕:做机构,如同耕一块地](attachment/190428/95e05dad2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