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青上双作品,上海电力百货大楼
装置的空间政治:404城市学习小组2012年12月27日活动记录
【1】前言
主持人:
来介绍一下,石青是这次上双主要的艺术家。他在我认识的艺术家当中,是一个对建筑理论和早期历史阅读很多的艺术家。当然许多艺术家不屑去读书,所以他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位艺术家了。他的工作室里有很多很多书的。那么这次他过来呢,我们之前简单聊了一下,他想要谈他的作品当中,关于空间在艺术与生产中承担什么样一个角色。尤其是在参观和展示对象游走之间,艺术作品到底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
这个是我们博士的同学邱兆达,他上次给了我一篇库哈斯的媒介理论,库哈斯的媒介运作的一篇论文,我觉得写得挺好的,虽然一直在建筑学范畴在说,但是我觉得对库哈斯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就请他来,喝喝茶扯扯淡,聊着这么一个事儿。
石青:
我也是来扯淡的。其实空间作为一种艺术的方式历史并不长。这一点格罗伊斯在他那篇《装置的政治》里说到这一点。就是说艺术它的传统分类还是按媒介分类的,雕塑、绘画、然后到今天已经有媒体艺术,然后有表演艺术、有录像艺术。但是这些都好说,就是你在跟别人介绍你的工作方面,你说你做什么的,比如搞绘画的,都好说。那么唯独是你做装置的你说不清楚。你如何跟别人解释你做装置,这个非常难解释。因为你说你做雕塑,其实你也不是,雕塑跟装置不一样,雕塑是个可凝视的客体,你盯着它看,这叫雕塑。装置不是,装置它是一个,用我们现在的话,它是一个场,它不是一个中心的东西。所以装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特别难解释的。
后来看了格罗伊斯的《装置的政治》,他对装置的理解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比较准确的理解方式。他对装置的解释其实是密切跟空间相关联的。比如一个典型的展览里有各种类型的作品,有录像有雕塑有绘画。观众可以一个一个去看,你可以把它们分割开看,
你也可以拒绝。比方说这幅画我不喜欢,我可以跳过去,我可以不看。但装置不是这样,装置它就是一个空间,它是一个空间的艺术,你没有办法拒绝它,你只能进入它,你如果拒绝的话就是拒绝整个空间。当装置在一个空间里出现的时候,整个状态都可以说都是装置的组成,你只能去进入。所以说格罗伊斯为什么单独谈到装置的政治,就是他认为,在这个空间里,艺术家可以有自主性的建造这个空间。他认为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自我民主化的开放的形式。我不能拒绝任何一个人,我把所有人邀请进来在我的空间里。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艺术家自己认为的,或者说是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家认可的方式,民主的开放的方式。这种开放的方式是和装置的空间性质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下面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好,艺术家的这个空间,它还是一个象征性的私人空间。因为这是我的作品的地盘,是我可以布展,我可以布置,而别人是不能动的。从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种象征性的私人空间,这种象征性空间可能是由艺术家的一种自我意识,或者说是他的一种观念去塑造。比如他可以把空间塑造成是一个公共空间。但这种公共空间呢,它又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空间是比较暴力的,因为游戏规则是艺术家定的。但格罗伊斯并不把这看成是一个矛盾,他认为西方的自由,恰恰问题就在这儿。我们所谓的自由,是一种制度下的自由,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状态下的一种行为方式。它是一个制度下的,是在有法律下的,在有所规定可为不可为之下的一个方式。所以他认为,装置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揭示。它可以让观众在这个层面上,看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包括我们政治形态中,权力的隐藏方式。他引用海德格尔的话,解释装置它有一个去弊的空间的方式,它的作用在揭示 去揭示一种社会权力关系。当然这是他的一种角度。但是我认为他这是在把装置和空间,尤其是空间政治做了一种紧密的捆绑。他是给装置一个很好的政治学上的意义。所以说在这里,我是把空间作为一个艺术的政治方式去做的。其实空间的生产方式,就是艺术的政治方式。
所以下面我就把这次要谈的这个前提说一下,然后我会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吧,因为我觉得谈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比较抽象的。案例的话,可能会让问题更加具体化。我觉得有几个东西要提前说明一下。第一呢,因为今天是跟本当也说了,跟建筑的话题,或者说跟建筑系统有关系的,这么一些交叉的话题,可能这样谈论起来就比较能够容易沟通。第二点呢,在今天你也很难把艺术和建筑用一种既有的方式进行划分,我是盖房子的,你是画画的,很难分,所以我们都是在共同的公共政治的角度去来解读它,来重新编辑它、讨论它。是这么一个背景。
所以说今天我所讲的这些案例呢,又结合了像这次上双的格罗伊斯,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策展人、批评家、写作者。他是前苏联人,然后他后来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然后在美国。他的很多观点是,在今天来讲算是比较犀利的,而且他的批评理论对我们今天的一些政治来讲,也比较给力的。包括他大量连续引用阿甘本啊,朗西埃啊,他们的一些东西。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在第一线的,策展、写作人。所以说,在这个话题里讨论,可能事情就变得更加具体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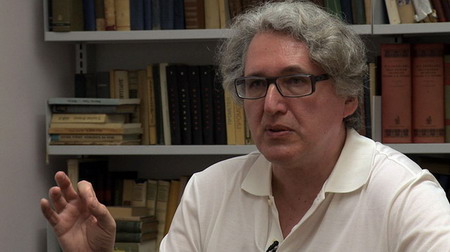
Boris Groys
【2】 空间的叠加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空间都是和社会生产关系有关。当时我在上海双年展做了一个叫“上海电力百货大楼”。因为之前做过一些研究,就是对上海四大百货的研究,就发现在1929年,四大百货,它的空间结构就已经非常有意思了。它很多东西是首创。因为以前我们国家的那种所谓的百货公司,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单纯的一个贩卖。而它不仅让贩卖专业化,而且它提供了一种叠加的功能,它里面有歌厅、有餐厅、有洗脚房、有办公室、有旅店、有屋顶花园。甚至说在后来的新兴、和大兴顶楼有一个玻璃做的广播电台。在我们这个社会层面,凡是跟消费空间有关的东西它全涵盖了。它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贩卖的一个场所,甚至是整个和人类消费有关的功能全都集合进去,甚至说包括刚才说的最新的媒体方式。而且解放以后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最高的楼,叫七重天,最高的永安那个,就是佐丹奴那个楼,最早是被上海电视台给征用的,作为最早上海电视台。而且,G。C。D在那里升起了第一面红旗,所以我们能想象党这个对点的把握还是挺讲究的是吧。
所以说,这里我是把它那个功能搬过来、移植过来。移植过来不是说要把它这几个所谓的点挪过来,而是说学习这种空间叠加的方法。其实这个方法跟屈米的方法,空间叠加一样。又是火车站,又是游泳池,又是个什么什么。它有这样一个系统,但是他是隐喻的。但好像在实际功能里也有。比如他在一个图书馆的方案里,设计了一个跑道,感觉是一个运动场和图书馆的叠加。当然在建筑最终的、至少在他盖的房子当中,并没有那么成功的结果。叠加概念体现的最明显的,还是那个公园,拉维莱特公园。就是法国那个公园,这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功能叠加的……
主持人:
但是他是用符号隐喻来去明示。拉维莱特我去过,这是一个没什么功能的公园。这是建筑语言学的一个悲哀,到了那个地方去以后,也就这么回事了。也不能说不成功,拉维莱特公园已经是非常成功了,已经达到他95%以上的想法了。但就只能是案例。
其实艺术也一样,艺术很多,也都只是自己的,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能进去的东西。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石青:
嗯。这个百货楼作品,人们是突然一下子看到的,并不是老远看到的作品。所以这个空间虽然在双年展展厅的很中间,但是非常的隐蔽。所以也是结合了我之前的一个认识。就是说,我是从对物的关注到对事件的关注。因为艺术以前更多的是以物的形式存在的。我们说过,做一个作品,说白了作品就是一个生产关系的终端,就像一个商品一样,那么商品就要制造、物流、贩卖、销售、广告,然而我们看到最后是一个物。那么大多数现在可以说90%的艺术家,无论对艺术的关注,还是对物的关注,都要做一个好看的作品,美的作品和一个符合美学规范的、要求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现在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导致了艺术实际上还是很保守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建筑行业,更多的是怎么一种做法?比如生产过程、建造过程是怎么样的?
主持人:
这个事这样,应该说在各种公司里不尽相同。还是说都市实践吧,在都市实践的话,空间问题确实会比较早的在设计最初就会被提出来。尤其是关系到空间和土地权力之间的联系的时候。包括我们的退界、公共广场的位置和它的大小,这些在早期的模型的推演当中会被呈现出来的。
但是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了,因为大多数的地方其实,嗯,至少像张永和那个系统,它还是以建造物的本身为主,即便他有同样的设计过程,造物美,精道还是最重要的目的,所有的工作都是指向这个的,他不是称自己为唯物主义嘛。当然啦,对空间的关注最后是不得不去关注的。即便是在设计院,最后也是不得不去关注,因为还有功能要使用呢。你这个房子,它不是自己捏造的东西,而是有任务书的,总归是有功能有意愿的,比如火车站这种东西。你最后还是得关注空间和现场这些的。
因为我觉得你要在一个社会空间、一个公共空间做一个建筑的话,你必须要对各种各样的负责任。但艺术家做,对公共空间他是不需要负责任的,只要对自己负责任。所以说他最后只能更多的是对一个作品的关注。
石青:
那关注的,就像你说的一个作品,或者说最后完成的一个物,得看是把它当成艺术品,还是把它当成商品。建筑师也是一样,建筑师要把它当成商品,那就很简单了,你必须得考虑空间和权力等,还有经济效益的问题。艺术家也是这样。如果你把它当成最后要销售的,或者说和媒体共融的一个东西,那么在今天来讲,可能艺术品和商品之间,区别也没那么大。因为只是针对观众,比如说在一个小空间里它是一个作品,到了博览会,它就成了商品。
主持人:
所以说是这个意思,在建筑当中,如果把建筑当成是一个产品去卖的话,不光是卖些图纸,还得服务到家。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空间、功能、以及和事件之间的关系,等等等。你必须得考虑的,否则你不成为商品。整套服务必须得考虑。
但是我们的生产方式不是这样,我们的生产方式更多的像是被安排好的。如果我做个学校,
那学校的空间它反正就是那个样子。一般你去做个学校它永远都是这样。比如学校、小学那就是这样,多少班,然后怎么排,都是布置好的,本来就有的。所以你在设计院当中会遇到这种情况,比如我正在设计一个小学,如果之前已经了一个,那你再设计一个小学的时候,还是照搬原来的小学的这种模式,甚至只是拿图调出来后,重新根据新的基地排一下,然后做一个不同装饰的立面。
石青:
意思就是说,你这张画画挺好看的,大家喜欢,就再画一次。换个背景嘛,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当它是个产品化事情以后呢,那这个东西就变味了。现在这个艺术品也能卖钱,还是个商品性质。就是说张永和也是赚钱的,但他不会完全拒绝商业作品。他做过的商业作品,几乎已经是个套路,他那个套路很明显。所以说他也是可以复制的,但是他最后通过媒介转换成商品的能力,不亚于直接作为商品为目的的那个产品销售。
我们饭桌上谈的是,即便是商品社会,但却也是带来了别的可能性。回头看,其实你刚才说的问题,在这个方面也一样的。早期的艺术品,哪怕是在欧洲,在原始时期艺术品也是有不可忽略的价值,比如在文艺复兴之前,都不可以卖的。但是服务对象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它也是订单,只不过是教皇的订单,那么现在教皇不存在了,那么订单就是社会订单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我就把这个问题拉过来,因为艺术它有一个所谓的批判性,在迄今为止已经有很多的这种艺术批判性的东西产生。但它的这个批判性失效在哪,因为这么个系统它本身就能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那么你反对批判的东西,它最后会消亡。现在是我花钱,是要我花钱让你干的活,让你上华尔街,让你反对我。这就是他们这一个系统的完善性,就是说让你的批判成为我的一部分。
所以说,今天尤其艺术在60年代以后,艺术、艺术品的批判性一直是个话题。但这个话题的问题在于它的失效,在于它被系统所收编、收纳、吸收了。那么今天我们再提批判性,应该是从哪个角度批判。那么我就认为不应该是物的一个东西了,而是说进入它的生产关系。你只有知道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你只有在它的生产关系之间加手脚、加小动作,才有可能对它产生一个真正的批判。
所以说,我们把一个物、作品,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生产过程的终端,就是你不能光看这个东西,你要回到整个这个生产关系里去。艺术家只是两头,艺术家中间有画廊、美术馆,有各种机构、各种委员会,然后他们在这里是很巧妙的对你的作品的一种过滤,然后吸收、转化,然后怎么怎么样。看上去艺术家是自由的,然而很多时候他们只是这个系统的一个订单。比如说很明显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边缘的这么一个题材,那么怎么在我这个全球化共识里面体现出来呢?那好,你中国艺术家做了很多作品,但我只要有毛主席头像的,我只要有民工头像的,我只要有社会冲突题材的。他们对艺术的选择和那个,什么荷赛摄影大赛的评判的方法一模一样。比如说民工题材的要有三幅,毛的、意识形态的两幅,他是有这样的配额的,所以说我们在整体机制里被选择。这个就是他们的艺术的生产关系的一个架构。如果我们不反对这个,那就只能按他这个走了。
所以说这个也接着上面来讲,如果说你要想在这里形成一个批判性,要是一个短暂性的,暂时形成一个艺术空间的。在我这个预设的空间里,突然出现一个不一样的,哪怕是一瞬间,这是一个方法。那么我是觉得,今天我更明确的提出一个,怎么去选择、进入一个美术馆的生产关系,那么首先你不要在他的预设之内。因为艺术、美术馆对你是由所预设的。你看美术馆布展,什么叫布展,布展就是进入它预设的一个范围:这里需要大作品哗进来了,那个长道需要什么样的作品,就要什么样的作品,它都是有个预设的。
顺便提一下,这个房子是章明的科技馆,大烟囱,现在叫 POWER STATION OF ART,叫当代艺术博物馆。它其实是一个事件驱动的空间、空间原形,不是说建筑师自己要去做这么一个东西,而是事件、大事件驱动的。
所以我就在美术馆里头做了一个美术馆,只是这个美术馆是空的。所以我就觉得这至少不在他们的预设之内。提供一个作品,而且跟他们那个需求还不太一样。这里,我是想,因为是很多路线汇集在这里,那么这个地方可能是多种的功能性在这里。你可以在这儿休息,你也可以在这儿做点别的。反正是空的,你怎么做都可以。那么后来,在实际情况中怎么样呢?额……很多的观众就是把这儿当一个通道了,走一圈就走掉了,好多人不敢在那里休息,生怕碰坏,因为他们对这个作品有预设。我看到其他作品还栏起来了,许多作品都栏起来了。当然我这儿没栏,但是他们也不敢坐那儿,因为他认为这一定是个作品,是个很奇怪的作品。不能坐,一坐的话就破坏作品。所以说你即使不在所谓美术馆功能的预设之中,但是你会被一个观众的观看意识所预设,这是个作品不能动。但也有些人挺好的,不受规矩的,又吃又喝的。就是这么一个设想
这里插的红旗,是后来邀请了两个瑞士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是讨论边界的。当时,他们需要找空间,我说你就放在我这空间展吧。这等于说是加进去的一个作品。这里有两个作品,一个是录像作品,一个是这个红旗,都是加进去的。所以我是认为这个就是这样,我认为遭遇就在这儿,很多东西是临时性的,不一定跟你是个共识的共同体,但可以把自己的体制给打断。那么这样的话,就可能是我认为的一个艺术可能要面对的问题和任务。
【3】空间的政治
下面讲的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空间是怎么设置的。这个也是空间艺术里关注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最早提的问题,什么是装置?
装置已经是艺术家一种比较自主性的、民主性的方式,虽然它来自于一种非常暴力的,非常私人化的这么一个处理方式。艺术家在定游戏规则,那么格罗伊斯就认为定游戏规则这种做法其实是跟空间社会权力这种结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样的话有个问题,就是艺术家做的事情也就变成修辞了。就是说这种揭示的话语也是一种,就像你说一个比喻一样,还是比较修辞化。
但是我是觉得可能还不止这个,可能这个谈的比较远一点,因为涉及到一个空间的问题。除了刚才说的格罗伊斯,还有另外一个列斐伏尔,他的空间的概念理论。先说柏克森的唯物哲学主线,他呢对空间是一个排斥、贬低的态度,他就认为历史是有生命的、丰富的、辩证的,而空间是孤单的、单一的、然后僵死的,他对空间是这么一个问题、一个认识。然后后来的列斐伏尔批判他们为马克思教条主义者,他们对空间是排斥的,他们认为历史、历史性是决定发展、文化生态的主线。甚至,福柯被列斐伏尔描述成一个在空间概念上模糊不清的,尽管福柯也提异托邦,他也提这个空间问题,但是他不明显。甚至有一次,列斐伏尔在一个研讨会上谈论空间的时候,有一个听众很激烈的对他来进行一个反驳,就说你还在谈空间,空间这个东西是反动的。你看,他用了空间是“反动的”这个词,可见当时那个时候整个无论是哲学还是社会哲学对空间的一种态度。列斐伏尔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就想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把空间的问题重新提出来。用他的话就是,空间和形式揭示了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并且作用于它们。这是他主要对空间的概念的引入。

石青作品,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所以说,结合具体到我这个作品,“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里来讲,因为我在这里,看这页吧,明显一些,它是设定了两个历史,一个历史就是说是工作室的历史,我工作室里有好多那种用的材料,实验用的模型、半成品,还有做完以后又重新再做一遍、改造的一些东西,这个散落在这个空间里。然后其中还有另外一些建筑模型,可能是乌托邦的、包括一些构成主义的这种历史形态,这么一些东西的模型展示放在一起。这说明,一方面是我的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的个人历史,一方面是一个社会中的集体性的这么一个运动。而且尤其像那个当时共产主义之后,有个叫生产主义者,他们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就觉得要不要取消艺术家这个角色,他们认为是艺术家加工程师。其实这点的话我认为就跟建筑有关系了,那帮人的确是一帮设计师跟建筑师和艺术家的这种合体,他们认为可能最好的应该是艺术家跟工程师的合体。那么到后来越来越激进,他们认为干脆就没有艺术家这个东西。像之后的包豪斯的梅耶就是,他完全否定艺术家的角色,他觉得这帮人就是天天在无病呻吟,完全就是那种不干什么正事儿的,于是他的运动更加激烈。包豪斯不是管老师叫师傅么,其实师傅这个词,跟那个工程师那个词给我们的启示很多程度是一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一个角色的分配,所以要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这样。所谓历史这样的东西,它在和空间并置的时候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时我做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没有看格罗伊斯的文章。但是我看了很多当时共产主义的时候很多观点,所以我把它放进来。但是我在这里又不想造成一种线性的二元论对立的结果,一个个人的、一个集体的,这边还是活的、这边全都死了。因此这些词,我管它叫死词,都是当时是很激进的名词,在今天已经不用了、不知道了。因为很多英文中国人可能不敏感,外国人其实他也不大认识,因为这些词全都是一些缩写,或者是一些那种他们自己造的词,比如说塔特林造的那个词,飞翔器,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主持人:
学过建筑史的话,对这些词应该是很敏感的。它就是专业性的,早年的风格派,De Stijl什么的。它们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比较激进的东西,包括艺术、包括工程。你看这个就是全铁,这个在历史书上是有一个照片,其实也是一个方案,他画了一个图。然后石青就照着照片和他构想的那个尺度把这个模型复原出来。
石青:
未完成的。所以然后你看我这个架子,这都是没做完的,做一半做不下去的东西。然后植物呢是作为第三方引入的,也是跟列斐伏尔所谓的三元辩证法有关系。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有看他书,我只是觉得必须有一个东西,让它来进来,而不是让它前面有这么一个冲突。所以我把植物当做第三方引入,这也是我读理论的一个发现。因为植物它是中性的,就是说你怎么把它植入进去,就是说你剩余的位置放些植物。为什么放植物不放别的呢,到不是不能放别的,我觉得植物可以,放娃娃也可以,而且可能洋娃娃的中性可能更强。所以说艺术家的粗暴就在这儿,我觉得放这个,啪就放进去了。不过这没关系,粗暴我不管,放娃娃也一样粗暴。
主持人:
就是说你在放植物的时候,植物的大小位置,这些你是靠什么判断呢?是视觉影响的吗?还是就叫一帮工匠随便放?
石青:
是我自己放的。植物的引入很重要,它一定要是中性的东西。它不能再产生符号性很强的东西,比如说你放些砖头,或者你放些钢铁,这些指向性太强。植物在这方面来讲,它是比较灰色的。而且它还是一个遮盖的作用,会把东西给遮盖住。比如说在拉维莱特公园设计当中,设计图纸本身就没有植物,只有网格线。它本身没有植物,但它真是个公园,当你真的要去造的时候,植物就必须要去种。这是后来景观都市主义在早期的讨论当中就已经提到这方面的问题了。
散开说,这里还有一个艺术家自己的认识,个体的经验和趣味。这个没办法,可能换你就放娃娃,也有可能。也可能你换一个性质同样的东西。这都是艺术家个人经验在里面。摆放原则会不会又牵涉到一些视觉艺术的经验呢?这个就需要艺术家的一些个人趣味和他的喜好去决定。
丘兆达:
建筑有时候就不是个人趣味的问题了。比如这个展览里的植物,是不是可以种满,然后我让你走都不能走,强暴你?这个其实跟钱有关系的,植物要花钱的。更微妙的是石青摆植物的时候兜里要算计一下我还有多少钱,这个要算计的。所以到底是用真植物假植物,他也要算计一下,真植物还有在展览期间维护的问题,是不是假植物更方便,或者算了一下发现假植物比真植物贵太多了,最后还是选真植物。
建筑呢是不用算的,图上一个个圈画就完了,反正不是他掏钱。是不是要考虑预算的问题啊?可一般这个东西不纳入建筑生产的预算的。我曾经做过一个体育馆,当时施工时候说缺植物,图也没有,就直接打个电话给校办,说弄点植物过来。啪一下子,体育馆那边,我还没去呢,它全部放满了。我们建筑的可能更要考虑的是没学,,要对美学负责的,对领导的美学负责的。说笑了,继续继续。
石青:
我们刚才谈到了空间的一些元素,这里还有一个设定。因为这里的东西就是说,你怎么界定它。我是很粗暴的,这个是材料,那个是半成品,这些性质都是我认为的。的确,我也认为它没做完,但是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一个艺术家,你把一个破瓶子拿进去,观众都把它当作品,这个本身在预设之中。现在你说它不是作品,那么观众会困惑,就会不买账。他还认为你这是个作品。就像以前有个艺术家写个纸条在那,说“展厅中的所有作品都不是作品”,这个有点反抗的意思了。但没用,在规则里,它还是作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是经过艺术家认定和筛选过的,选择过的,必然带有作品色彩。
这个一个悖论,但是这种悖论,就像格罗伊斯说的,它会让观众有一种疏离感,这也是一个装置的特点。传统的艺术,他认为传统的典型,是会让观众感觉孤单,比如看画,看雕塑的时候。因为每个作品是分离的,你看这张画,我看这张画,我们一张一张画看下去。但是装置不行,装置是你必须这么一堆人在那同一个空间看这么一个东西。它是反区域划分的。就是说你只能在我们这儿,临时被我们召集起来看这个东西。他认为这个是装置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按照这样的说法,那么在一个装置里,其实观众反而成了中心了。它提供一个反思或者说是再观察的机会,这个和其他艺术不太一样。他认为,我们展厅里的观众,这些观众是一个无条件型的集体,这些人没有一个共同的过去,它不是一个共识的主体,就是临时凑的,是个旅游团。像我这个展览去了很多旅游团,很多人说,我擦,你们这是园林展吗那么多植物?
这是花园吗?还有说表达生态可持续的。很搞笑,因为这个地方是香格纳画廊,在M50,M50又是上海历史保护的一个什么旅游点,4A景区还是什么。然后有一个旅游大巴开过来,一群大腹便便的外地游客就会进来看。看到很多植物,就会说这个艺术家表达生态的,就会评论的。很多艺术家也这么说,这些观众就跟我们坐一架飞机临时凑起来是一个道理。这个飞机掉了,上帝就说好不容易凑齐了这么一拨人,凑齐的那拨人是没有共同的过去,只是在飞机上一起了,没有一个共同历史的。他认为这反而是装置所能体现的一个所谓民主化的东西。这是它的一个贡献。所以说你看当代艺术作品里,尤其在装置作品的空间里,很多就是针对一个作品鉴定,然后怎么生产出观众,而不是艺术家做了作品,然而观众来看。好多有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反而在以前的艺术里面这个是没有过的。
那我是觉得,真的是在一个装置的东西里,才能产生一个就是大众能够参与的东西。这也是艺术家可以玩的一个东西。这里面的弹性和深度,也不像格罗伊斯说的“可能还有这个东西”。我认为装置可能是比较彻底的一种所谓当代艺术的一种形式,它不是一种媒介,你没办法说它是媒介还是什么东西,没法说。(主持人:其实是热媒介,传统艺术形式是冷媒介)
【4】空间的劳动
下面再讲讲劳动。劳动这个话题,我感觉有点,有点更像艺术家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的理解里,建筑师要工作但不需要劳动的。而艺术家要,传统艺术家要自己雕一个东西,要身体劳动,对吧。那么建筑师不就画画图吗,你没有身体劳动,你也不需要去盖房子是吧,你盖房子还盖不好,还盖塌了也有可能。
而今天的艺术家反而和建筑师有点像了。就是他也有了一个所谓的劳动身体和工作身体的之分。最典型的是艺术家赫斯特,那可是大腕儿艺术家,杰夫·昆斯啊,包括很多艺术家。现在包括刚出来的年轻艺术家,不自己做东西的。到了当代艺术,有些东西也没法做,比如说我焊个大铁架子,自己没办法做的。其实你看我作品很多都是自己做的,但如果焊大铁架子一定要有工人做。因为你没法做,你自己算什么呢,你没有资源,没有体力做这么大。所以今天,如果艺术家获得个项目,出了方案,第一反应是,拿材料费。拿材料费找工人做,去完成一个作品。那么这个时候艺术家更多的是像一个工程师、像个建筑师一样。他画图纸,画完图纸之后把订单交给下家,下家就是各单位。那么好的时候,就是展览不多的时候,下家好找,而展览多了,比如大型群展的时候,就不好找了,因为大家都抢。而且像很多国外的大牌艺术家,他们都到中国来做东西了,因为劳力便宜。今天更多的,尤其是做装置的,其实是一种工作身体而不是劳动身体。那么格罗伊斯他的理解就是,艺术家把自己的身体和劳动分开了。
当然一方面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艺术家,以前的艺术家,辛辛苦苦手工打造,这个东西就比一个工人打造的更有价值,更有崇高性(SUBLIME),因为这个作品里带着艺术家的汗水、心血、智慧,所以它更珍贵。它是艺术家亲手雕的,这是我们的一种恋物,可以说是一种工艺的东西吧。格罗伊斯认为在装置里面,艺术家把这个恋物的东西切除了,就没有这种恋物的可能了。也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复制的东西,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种东西其实它是更通向诸众的一种方式,它已经没有能恋物的可能了。
那么刚才说,那么艺术家的身体,还存在艺术角色,它是一个什么角色呢?格罗伊斯也有讲到。他认为所谓的艺术家的劳动身体还有,比如说你去展厅去布展,你把画拿到空间,这个还是你的劳动身体,但这个身体已经从你去做一个作品变成了一种行政上的东西,你要跟人家谈判,跟画廊、基金会谈判,你要运东西,你要去布展,你要去指挥,这种方式,这也是一种劳动身体,你并没有完全脱离掉。只是说这种劳动分为了建设性的和非建设性的。这种是非建设性的,不是直接进行生产。另一方面呢,格罗伊斯说,展厅里面出现了艺术家的身体。他就举了个例子,是阿布拉莫维奇,做行为的。做行为她要用身体来表现,阿布拉莫维奇有个作品是,她在画廊生活一个月,她站在那儿,就是供观看。他就说这时候产生了一个反思在那儿,就是说我把一个东西挂在那,你不会认为它是一种劳动,你不会想到它,就感觉它就应该在那似的。其实它也是人搬过去的,调整过的。只是把那个物去掉,换成一个艺术家了。那你就想到其实那个物也需要花费劳动的。比如挂画的时候要对对齐,这就是劳动。这个时候,这种劳动让艺术家本身成为一种展示。艺术家自己身体就成为一个媒体,他认为这是劳动身体的二重性和歧义性,艺术家自己生成了一个新的身体。
那么我这个作品里,我找了三个木工师傅,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东西。就是做一个木框架,木结构的东西,一个哥特式的木结构,有扶臂呀什么的,就是一个样子。然后我们每天是要工作的时间是一样的,而且每个人接受的费用是一样的,比如工人一天四百,我作为艺术家也四百,画廊给我工资的。然后我们把这四个东西全给画廊,画廊卖掉了我们均分。这个时候艺术家的身份和工人的身份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约定好这个图纸,你可以按照你的想象去做,你可以有一个你自己的意愿在里面。我们当时在展厅里在做,工人比我做得快。虽然我每天用的时间是一样的,但我肯定没人家快。我是艺术家能做就不容易了,想方案这也是劳动。如果前期方案不算,只说在这个空间做的,他们做的都比我快。其实我也不比他们慢多少,因为我的时间,有时候下午来这个人来那个人,时间其实是耽误了。但是我晚上会补齐,他们五点钟走人,我七点钟走人,但时间一定要保证一样。工人都是钉起来的,很快。但我这个其实事先做好的,一拼就行了。我用一个好像建构的办法一个个弄起来的,所以挺好看的。他们完全就是通常钉的办法。我说你们可以自己另想办法,想任务,开放一点。但其实他们这帮人就是接活的,接活多了,就是已经完全不想了。你给他们这个想的权力他不要。所以我在墙上写了一句话,是拉辛的一句话,他讲的是哥特时代的建筑师工人的那种劳动观,他说他们是全身心地创造和想办法去工作的。他们不是为了去接个订单,他们是出于一种什么呢,你说是忠孝感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是全身心地来对这个事情。
丘兆达:
其实放在这跟今天的劳动关系对上了。现在已经丧失了那种东西了。当然这是拉辛针对当时的工业分工的时候说的。拉辛写的这个那可不一样,那是醍醐灌顶的概念了。工人干完一天的活,回去以后工人在家里面,老婆给他面包啊,然后祈祷吃饭,祈祷结束,老婆问,今天你干什么了,答我今天磨了一下屋架上面一根梁,我做得非常好,啊,god bless me,我的儿子将来也这样 。人家造了几百年教堂,就造这一个东西,每天都在祈求这个,而且他是真心的,而且他是想尽办法做好。它不是一个订单,根本不能叫订单,从这里看上去,酷毙了,从那里看上去,又不一样了。也许三十年以后工艺改进了,他儿子想出了新的好方法,把原来的工艺改进了,这个工作态度不一样,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你这三十天肯定完成,甚至不用三十天,一星期就行。
主持人:
我当时做我们那个项目的时候,上工地的时候,好像跟你聊过这个事情。我们因为底层那个玻璃门框,是我们自己定制的钢的门框,所以需要钢铁工人焊起来。那么给他画的门窗图,然后大概经过幕墙的重新设计和确定构造和尺寸什么的。工人拿着图纸,因为图纸上面写着做法是点焊,然后他们焊起来就真的是点焊,一个小点的焊接。但是按照一般标准点焊是要有这么长的一段的,然后是均匀分布的。他真的是一点,我写的是一点,他就是一点,他认为这叫点焊。然后这么高一个门框,它上面点还不是按照均匀排布的,它是底下多,上面少。换句话说就是他懒得往上爬,够得着的地方就多焊一点,够不着的地方就少焊一点。我因为这个事跟他们吵架,我跟工人急了多少回啊。我有时候看着他们做得挺好,但背面一看,哇,做得特别糙那种。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跟甲方这边急了一下。甲方说你图纸没画好,你图纸没有告诉工人怎么做。我说我们图纸写了点焊了,难道还得告诉工人点焊是什么意思么?这根本就是语义学的混乱了。
这还不算极端的,更极端的我不是讲了么,就是工人根本不看图纸的。他就一个框在这,完了弄好以后来看,怎么跟我做的不一样啊。你去问他们找图纸,一找发现图纸新新的,跟送过去的时候一模一样,根本就没打开看。

石青作品,有什么样的要求就有什么样的艺术
丘兆达:
道理是一样,不过实际上遇到不同人,其实也不全一样的。我们当时在同济那边做了一个太阳能建筑,你们可能还知道。我们当时那师傅兢兢业业到什么程度,天天打电话,图纸呢?图纸没有,我是怎么做上去。我说我先给你们做下样子给你们看,那个木梁,就是木档子,螺丝、螺丝、螺丝、螺丝,四个螺丝位置点好,这个是图纸吧。然后他就真的这样打孔,然后他待会想了一下,说不行,有个地板交接的地方是要那样打螺丝的,然后他画给我看,问我这样打可不可以,他在这里点,那还是动了脑筋的。然后他说,你要齐口还是卡口,我说我要卡口的。这真算是负责任的师傅,然后他怀疑的跟我说,“你确定吗?那样我今天中午饭之前不能做完”我只能这么跟他说我陪他。师傅尽责的时候你能怎么跟他说,那就齐口的呗,那就是偷懒了。但是他会问你要偷懒还是不偷懒的办法。这就是学校好了,不是我付钱的。做完了还会给你看。像我们的另外一个案例最后就是跟着甲方去工地,然后就把那个负责人骂了一顿,然后让他们拆了。
我就是觉得这当中已经有一种生产关系产生了。就是说生产关系已经确定的这种权力关系本身,它导致了这种结果。这个结果有好有坏,你艺术家还能当艺术品,我们那哪能当艺术品。
石青:
这就是艺术和建筑这个社会特性和公共性不一样的地方。像你们没有办法去用这种方式做实验,但我在艺术里,劳动还是最后一个方法,最后一个策略。我甚至不按照你的生产关系去走,我可以按着我自己的身体来走,然后去里面搅合一下,能搅合多少是多少。这样做对建筑师来讲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麻烦。所以你必须清楚,这个是艺术的方法不是建筑的方法,就是身体可以作为生产策略,所以我一直在考虑劳动在艺术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建筑也许更多的是身体的政治,奔向相对正确目标的过程中产生的身体政治。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