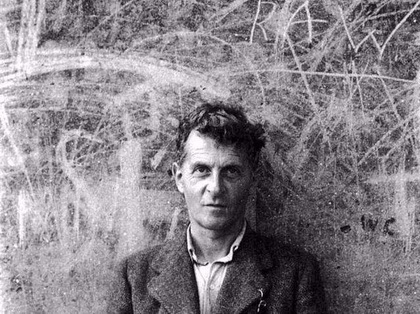几年前,德里达先生虽然来过中国,但我和他从未见过面。只是由于编辑《人文艺术》论丛的缘故,多次与他在文字里相识。朋友告诉我说:在中国,可能最早公开翻译介绍德里达思想的刊物,就是该书的第一辑(编者按:此结论似乎不够准确!)。时间为1999年初。汉语思想界的迟钝,从此可见一斑。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中,德里达的著作竟然没有出版一部,实在让人惊讶。
无庸讳言,德里达属于当代欧洲思想界的一名奇才。初次阅读到友人胡继华翻译出来的“话语的灵性”一文,我足足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反复斟酌其中的内含,但始终都很难明白文章的精义。正要把握德里达文章的内容时,便发现我所把握的东西已经悄悄地从身边溜走了,如同一个初恋不久的美人,始终让人捉摸不透,为了得着她神秘的芳心,你必须跟在她的长裙背后,魂不守舍。德里达把自己的这种文章风格,称为“延搁”(或翻译为“分延”),也就是说,只有你明白了一段文字后面的意思,你才能明白前一段的意思。德里达的语言,准确地传达出了他的这种哲学思想。甚至可以说,他的语言本身,就是他要表达的思想信念赤裸裸的见证。这样的思维方式,如果用于理解一个人的生活,便意味着:你必须理解他的下一个行为,你才能明白他现在的行动。德氏把任何文本的这种现象,称为“替补”。按照他的逻辑推论,假如我们把德里达的一生当作一段文字,或一篇文章,或一部书稿,那么,我们除非理解德里达死后的归宿,否则便不可能真正地、完全地认识他。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德里达的所谓解构哲学在死亡面前的软弱无力。由于他的死亡,再也不可能有什么东西可以“替补”上来,成为帮助我们理解他的全部文本的参照系;由于他的离世,再也不可能有什么东西可以继续往后延迟下去,成为支持我们把握他的一切思想的工具箱。
德里达的思想,明显带有法兰西民族崇尚感情的特征。人的生命情感,如同奔腾而下的江河,不断流走,不断冲出新的支流。这就是为什么以表达生命情感为职业的艺术家总是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德里达的思想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文学、艺术的批评领域。不过,在汉语学界,大致懂得德里达哲学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除了《书写与差异》少数几本德里达的专著是从法语原文译出的之外,目前市面上的一些他的著作,大多译自英文,甚至有从日文译出的研究论著。包括笔者几年前校对的那篇“话语的灵性”,其依据也只能是英文。笔者所掌握的法语,还不足以去阅读一般的法文著作,更何况去看德里达的精深论著。当时,一位来自美国的文学教授告诉我:即使在他的国度,能够读懂德里达的心思意念的人也不多。这成为了我自己在几年内一直对德里达敬而远之的借口。我相信:如果不明白一个人所讲的母语,我们便不可能渗透他的灵魂与肉体。我们把握在手中的,可能只是一些关于他的意识或意见而已。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不应当构成汉语学界的一些文化人对德里达入痴入迷的理由。至少在前几年,年轻的学人们相遇,每每都要谈及德里达的思想片断,即使没有亲自阅读过一本他的原著。德里达在短短的时间里,在汉语学界登上了几乎相当于“神人”的宝座,占据着不少青年学子们的心。他扮演着一个思想偶像的角色。作为一位后现代的思想大师,德里达的哲学,的确具有实实在在的穿透力,但无论怎样高举他的光荣、伟大、正确,都不足以把他当成“现人神”来顶礼膜拜。他的匆匆离别,再次预告了偶像的黄昏。无论如何,德里达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法兰西思想家。这从另一个侧面仿佛在启迪我们:在汉语学界,每一位以学问为志业、以艺术为事业的人,都需要思考:难道学问、艺术本身能够赐予我们永恒的安慰?难道人死后就仅仅是虚无?
他叛逆而敬畏传统,他渴望自由而传承历史的命脉,他的血液里积淀着犹太人漂泊无定的命运,他在一个物质主义猖狂吞噬人类灵魂的时代却捍卫精神生活的价值。
2004年10月11日清晨于成都澳深古镇
(作者为《人文艺术》主编,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