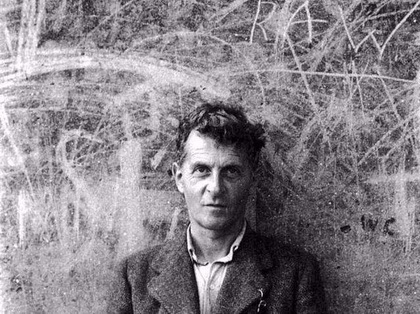一、西方史学研究的新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一样,处在深刻、迅速的变化之中。这个过程至今没有结束,仍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时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但人们仍然不难看到这种变化所表现出的“不变”,或“以不变应万变”的基本特点,那就是不断加强的理论化趋势和一体化趋势。这主要表现为重视历史认识中的理论描述,而不是将历史过程做编年式的堆砌;强调关注现实和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积极发挥历史认识主体的主体意识,在研究中无论是提出问题还是回答问题,都注重理论的诠释,以至一些历史学家提出“理论历史学”的概念;重视历史学同哲学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不断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不断开拓历史认识的选题。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认识广泛应用跨学科的方法,使传统史学和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二、西方史学发展中的新潮流、新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曾先后出现社会史和文化史潮流。这两股潮流虽然方兴未艾,不时有影响的成果问世,但是人们可清楚地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日益表现出强势的全球史观——全球史潮流。
社会史潮流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出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传统史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社会学则只见森林,却不见树木。社会史研究则要求从整体上认识社会历史现象,既要树木,又要森林,但是,“树木”不再是孤立的树木,而是“森林”中的树木;而“森林”也不再是单一的森林,而是由“具体的树木”组成的森林。2001年12月,德国著名社会史学家、现任国际历史学会会长于尔根·科卡在北京的一次讲演中指出:在60年代,我们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兴趣,已经不再是如爱迪生那样的大发明家或克虏伯那样的大企业家,而是工业化进程。我们也不集中精力研究拿破仑与俾斯麦,而是去研究那一个时代的革命,或俾斯麦时代的宪法或政党的历史。同样是在6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和E·P·汤普森等创立了“新社会史学派”,强调研究总体的“社会的历史”,提出“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影响颇大。
文化史潮流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文化学等学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文化史研究的范围急剧扩大,同时,它和叙述史的复兴也有直接的联系。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研究原始文化时,曾对“文化”进行这样的概括:文化是包含有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与习惯的复合体。这个概括既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广义的“文化史”概念涵盖有诸多的历史内容,在其直接影响下,很少进入或从来没有进入历史学家视野的问题逐渐成为历史认识的客体。1989年,曾出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加州大学林·亨特教授,编有《新文化史》文集,收有除他本人之外的另外8位教授的著述,较全面地反映了文化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
“全球历史观”在上个世纪50年代西方各种重构世界史的潮流中开始显现出来。1955年,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最先提出这个问题,此后又在《当代史导论》、《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等著述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但这在当时影响并不大,而8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才使“全球历史观”凸现出来。
60年代以后,西方有多种体现了全球历史观的著作问世,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 1982年)描述了1500年以前和1500年以后的全球文明,就建立一种崭新的世界史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在《世界史》(1967)中强调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他的另一部代表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1963),也表现出一定的全球性的历史思维特点。近年,美国历史学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1974 1989),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I·沃勒斯坦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左派”或“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新的历史视角研究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兴盛和衰落的历史,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后即处在剧烈的斗争和变动之中,现已进入“混乱和告终”时期。类似的著作还有英国史学家巴里·布赞等著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2000年)、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等主编的《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1999)等。2000年8月,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奥斯陆举行时,“全球史的前景:概念和方法论”被列为会议的三大主题之一。全球化趋势有力地促进了全球史研究的发展。英国历史学家P·K·奥布赖恩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回顾了自古代希腊起历代史学家为撰写全球史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澳大利亚学者G·R·斯努克斯、新西兰学者N·D·科斯莫、加拿大学者N·Z·戴维斯、美国学者J·H·本特利、M·P·阿达斯和J·R·麦克尼尔等都有报告,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全球历史观在西方史学的深刻影响。
当代西方史学的新特点、新潮流,决定了、同时也体现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尽管如此,西方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影响还是值得一提。因为不少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学术思潮,在历史思维的模式、历史认识的形式和内容,以及历史语言的叙述等方面,都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因此在论及西方史学的前景时,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但依笔者所见,其影响也不宜过分夸大。近年西方史学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新潮流和新趋势不是偶然的。它与冷战后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世界风云急剧变幻,“后现代主义”盛行一时有着直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