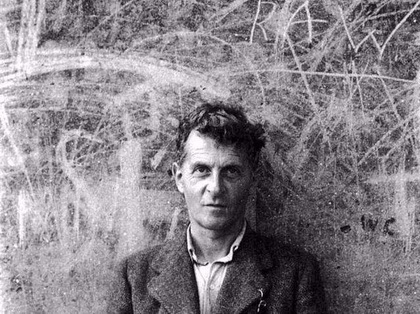摘 要:20世纪后期,历史研究的重点继续是从分析的社会科学转移到更加强调文化因素的方面来,但是面临着迅速变化的世界局面,却具有其更加繁富且已改变了的焦点。历史学家并未受到后现代主义太多的影响,但关于应该如何重铸过去的问题的确更趋复杂了。在历史学思想与实践的重新定向过程中,人们更为深入地反思和质疑了历史作为引向今日西方文明的一种单向历程的观念,政治领域和阶级的概念扩大或改变了,妇女与性别的历史日益被纳入到通史系统中来。而在迫切需要另行考察现代性以及撰写全球史的状况面前,我们对于广泛跨文化的方法仍然缺乏综合的认知,有待于未来的进一步规划。
关键词:西方历史学;政治史;女性主义史;全球历史;后现代主义
在20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期间,历史研究的重点继续是从分析的社会科学转移到更加强调文化因素的方面来,但是面临着迅速变化的世界局面,却具有其更加繁富而且已改变了的焦点①。
上个世纪后期,历史学家们曾对于所谓后现代主义对客观的历史学研究的挑战给予了相当重视,不过近年来,后现代主义已经不大为人注意了②。事实上,激进的后现代立场大多只限于美国——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印度——以及较小范围内的英国,尽管它的许多思想根源都来自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它的基本设定是:语言乃是一种自我参照的体系,它并不反映、而只是创造现实,这就否定了有可能重建过去,恰如人们确实所曾生活过的那样,从而勾销了历史叙述与小说之间的那条界线。对于这种过激的立场,1997年詹金斯(Keith Jenkins)发表了一篇极端的总结,他写道,全部近代的历史观,即历史学家可以重行捕获历史的过去,“现在看来乃是一种自我参照的、大成问题的兴趣的表述,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解说性的话语。……事实上,历史这时候就成为了只不过是在一个毫无根据的、有成见的表述的世界之中的另一番毫无根据的而又有成见的表述而已”③。
但是这一点却难以适应历史学家们所运用的各种假设,即便是今天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之后。人们怎样重新铸造过去的这个问题,比起它对于较古老的政治学派或是对于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学来说,都已经变得复杂得多。古老的历史研究的纯客观主义,早已被人放弃了。事实上,它从来就不曾被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五条件地接受过。然而近年来警觉性增长了,即历史学家乃是带着问题去接触他们的题材的,而且解答它们的方式则要受到历史学家建构他的叙述的那种语言学的与概念的工具的影响[1][2]。然而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这种过激的形式,对于历史研究和历史著作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由后现代主义思想和从“转向语言学”所引发出来的一些观念目前却大量反映在历史著作之中,尽管这些观念并非直接出自现有的后现代主义,而是出自与历史学思想与实践有关的发展之中。
而与后现代主义相类似的那些观念,就对于历史学思想的重新定向产生了一种深远的影响。这就包含着要质疑历史之作为引向今日西方文明的一种单向的历程。从这种对历史重新界定所得出的激进后果,并不必然地相应意味着历史并没有任何的一贯性。然而历史学家们却开始从宏观历史的结构转向更为关注较小的枝节、日常生活而尤其是小人物的经历。这一切也都关乎历史学家们处理史料的方式。这里的巨大冲击之来自各种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远不如其来自文化人类学[3][4]、语言学和符号学,它们全都参与了20世纪最后几十年和21世纪初思想气氛的转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从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以来,人们的注意力就日愈放在了文本形式的语言作用上来。然而历史学家们对于语言在历史学探讨上的重要性,却是意见分歧[5]。司考特(Joan Scott)④论证说,历史学家所处理的文本与真实的过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语言并不反映而只是创造现实,有更多的历史学家把语言和语境看作是历史理解的重要工具,但也注意到这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发生的。
同时,很多朝着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学家所主张的信念,即政治变化与政治事件须以社会经济因素才能最好地得到解释,却仍然没能够令人们产生多少信心。过去的十年里,在处理政治史方面曾有过两个显著的新重点[6]。是什么构成了政治领域的概念被扩大了。大量的政治史,包括社会科学史家所写的政治史,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都把焦点聚集在国家上,并且通常是在作为国内和国际政治活动中心的民族国家上。这一点确实不仅欧洲和英语国家的历史学家是如此,在中国、日本和韩国也如此,在后者中间,早在20世纪初期[7],民族史就已经取代了王朝史,而且在其他1945年以后新独立的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同样如此。甚至于在以前的殖民地国家里,民族国家的观念近年来也受到了挑战,最重要的是在印度;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低等(族群)研究”团体[8][9][10]就强调指出,不仅西方的民族国家的观念是精英主义的,而且那也不适用于更古老的印度史及其社会的与文化的分歧性。但是新的聚焦点出现了,——特别是(但不仅只是)在美国,——它把更大的重点放在了社会的、种族的和性别的因素方面。现在,一个民族往往是被看作一个次级的、可加以认同的各个单元的混合体,而不被视为具有统一认同感的有机单元。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新展览,就反映了具有不同传统的多种族的民族概念;然而正是这一多元文化主义,正在重新形成为美国的同一性,而并没有使之解体。
此外,在社会史中仍然流行着的阶级概念也经历了变化。汤普森(E.P.Thompson)在1963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就不再单纯地以社会经济的名词来理解阶级了,而是扼要地在文化方面也把各种观点和思想的模式都包括在内。但是这种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哪怕是当今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却仍然在把阶级看作是一个整体性和一体化的单元,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过时了,因为它未能考虑到远为复杂得多的各种社会的特性。在对各种政治和社会的分析中,种族、性别、宗教和意识形态要比其他的各种因素具有更为深远的重要性。这一点有时候就导致了文化史的孤立地位,而忽略了各种经济与政治因素之更大的整体作用。
此外,构成其为政治(而且也还有社会)领域的概念,也在两个方面得以扩大。一方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即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扩大事实上囊括了文化的各种不同成分;而另一方面则包括其以权力关系而表现出的私人领域,那就包含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福柯(Michel Foucauh)已经提出了权力关系在人与人的层次上是怎样在运作的基础。而在此前,权力运作都是以强而有力的中央机构(例如政府或经济)这类术语来加以考察的,在那种超级政府的形式里,权力是作用于并渗透到生活的一切层面而受到更大的注意的。而文化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语境,则仍然面临着被忽视的危险。
①有关晚近趋势的扼要评价,参见《社会史杂志》37[2003],特别是斯特恩斯(Peter N.Steams)的“社会史的现状与未来”(第9—20页),科卡(Jiirsen Kocka)的“所失、所得与机遇”(第21—28页),克布勒(Hartmut Kaelble)的“社会史在欧洲:问题的提出”(第29—37页),法斯(Paula S.Fass)的“文化史还是社会史”(第39—46页),巴达萨拉希(Prasannan Parthasarathi)的“印度社会史现状”(第47—56页),查理(Christophe Chade)的“当代法国社会史”(第57—68页);关于劳工史: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第69—76页及其他论文。又见贝哲(Stefan Berger)菲尔德纳(Heiko Feldner)和帕斯莫尔(Kevin Passmore)所编《历史著作,理论与实践》(伦敦,2003)。
②参见布莱萨赫(Ernst Breisaeh)《论历史学的未来——后现代的挑战及其善后》(芝加哥,2003)。又见埃文斯(Richard J.Evans)《保卫历史学》新版(伦敦,2001)所附对批评者的答复。
③见詹金斯(Keith Jenkins)所编《后现代主义历史读本》(伦敦,1997)第6页。又见查戈林(Perez Zagorin)对詹金斯此书的回应(《历史学,参照与叙述:对当前后现代主义的反思》,载《历史与理论》38[1999]第1—24页)以及詹金斯(一篇后现代对查戈林的答复》,载《历史与理论》39(2000)第181—200页。
④关于司考特晚期观点的总结见《历史之后?》,载司考特与季德斯(Debra Kemes)所编《思想的派别:二十五年来解释性的社会科学》(普林斯顿,2001)第85—301页。
而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晚近的女性主义史,这种被扩张了的权力观就在其中起着一种核心的作用。女性主义史的关键观念乃是女性的被压抑。早期的女性主义史曾被谴责为“过分地白人、过分地中产阶级和过分地异性化”[11][12]。女性主义史在20世纪90年代就日愈让位给了“社会性别”史,那是指女性和男性在历史社会语境中的关系。这里提出的是经济地位、种族性、性取向、立法、风尚和习俗的各种问题。
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在女性主义的理论中要比在历史思想的其他领域中起着一种更大的作用。对于某些像是司考特那样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来说,父权统治的各种形态是深深地包孕在自从古典的古代以来西方哲学“理性中心”的传统之中的,因而他们就号召对西方全部历史的、政治的和哲学的文本进行解构。女性主义的学者们根据更为经验的理由来研究妇女和其他被附庸化了的或被边缘化了的集团望求改变现状的各种方法,并且还从新的女性主义的视角重行审视了历史上的各个关键方面,诸如资本主义的出现、法国大革命、奴隶制与奴隶解放、北美和欧洲的社会改革、民权等等,以及殖民地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11]。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妇女之间的差别的考察就越发地取代了男女之间的差别。但是最近15年中一项重要的发展,便是妇女与性别的历史日愈被纳入到通史之中来。
受到与后现代主义相平行的各种观念的影响而并未完全分享到它那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的另一个领域则是有关记忆的中心作用[13]。恢复历史记忆大部分要靠口述历史,而口述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确立了。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一项公共集资的大型计划就访谈了孑遗的往日奴隶。而20世纪80年代有一项广泛的德国口述历史,采访普通平民、尤其是产业工人是怎样经历了第三帝国的。在苏联最后的日子里,回忆口述史小组也通过个别访问,力图重构斯大林主义之下的生活。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不仅是纳粹大残暴的受难者的经历,而且还有犯罪者的证词,都得到了广泛的研究[14]。尽管警惕到口述证词的不可靠,这类访谈的目的仍然是要对真正的往事获得一番更好的了解。对历史理解的另一种非常之不同的路数,则是由法国Lieux de M6moires(《记忆的园地》)集刊的编者们所创始的①。编者们对于力图在文献证据的基础之上重建过去而确立学术性的历史提出了另一种办法,即代之以把焦点放在为集体所回忆的历史之上。取代了个人回忆的乃是它要依赖已经成为集体认同的可感知的回忆物,诸如纪念物、节日和各种神圣的地点。对于他们而言,这就是民族的同一性,而特别是法兰西的同一性。德国历史博物馆也有一项主要的计划,是通过研究传说与神话在创造民族的认同感中所起关键性的作用来探讨欧洲各民族以及美国各民族和以色列怎样回忆他们的过去②。
正当一方面是历史著作越发经常地从宏观转向微观的题材,从广阔的转向微小的地区性的历程和结构时,当前世界的情况却对今天的各种社会都不可避免在经历着的各种转型要进行大规模的考察。两种大为不同的综合工作,都反映了苏联解体之后已发生改变的情势。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中曾论证说:“所有经历着经济现代化的国家,都必定要变得彼此日愈相似”。这就把福山引到了下述问题:“到20世纪的末叶,我们再一次谈论有一种方向一贯的人类历史,它终将把大部分的人类都引向自由民主,——这对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意义?”对这个问题,他的答复是肯定的。对于他,这一发展的驱动机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宣示着未来的那个样本就是美国。福山坚信一个由自由民主所造成的世界是不会有战争的诱因的[15](xiv-xv,xii.xx)。
正如冷战结束之后不久的那些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这一观念形成了一种幻觉。它是建立在一个非常简单的现代化模型之上的[16],那对于许多即使是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对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区分产生了相当警觉的社会政治史学家来说,就显得是很不妥当的了。它还以一种把自由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概念当作就是和谐的社会这一概念而在运作着,却并未能考虑到社会的不平等的作用以及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无论它们是经济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宗教的、性别的或是种族的。它还把西方的情况设定为一切非西方社会的规范。 ① 参见诺拉(Pierre Nora)编《记忆的园地》,英文版《记忆的领域:回忆法国的过去》(纽约,1996—1998)。关于德国的姊妹篇,见法兰梭瓦(Etienne Francois)和舒尔茨(Hagen Schulze)《德国回忆类编》3卷(慕尼黑,1998)。
② 参见弗拉克(Monika Flacke)编《各民族的神话》(柏林,1998),第2卷将于2004年问世。
亨廷顿(Sanuel Huntington)1996年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出了另一种相反的模式,它强调文化的作用而贬低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他写道:“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各族人民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并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它们是文化上的。”[17](P21)就像早在上个世纪的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一样,他把一系列的文明认作是世界舞台上起决定作用的单元,并预言了这些文明之间的不断冲突,尤其是在西方、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之间。但是他以本质主义者的术语把这些文化看作是有机的单元,其中时间上的转化与内部的分化都不起主要作用。他摒弃了对国际和平与共和的一切希望而论证说:“西方的继续生存有赖于美国重新肯定自己的西方认同性以及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当作是独一无二的但并非是普世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它并保卫它反对来自非西方社会的各种挑战。”[17](p20-21)这一点对于他也就意味着,被今天许多社会史学家所认可的多元文化主义代表着一种正在威胁着要毁灭西方的癌症。
无论福山的还是亨廷顿的模式,都在晚近的历史学中受到了认真的对待,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政治涵义,并且也因为他们是在全球历史的思辨层次上进行操作的,而与那些在自己的经验工作中避免采用这类模式的历史学家们的工作格格不入。然而,过去15年之中的发展已经表明,无论是转向微观历史还是老式的民族史或地区史,都不足以处理正在全球规模上进行着的变革。重要的乃是要重新考察现代化的特性。随着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思想中的文化转变,“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已经不行时了。现代化认为是应以“现代的”观点、制度和行为逐步地取代“传统的”。其动力乃是思想的、科学的、技术的,而最重要的则是经济的。它植根于西方文化,但它的范围却是普世的。它设定了“资本主义的形成、工业化、自由民主结构的兴起、民族国家的建立、多元主义社会的形成以及建立在成就、科学的进步、某种人格结构、某些信仰体系以及心灵状态”[18](p120)之间的互相关联性。
现代化这一观念遭到了两种理由的反驳。首先是由于其宏观历史的特性。它对于历史强加上一种主宰式的叙述,然而历史,正如它的批评者所论证的,并不是一个一贯的、定向的历程。其次,因为它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规范性的而又可预知的,不仅是对西方而且也普遍地对全世界都是可预知的。它忽略了进步与现代化的消极方面、20世纪的浩劫、世界大战、种族绝灭、法西斯的专政。对于它的许多批评者而言,它以其殖民的、后殖民的各种形式,乃是和西方帝国主义紧密相联系着的,包括对非西方之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统治。近年来某些印度知识分子提出了对现代化与西方现代性(及其所设想的根源乃是出自启蒙运动)的批判,也采取了类似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提出的形式[10[19]。
然而无可争辩的是,就在我们的眼前进行着种种现代化的历程,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当然也还有经济方面的,而且这些领域的现代化尽管大部分源出于西方,却改变了全球的各个社会。因而现代化就要在全世界的范围上加以看待。但是旧式的现代化模型运用到非西方的各个社会时,显然是不敷用的。而哪怕更早些的时候,用它们来分析西方的发展也是并不适当的。例如,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力图解释何以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的历史行程竟然偏离了他们认为是现代化的正常进程,像是由英国和美国所代表的那样;在英、美那里,工业化乃是伴随着民主化的[20]。但是晚近的研究已经表明,不仅是欧洲的现代化有着不同的道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也代表着现代化的各种形式[21],而备受称道的英国模式却并不反映现代英国、法国或美国历史的各种复杂性与矛盾①。
① 例如保尔坎培(Arnd Bauerldimper)《历史著作是一种规划<辉格党的历史观>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德国的另一条道路>这一变格的批判》,载贝格(Stefan Berger)、兰贝尔(Peter Lambert)和舒曼(Peter Shumann)所编《德英文化交流的历史家岁月、历史、神话与回忆,1750—2000》(哥廷根,2003)第383—438页。向古典的现代化观念挑战的较早著作有迈尔(Amo Mayer)《旧制度的持续》(纽约,1981);格申克朗(Alexander Gerschenkron)《历史视角下的经济落后性》(麻州,剑桥,1962);摩尔(Barrington Moore)《独裁制与民主制的社会起源,近代世界形成中的领主与农民》(波士顿,1969)。
这一模式之应用于非西方世界,已经证明了是更为不适当的。现代化有相当多的成分作为公司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部分,在技术的和经济的领域内并且在一定的范围内(视不同的社会而有所不同),也在消费者的模式上和大众文化上,都可以看到有类似的发展,因而就存在某些一致化的成分,然而它们都是不完整的。各种不同的社会都曾采纳了西方的现代性的某些方面,但并没有全盘采纳它们,而是把它们嵌入了自己本土的文化之中。在最近的《乡土化欧洲》的一系列论文中,有一位著名的印度社会科学家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一方面力图表明以走向现代性的各个阶段来说明历史发展的这种西方观点的狭隘陸,那些把各种殖民地文化都说成是往古的或前近代的形态,注定了是要让位给现代化的进程的。另一方面,他承认西方的科学形态与社会的科学合理性已经一般地正式在被殖民的世界所采纳了,特别是在南亚。因而他写道:“在今天,所谓欧洲的思想传统乃是在绝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印度)大学中的社会科学各系里所唯一活跃着的传统。”因而很少有(假如有的话)印度的社会科学家会把自己的理论置之于更为古老的印度思想家的基础之上。欧洲殖民统治在印度的一个结果便是“一度在梵文或波斯文或阿拉伯文中绵延不绝的那种思想传统,现在是‘真正死去了’”[22]。但是在政治和文化的层次上,殖民者所引进的模式却并非没有受到挑战。一方面,反殖民和后殖民的运动深深地受到启蒙运动有关人权与民主的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们又和更古老的社会组织与政治的观念共存于印度的民主制之中,而其中的古代印度宗教观念可能被看作是迷信的。但后者却一点儿都不是前现代的,而是构成为现代性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因而也就不存在只有一种现代性,而是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现代性;历史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已经开始谈论“多样的现代性”了。按照查克拉巴蒂的说法,没有它那宗教的根源,就不可能理解印度的现代性。但是又正如他在另外的地方所指出的,现代性——我们可以设想它先天具备一种世俗的观点——也遭到了美国的以及拉丁美洲的五旬节教派复活的挑战,并且还有过激形式的正统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它们不仅仅是有赖于本土的传统,而且还在于它们反现代主义的本身就运用了现代的手段来动员群众追随他们。
对现代性的研究就必然导致全球性的比较研究。自从1990年以来,我们便已看到历史研究日愈扩张而超出了民族的和西方的主题。然而在这一点上,对于全球性的历史研究以及对于所需要的方法论的可需性,虽有着许多议论,却很少有实际的工作。专业的历史学家比起历史社会学家来,一直是很不利的。特别是在欧洲,历史学家们迄今一直是专注于他们的民族史;而在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更多的历史学家成为了非西方领域的专家,但一般地只是精通一个特定的区域。历史学家们所受到的训练则是要依靠倾向于把他们系之于民族史的或地方史的档案和原始材料。相形之下,很多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乃至政治学家则以规范性的宏观术语在看待他们的科学,力求加以普遍化。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也越来越转向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了。比起十年以前,今天在东亚、南亚、伊斯兰和撒哈拉乃至大洋洲的历史方面,已经拥有了更多的专家。对这些地区的研究,已经更加接近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但他们有很多情况还不是比较性的和跨文化的。现在有一份《世界史杂志》是1990年创立的,还有一份《全球史杂志》正在筹建之中。较早的有关全球史的研究,诸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1978—1989)》,焦点是集中在欧洲资本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渗透,而很少关心文化方面,虽说这样地遵循现代化的理论乃是出于一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今天对全球历史的需要是再明显不过的①。然而仍然有大量观念上的和方法论上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对于各种社会与文化的复杂性的考虑,比较研究——当比较是在跨文化的全球性层面进行运作时,尤其如此——就需要明确界定什么是要进行比较的以及要用什么方法。在这种意义上,韦伯的“理想形态”的概念并没有过时。但是我们今天却觉察到市场力量所驱动的全球化并没有形成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层次上的一致化,而是形成了植根于本土传统之上的分离化。警觉到跨文化的与跨社会的比较的复杂性,并且认识到全球化并不就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模式可以转移到国外去的单向过程,致力于比较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和社会科学家们于是在最近几年就开始谈论起“纠缠不清的历史”[23][24]。而且显然的是,全球研究不可能由个别的历史学家孤立地进行,而是需要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们的通力合作,以及综合历史研究与各种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各种跨学科的方法论上调谐合作。在这一点上,目前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处于这种调谐合作规划的开端。
① 参见梅兹利什(Bruce Mazlish)和布特仁(Ralph Bultjens)的《构想环球史》(布尔德,1993)。又见《国际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百科全书》中所载有关全球的各个方面与全球史的各种论文。
就历史工作(因此也就是社会科学工作)的流程而言,大抵上迄今一直是单向的,即从西方国家向外辐射。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有极其大量的西方著作译成为日文、中文和朝鲜文,也在较小的范围内译成为阿拉伯文和[伊朗]法尔西(Farsi)文,但却很少有向着相反方向的流动。印度是个例外,但大部分乃是在自从《次等研究》创刊以来的晚近30年之中。其原因之一则是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英文已经广泛地成为学术界的语言,而中等和高等教育又都是以英国为范本;并且不仅是很多印度的知识分子都在英国受过训练,而且近年来有很多印度的学者都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里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中,印度作家们参与了西方的话语。而处于印度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的核心的,当然是殖民主义的创伤。《次等研究》批判说,已经确立的印度反殖民历史学所遵循的那种叙述式的政治历史学其实是不能应用之于印度的过去的;而且它把焦点置之于主导政治与社会的精英们的身上,也忽略了各个次等的阶级。于是他们就同时转向“自下而上的历史”,正如他们自己的西方同道那样。然而他们也像他们的西方同道一样,在他们对现代西方文化中启蒙运动的根源的评估上出现了分裂。如南狄(Ashis Nandy)就把全部近代科学思维的传统都认为是从事于确立对非西方世界的殖民与随之而来的后殖民的霸权的一场大不幸。他谴责了“历史观念与近代民族国家之间所确立的种种联系、世俗的世界观、培根式的科学理性观、19世纪的进步理论以及近几十年与多种形式的暴力、剥削相勾结的……发展”。这种世界观就取代了其他有恃于“神话、传说和史诗来界定其自身”的那类文化的世界观。南狄不是在呼唤着另一种历史,而是在呼唤着否定历史[19](P44)。另一方面,萨卡尔(Sumit Sarkar)这位领先的印度社会史家也曾一度与《次等研究》联合一道警告他的同胞们要反对毫无批判地接受萨义德(Edward Said)把焦点放在“殖民话语上,通过它,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就被认为是奠定了文化的主宰”。这一后现代的分析,按照萨卡尔的说法,“就冒有恰好是忽略了使得近代西方得以横行霸道而如此之过分地压迫别人的危险:亦即它与帝国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权力之非常具体的各种形式的联盟”。在他看来,南狄对一种和谐的、前近代的过去加以浪漫的理想化,因而忽视了传统的印度社会中的不平等和压迫。反之,他论证说:“有选择地适应于西方自由权利的话语往往会是有用的,正有如它大体上也曾确实是运用之于种性的不平等、性别中心和阶级压迫的那些问题上一样。”当承认后现代与后殖民的解构暴露了现代话语中内在的权力关系时,他还警告说要反对朝着语言学与文学的转向对于传统上的逻辑高出于修辞学的那种首要地位的颠覆作用。
最后,有关晚近的史学史的大多数著作都仍在遵循传统的路线,很少受到怀特(Hayden white)1973年所写的《元史学》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很多以西方语言所写的史学著作史的书①,然而它们大多数(也包括本书在内)都只是讲述欧洲和北美的作家,还没有关于历史学思想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有一系列的论文集探讨了个别的文化的历史②,它们都是广泛的比较方法的重要基石,但是仍然缺乏综合的认知。我们所提到的各种问题使得撰写全球史面临着历史学中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的困难。这样的一种历史仍然属于未来的规划③。
① 例如格罗斯(Mirjana Gross)《从古代到后现代——当代史学著作及其起源》(1998),贝特莱(Michael Bentley)《近代历史学》(伦敦,1999),格林(Anna Green)与特鲁普(Kathleen Troup)《历史之家:二十世纪历史学与理论批判读本》(纽约,1999),韦勒(Hans-Ulich Wehler)《二十世纪末的历史思想》(慕尼黑,2001),克莱默(Lloyd Kramer)与玛萨(Sarah Maza)《西方历史思想手册》(牛津,2002),艾巴赫(Joachim Eibach)与洛特(Ctinther Lottes)所编《历史学指南》(哥廷根,2002),凯莱(Donald Kelley)《历史的命运》(纽黑文,2003)。一部真正的全球字典是伍尔夫(Daniel Woolf)所编的《全球历史著作百科全书》两卷(纽约,1998)。
② 包括吕森(Jom Rüsen)和米塔格(Achim Mittag)所编《文化的多重性》(1998),吕森所编《西方历史思维:跨文化的辩论》(纽约,2002),福克斯(Eckhardt Fuehs)和司徒赫泰(Benedikt Stuchtey)所编《跨文化的疆界:全球透视下的历史学》(伦敦,2002),王晴佳(D.Edward Wang)与伊格尔斯所编《历史学的转折点:跨文化的透视》(罗彻斯特,2002),以及司徒赫泰(Benedikt Stuchtey)与福克斯(Eckhardt Fuchs)的《撰写世界史1800—2000》(牛津,2002)。
③ 应该提到晚近两部试图从跨文化入手的历史学规划:伍尔夫(Daniel Woolf)最近编纂的《历史著作全球大辞典》(纽约,1998)刚刚完成手稿,将刊载于即将出版的新版《思想史辞典》。与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uerfield)为前一版的《思想史辞典》(纽约,1973)撰写的历史学辞条不同,巴文除了有一短节论中国的古典学术以及有一段论卡尔多安(Ibn Khaldoun)而外,它完全是专谈西方传统的,伍尔夫则以大得多的广泛章节论述了自从远古以来各个文化的历史著作。伍尔夫最近正与一批合作者在规划一部多卷本的全球历史学的历史。他小心翼翼地在避免欧洲中心论并力图以其自身的术语来表现每一种文化。我本人和王晴佳一道目前正从事写一部自从1750年以来的寰球比较史学史,在范围上要比伍尔夫的规划更为局限一些,但更为关注欧洲渗透到大部分非西方世界的时代中,西方的与非西方的史学思想的交互影响,从而介绍了一种公开的比较观点。
参考文献:
[1]Robert Anchor.历史学家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争论[J].历史与理论,38,(1999):111—121.
[2]Chris Lorenz.构造过去:历史理论序论[M].科隆,1997.
[3] D.Faubion.人类学与历史[A].国际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百科全书[C].阿姆斯特丹,2001:519-523.
[4]William M.Reddy.人类学与文化史[A].Kloyd Kramar,Sarah Maza.西方历史学思想手册[C].伦敦,2002:277—296.
[5]Melvin Richter.政治社会概念史[M].纽约,1995.
[6]James Sheehan.政治史(政治的历史)[A].国际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百科全书[C]:11667—11673.
[7]王晴佳.“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五四运动的历史学研究[M].阿尔巴尼,2001.
[8]O.Chatterjee.低等族群史[A].国际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百科全书[C]:11237—11241.
[9]Vinay Lal.低等族群学派与印度史的升级[A].王晴佳,Georg c.Iggers.历史学的转折点:一种跨文化的观点[C].罗彻斯特,2002:237—270.
[10]杜赞奇.后殖民时代史[A].Lloyd Kramer,Sarah Maza.西方历史学思想手册[C]:417-431.
[11]K.Canning.性别史[A].国际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百科全书[C]:5929.
[12]N.Hewitt.历史中的性别与女性主义研究[A].国际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百科全书[C]:5929-5933.
[13]历史与记忆[A].国际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百科全书[C]:6822-6829.
[14]Chris Browning.普通的人们——101后备营及其在波兰的最后瓦解[M].纽约,1992.
[15]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M].纽约,1996.
[16]P.Nolte.历史的现代化与现代性[A].国际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百科全书[C]:9954-9961.
[1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新塑造[M].纽约,1996.
[18]柯斯卡.多重的现代性与协议的普遍性[A].Dominic Saehsenmaier,Jens Riedel,Shmuel N.Eisenstadt.对多重样现代性的反思:欧洲的、中国的和其它的诠释[C].莱登,2002.
[19]Ashis Nandy.历史之被遗忘的两面性[J].历史与理论,专刊34(1995):44-46.
[20]Hans-Ulrich Wehler.德意志帝国(1871—1918)[M].列明顿,1985.
[21]Jeffrey Her.魏玛与第三帝国时期反动的现代主义、技术、文化与政治[M].剑桥,1987,
[22]查克拉巴蒂.地方化的欧洲:后殖民时期的思想与历史的分歧[M].普林斯顿,2000.
[23]柯思卡.比较与比较之外[J].历史与理论,42,(2003):39-44.
[24]Chris Lorenz.比较历史学:问题与前景[J].历史与理论,38,(1999):25-39.
[25]萨卡尔.后现代主义与历史著作[J].历史研究(新德里),15,2,n.s.(1999):293-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