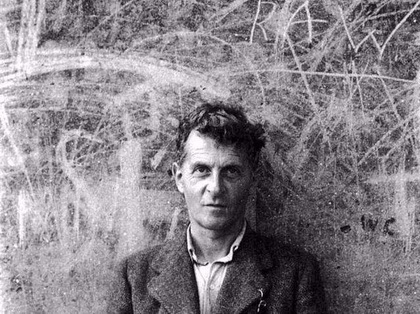作者:基克弗里德·罗姆巴赫
作为时间化的对象构造与存在筹划
——论胡塞尔对象类型的时间构造
与海德格尔存在样式的时间筹划[1]
[德国]基克弗里德·罗姆巴赫(Siegfried Rombach)
(王鸿赫 译/陈志远 校)
不论对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者之领会境域,还是对于胡塞尔的对象构造来说,时间都起着核心作用。本文将就此实事关联进行研究,探讨现象学中这两种奠基性哲学纲领之间的关系。尽管这里存在着实事上的相近和体系上的相似,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本人却并未明确指出要参看对方。
第一部分将展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即按照时间化的各种特定方式来区分存在的不同样式。第二部分将表明,胡塞尔对这种复合体所做的分析可能对海德格尔有所启发。接下来的第三部分则将描述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和1906/07年的讲座《逻辑学与认识论引论》[2]中所进行的开端性研究。最后的第四部分将阐释胡塞尔在《论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1917/18)》[3]中对此论题所做的细致分析。
在内容基本起点上的相似和两位思想家间的历史联系指明了胡塞尔在这方面对海德格尔的影响。更细致的考察将会表明,胡塞尔对对象类型的各种特定时间化方式所做的分析,比海德格尔更加具体详细,后者更多的是在强调基本思想的普遍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对此在以及上手事物(或宽泛意义上的现成事物)的时间化方式进行制定。
一、海德格尔关于存在样式之时间化的基本思想
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问题上, 1927年出版的马丁·海德格尔的开创性著作《存在与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被公认为现象研究活动中的独立新起点。在方法上,通过非反思且反理论性的诠释学式的此在现象学,海德格尔脱离了胡塞尔反思性的超越论式的意识现象学。
对于早期海德格尔来说,哲学的终极论题是“从此在的诠释学出发的普遍的现象学存在论”(SuZ, 38)[4]。这种普遍的现象学存在论受到这样一个主导思想的支撑,即存在的一般意义就是时间本身,因而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只有基于时间才能被领会。此外,海德格尔还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各种存在方式或存在区域,即所谓的存在样式(也被其称作存在模式,存在方式或存在特征),是通过不同时间性的或时间状态上的规定和区分产生的。海德格尔在1925年夏季学期的讲座《时间概念的历史引论》中这样论述到:“时间是区分划定一般存在领域的一种‘索引(Index)’。时间概念阐明了对存在者普遍领域进行划分的样式和可能性。依据其发展等级,时间概念指引着如何解答存在者之存在及其诸可能区域的疑问,并且它的这一作用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明确认识 [...]”(GA 20, 8)[5]
随着讲座的进一步深入,海德格尔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这一问题:“究竟是什么赋予了时间和时间概念[…]这种资格?使它具有目前为止仍被视为不言自明的特有功能,即,区分并刻划诸现实领域——时间性的、非时间性的、超时间性的现实。”(GA 20, 8)在之前的一段中,海德格尔举了一些对诸实在领域进行特定时间构形的例子:“完全就其外在而言,历史和自然界是时间性的。人们常常将这种时间性的全体现实与非时间性的持存(Bestaende)对置起来,例如数学的研究课题就属于后者。除了数学这种非时间性的持存,人们还知道形而上学或永恒性神学的超时间性的持存。”(GA 20, 7)
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海德格尔本人区分了六种基本存在样式:
1. 生存,指作为此在之存在的存在样式,即我们作为人这种存在者自身向来所是的此在。
2. 共同此在,指作为同样以此在方式存在着的他人之存在的存在样式。
3. 存活,指动植物这种不以此在方式活着的存在者的存在样式。
4. 现成状态(狭义),所有物理的和无机的自然之物都属于这种存在样式,例如石头。[6]
5. 上手状态,指海德格尔发现的所谓用具的存在样式。[7]
6. 持存,观念对象属于此种存在样式,也就是说由逻辑判断或数学定理所表达的一般性事态或观念性事态。
在《存在与时间》的另一处,海德格尔又将实在性作为一种存在样式与上手状态和现成状态并列在一起,尽管前者与现成状态在概念上有所交叉。(SuZ, 230) 因此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并不想用上述六种存在样式(生存,共同此在,存活,现成状态,上手状态和持存)囊括所有可能的存在之样式。他也不想用那些已被命名的存在样式,提供一幅终极有效且成体系的存在样式之图示。
例如一件只有从美学角度才能被领会的风景画或艺术品,按其本质难以归入已命名的六种存在样式。艺术品和风景画既不属于现成状态或上手状态,也不属于存活或持存的存在样式。艺术品以及诸如伦常价值领域,皆形成其特有的存在区域。但笔者不想在此进一步探讨如何使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样式完备化。
让我们回到海德格尔自己提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赋予了时间和时间概念[…]区分诸实在领域的权能”,即区分诸相互关联的存在样式?海德格尔仅针对两种存在样式来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第二篇只对生存这一存在样式进行了时间性阐释。这里必须严格指出,海德格尔并未完成自己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在澄清存在之意义的基础上重新阐释生存存在样式的要求。
按照《存在与时间》第八节所展示的“论文纲要”,未发表的《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第三篇的标题为“时间与存在”,在此篇中海德格尔试图指出,存在之意义究竟是如何基于时间才能被领会的,并同时阐明诸存在样式如何通过其各自时间性的或时间状态上的规定而彼此得到区分,以及条理清晰地指明时间如何作为诸存在样式的界限(discrimen)起作用。“根据一则笔记的记载”[8],《存在与时间》(已于1927年1月发表)第一部分第三篇的提纲已被海德格尔销毁,由此有关从时间状态上区分诸存在样式的论述,需要参阅海德格尔1927年夏季学期在马堡的讲座《现象学基本问题》,因为这个讲座被视为对《存在与时间》第三篇做出的第二次新近修订,它绕着存在论历史的曲折之路,向作为存在之一般意义的时间推进。他在讲座中示范性地对上手状态以及同时广义上的现成状态做了时间状态上的阐释。[9]
海德格尔将上手状态存在样式在对存在者进行筹划时所依据的时间状态上的境域称为现前(Praesenz)或在场(Anwesenheit)。尽管海德格尔为每种存在样式都指定了一种存在领会在时间状态上的特定境域,但即使在《存在与时间》以外,在其全集中除了对此在的时间性以及上手事物(或现成事物)的时间状态进行制定修缮外,找不到针对其它存在样式的进一步具体的时间状态之阐释。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可以指明时间如何从存在论上规定其它存在样式的依据和提示。例如可以从1929/30年冬季学期的讲座《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GA 29/30)中获知一种属于存活存在样式的动物的存在论:石头是没有世界的。动物则缺乏世界,其存在方式是蒙昧的,它对存在和世界的领会被蒙蔽了。相反,人构建世界。如前文所述,持存这一存在样式一方面具有非时间性特征,如数学定理,另一方面具有超时性特征,如形而上学和神学的洞见。然而一种具体的、就像在《现象学基本问题》中对上手状态所做的那种时间状态阐释,在海德格尔全集中再未出现。[10]
依据《存在与时间》双重的结构主线,我们简要归纳一下海德格尔自己所做的阐释:
(a) 存在只有基于时间才能被领会。
(b) 时间是区分诸存在样式的“界限”。
在一些段落中,海德格尔宣称康德是在他之前“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着手这一课题时基于时间来领会存在的人。例如在《存在与时间》的导论中可以读到:“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研究道路上朝时间状态这一向度探索过一程的人,或者说自己被现象自身所迫而走上这条道路的人,是康德。”(SuZ, 23)
二、海德格尔可能受到过胡塞尔的启发
但与海德格尔的看法相反,事实很清楚地表明——本文的论题由此出发——康德并非将研究课题朝这一向度(即基于时间来阐释存在)推进的唯一一人,因为在胡塞尔那里也可以找到这一方向上的研究。确切地说,这方面细致阐述的出现远远早于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尤其是有关通过每一具体的时间构造来区分诸对象区域或对象类型的阐述;这些阐述主要集中在不久前作为胡塞尔全集第三十三卷[11]出版的通常所说的1917/18年贝尔瑙手稿中,这份手稿也部分收录和发表于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Ludwig Landgrebe)修订的《经验与判断》(1939)[12]。在胡塞尔1920/21年冬季学期在弗莱堡第一次举办的讲座“超越论逻辑学”中,同样也显示出了这一方向上的种种趋向,兰德格雷贝将其中的有关段落与贝尔瑙手稿中的有关段落在《经验与判断》中的一章中进行了嫁接。[13]1920/21年冬季学期讲座中的这些至关重要的段落在胡塞尔全集第三十一卷中,作为《被动综合分析(1918-1926)》[14]的增补卷,以标题《主动综合:1920/21年的讲座“超越论逻辑学”》按其结构原貌于2000年首次出版。
胡塞尔这些真正的开端之举在时间上不仅早于海德格尔在其第一本著作《存在与时间》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而且也早于海德格尔在其讲座中对该论题所做的首次探讨。海德格尔在其1923年弗莱堡夏季学期讲座《存在论(实际性的诠释学)》(GA 63)中首次谈到了该论题,这个讲座也标志着他开始起草《存在与时间》。在讲座中,海德格尔将生活(Leben)(即后来的生存)存在样式与在世界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样式区别开来。
海德格尔一方面无保留地断言,康德是唯一一个在研究课题上追随这一思想轨迹的人;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却又翻阅过胡塞尔的研究手稿,在其不同的手稿(当然也包括贝尔瑙时间手稿)中,可以找到对存在构造进行时间阐释的确切开端,而且首先是那些通过时间性来区分诸存在区域的研究文稿。最迟也从1919年开始,直到1923年海德格尔去马堡任教,在此期间他与胡塞尔有着频繁的思想交流,并同时得以接触胡塞尔的研究手稿。因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七节(即所谓的方法一节)的一个脚注中这样说到:“如果下面的探索能在‘实事本身’的开展方面前进几步,那么笔者首先要感谢胡塞尔。笔者在弗莱堡助教时期,胡塞尔曾亲自给予笔者以深入指导并允许笔者极其自由地阅读他尚未发表的研究文稿,从而使笔者得以熟悉至为多样化的现象学研究领域。”(SuZ, 38)
一如我们所熟悉的海德格尔自己的说法,即他从胡塞尔那里获得了发展自己现象学哲学的方法上的技能。此外也不难看出,海德格尔从胡塞尔那里也找到甚至获取了内容上的启示、入门、乃至洞见,触发他制定出了自己的存在课题,这从至此所展示的原始材料总的来看并不是不可能的。虽然海德格尔在《我进入现象学之路》[15]一文中提到:《逻辑研究》中“所强调的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之间的区别,从其用于规定‘存在者的多重含义’这一作用方面向我显露了出来”,然而当他表述“基于时间来领会不同的存在样式”这一其核心基本思想时,他没有再在什么地方提及过胡塞尔。完全相反,康德却一再被他明确(expressis verbis)称为“唯一”一位在这个课题上有点作为的人。
海德格尔在其1925年夏季学期的讲座中论述说,胡塞尔对纯粹意识做出了四条存在规定:⑴纯粹意识是内在的存在,⑵它是绝对被给予的存在,⑶它在“不需要任何东西就可存在”(nulla re indiget ad existendum)的意义上是绝对的,⑷纯粹意识是体验的观念性存在这一意义上的本质存在(参阅GA 20, 141 f.)。在所有这些规定之外,至少还可以向海德格尔提出下面这样一个问题:纯粹意识作为一种由时间形式所规定的根本且原初的存在,在胡塞尔的全部著作中俯拾皆是并且一再得到刻画,但对这种纯粹意识的规定究竟哪去了?为什么海德格尔偏偏不提意识的时间性?对意识的这种规定在胡塞尔那里可是不容忽视的。海德格尔对此中关联秘而不宣的动机何在?这更多地是个历史性的问题,对它的解答几乎也只能靠猜测了。[16]尽管如此,还是值得在海德格尔式基本出发点的衬托下,在体系-内容的层面来进一步衡量胡塞尔的研究出发点。
胡塞尔有关意识中对象世界的构造学说,最终可以回溯到作为其最原初规定的一切意识的时间状态上来,并且,正如下文所要显示的,它也回溯到对象或存在区域的各个样式或类型所特有的时间构造上来。由此可以表明,诸如将时间视为对象类型或存在区域的“界限”这种思想模式在胡塞尔那里已经出现。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阐述到:“时间意识是构造一般同一性之统一体的策源地。但它只是一种产生某种普遍形式的意识。”(EU, 75 f.)“所以,这种原初地构造起来的时间伸展到多远,一种可能对象性的原初地和感性地(就是说被动地、先于一切主动性地)构造起来的统一性也伸展到多远[…]”(EU, 182)但在此需要注意,时间不仅标示出内意识的形式,也标示着反思可把握的内在意识对象的形式,即意向体验的形式和感觉的形式。甚至所有被超越地意指的对象性也以其各自特有的方式得到时间构造,或者与时间有其各自特定的关联。
由此,对对象的意指或直观根据其各自所属的存在区域,可以被视为它们在时间中各自所特有的一种构形,因而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时间化。胡塞尔基本上命名了下列对象类型或存在区域:实在的、个体的对象与观念的、普遍的对象。
在进一步深入阐述贝尔瑙时间手稿中与此有关的段落之前,先简要展示一下《逻辑研究》与1906/07年冬季学期讲座《逻辑学与认识论引论》中,按照时间构形来区分诸对象类型的那些最初的依据。
三、《逻辑研究》与1906/07年讲座
《逻辑学与认识论引论》中的对象类型和时间类型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1900/01)第一版就已将实在存在与观念存在之间的区别回溯到了时间上,他这样写到:“对我们来说,时间性足以成为实在性的特征标志。[…] 因为这里所涉及到的唯一一个问题恰恰在于:观念之物的非时间性‘存在’的对立面。”(Hua XIX, 129)[17]胡塞尔在此逐字叙述到,“存在的意义”在实在存在与观念存在那里“并非特别相同”。(Hua XIX, 130)
按照《逻辑研究》的理解,实在存在者是在时间中构造起来的,观念存在者不是在时间中构造起来的。非时间性存在的意义属于这种观念存在。胡塞尔在1905年《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45中也论述过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同的区分。(参阅Hua X, 96 ff.)
胡塞尔在其讲座《逻辑学与认识论引论》(1906/07)中首先解释到:“所有客体化行为都在时间意识中进行[…]”(Hua XXIV, 264),随后在此讲座的后文中,为了给出意向相关项方面更细致的阐述和充实,他进一步论述到:“时间不是意识的一种形式,而是每一种可能客体性的形式,并且只要内容可以作为感知中的对象以及其它客体化行为中的对象构造起自身,这些内容便具有时间。”(Hua XXIV, 273)胡塞尔在讲座中以作为同一观念意义的定理为例,区分了实在存在与观念存在。他将超时性特征归于观念存在。为此他所要指出的是,与它在各种具体体验中各式各样可重复的对象化或现时化相比,定理在逻辑-观念的意义上是一种同一之物。“它有所意指,但它所意指的东西并不会伴随对其的表达以及反复进行的领会和信仰而增多,相反,它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同一之物。”(Hua XXIV, 37)胡塞尔意义上的定理完全意味着一种在本体论的框架内进行考察的实体,他在上述文段中明确表述到:“[…]定理本身是某种有其自身特性的存在者。它并非某个东西,也不是实在之物,但却是某种存在者。[…]甚至观念对象也具有其实存与非实存。”(Hua XXIV, 38)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以及《内时间意识讲座》中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见解,即首先以时间中的存在者这层意义来规定实在对象,其次,将观念存在刻画为一种非时间性存在者。之后在提到过的1906/07年讲座中,他又探讨了超时性存在者的对象区域。
在由埃迪‧施泰因(Edith Stein)修订的1917年的论文《对T.埃尔森汉斯和A.迈塞尔的批评》(“Zur Kritik an Theodor Elsenhans und August Messer”)中,胡塞尔写到:“我们有两种实存的客体,以及两种与此相关本原地给予着的意识:在感性感知中构造起来的自然和理论思维中的范畴(或逻辑)对象。我们在此所揭示的这两种对象领域当然无法涵盖存在者的全部领域。还有多种多样的客体,它们既非自然之物也非思维对象(比如我想到了价值,财富等诸如此类的),以及相应地多种多样给予着的意识,既非感性感知也非思维。”(Hua XXV, 243f.)
依据胡塞尔的这种说法,价值和财富扩充了可能的对象类型。同样,除了实在对象和观念对象,胡塞尔还向人们介绍了文化客体这种对象类型。一如我们从《观念II》所获知的,胡塞尔根据分层模式(Schichtenmodell)来阐释他所谓的文化客体。胡塞尔在1925年的讲座《现象学的心理学》中写到,每一个文化客体都是一种“实在,这种实在于自身中合乎表达地承载着一个精神意义”。(Hua IX, 113)“这个意义使这个实在成为文化客体,这个意义当然也涉及到时间,并且我们以某种方式也可以在它那里谈论某种延续。可是在文化客体这里我们找不到什么可以用来说明这个延续的可变状态,也找不到伴随延展着的时间充盈材料而发生的它所特有的时间延展,文化客体的同一性中没有任何可能的变化或不变化。” (Hua IX, 116)因此,在构造过程中,文化客体不仅证明是感性被给予性上观念意义的叠加,而且在意向相关项上,实在存在与观念存在之间的关联保持为一种奠基关系。
借助此处所运用的《观念II》中的分层模式,从根本上看并没有得出什么真正的新的存在区域,与生物界和精神世界的存在方式类似,在构造方式上,文化客体的存在方式由作为前设存在领域的实在之物与观念之物的奠基关联交织而成并由之导出。
处在人格自我的建构最底层的是实在意义上的物质自然,在其上建构起的是生物界层次,最后是精神世界层次。以此为例,新的对象类型(如人的人格)得以成为课题,但它们原初固有的存在意义(一个转向,胡塞尔本人也依托这一转向)却仍隐匿着,这并非由于胡塞尔的疏忽,而是因为存在意义不能从实在与观念这两种前设性的存在方式中近乎成型地构造起来。
亦如上文探讨海德格尔时的情况,本节止于至此所给出的分析概要。至于对胡塞尔本原的存在样式或对象类型加以完善并系统统一化,有关这方面的进一步论述留待其它地方进行。
比照海德格尔对上手状态和现成状态存在样式所制定的时间构形,下面将示范性地阐明存在样式在胡塞尔那里的时间构形。
四、贝尔瑙时间手稿中对象类型的时间构造
带着这个目的,我们将专注于贝尔瑙时间手稿中实在对象的时间构造有别于观念对象之构造的分析。
时间意识的构造分析严格地遵循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之间的这种先天关联。因此在客观时间中发生的事情不可与“被给予方式的‘河流’”相混淆,“在这些被给予方式中,每个时间之物都向主体‘显现’。”(Hua XXXIII, 183)无疑,胡塞尔在贝尔瑙手稿中明确提出:“我们始终或者确切地说是必需进行这样一种两分:存在本身与这种客观存在的诸多被给予性样式。这些被给予性样式更迭不固定,但却是先天固有地形成的。”随着研究的进一步进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具有某种相似,他自问到:“那些时间样式都标示实存样式吗[…]?当我们从(一如在本质把握中)涉及本质的信仰转向对个体存在的信仰时,一般信仰发生了分化吗?此在是一种与本质存在相并列的实存样式吗?即使在这里难道人们也不能谈论什么具体的差别吗?就好像实存这个属(Gattung)分化为本质存在(Wesens-Sein)、如是存在(Dass-Sein)和向来如此(was immer sonst)一样。”(Hua XXXIII, 296)但“本质意识具有一种不同于此在意识的更复杂的结构[…]”(Hua XXXIII, 297)
每一个意识体验都是在内在的、现象学的时间中进行的。但这与朝向对象的各个意识体验具有什么类型的意向对象性无关。实在对象和观念对象是在时间上延续着的意识体验中被给予的,它们发生在总体关联(即所有体验之河流或体验流)中一个可在内在时间中确定的位置上。鉴于其在意向体验中的被给予性,所有的对象类型由作为体验构形的时间的被给予性样式所决定。诸实在对象具有个体性客体的特点。它们的个体性是从时间位置的一次性和时间中与此相关的延续中得到的。对于实在对象来说是客观的超越时间,对于意向体验及其因素来说是内在时间或现象学时间。与被给予方式的杂多性不同,通过时间的个体化,即通过上面提到的时间位置的一次性,可以达到超越实在对象的客观对象同一性,这是它们的本质结构所具有的。[18]
观念对象合乎意识的构造同样也在内在时间中进行,但与实在对象相比,观念对象并非处于客观时间中的个体性客体。它们的普遍性结构表明其存在方式并未束缚于某一确定的时间位置,此外它们还表明,不可能通过一维时间序列中的编排来建立伴随着观念对象的被意指之意义的同一性。[19]
胡塞尔将给出对象的体验所具有的这种内在时间也称作被给予性时间,以区别于在体验中被意指的对象性统一体所具有的在意向相关项上被定性的时间,为区别起见,他称后者为本质时间。胡塞尔在此造的这个术语“本质时间”在我看来有点选择不当,因为这个术语易引起误解,即本质时间也指涉一般本质的时间。但这个概念所指的是被构造的对象的时间,它作为客观的但不必是超越的时间中的客观统一体与被给予性时间相对立,后者是进行给予的体验所具有的时间。人们可能会由此受到蛊惑,索性将这种具有对象性意义的时间命名为“对象时间”。但这个概念性表达也会导致一个严重的误解。因为与被给予性时间相反,“本质时间”这个术语本真的解释进路在于与时间的关联所具有的含义,即这种关联是在本质上为各自对象类型所拥有。例如,实在对象的本质时间并不是指它们各自具体的、在个体层面得以规定的客观自然时间中的编排,而是对于实在对象来说,“本质时间”这个术语表示这样一种本质明察,即所有的实在对象本质上在客观时间中都有其位置和延展。因而本质时间这一表述也可用于描述意向相关项上的实在对象的时间化,不仅如此,正如人们所意指的,它同样也可用于描述意向相关项上的观念对象的时间化。这个提示值得注意,因为伴随本质时间,胡塞尔(Hua XXXIII, 316-317)在此同时还使用了本质,本质对象和本质形式,但这些术语只能用于观念对象。
对于实在对象而言,被给予性时间与本质时间的时间形式在结构上一致。这并不是说,被给予性时间和本质时间在此是同一种时间形式。感性感知(比如对一个房子的感知)作为意向体验发生在时间中。我的这一感知体验拥有其一次性且确定的时间位置,以及超出这些一次性且确定的时间位置的时间延续。同样,这个作为超越对象而显现的房子也在由前后相继的固定时间位置所形成的一维序列中得以定位。除了时间形式在结构上的这种相同性,还需要强调指出实在对象被编排进其中的自然时间或世界时间与体验的内在时间之间的区别,只要后者不要被误解为心理学上的实在事件。尽管一个房子通常在我们感知的前后在客观自然时间中延续着或确切地说是继续延续着,而且对房子的感性感知的延续与房子本身的延续并非全然一致,但当对房子以及一切实在对象进行感知时,体验的被给予性时间与对象的本质时间虽然形式上不同一,具体延续上也非全然一致,但却具有相同的性质结构。即使双方的延续真的达到了全然一致,也仅表明了感觉的被给予性。严格地说,在它们那里被给予性时间和本质时间根本没什么区别。[20]但我们首先将注意力只锁定在超越的实在对象上。它们处于且行进在自然时间中,在由客观的现在、先前和稍后所构成的必然演替的、一维的、不可逆的、因而也是一次性的时间形式中。对于这种对象类型而言,客观时间中的这种编排是“对象性本身的一种结构性因素”。(同上,316)
恰恰是被给予性时间与本质时间结构上的一致使得观念对象缺失。“时间[…]虽是一种形式,它们[即观念对象]在时间中得到把握,但却不是这样的形式,即没有包括观念对象的任何构造性[即意向相关项上的]特征或任何本质部分。”[21](同上)由此可见,对观念对象在客观的、超越的时间中所进行的编排都不属于观念对象的对象意义。因而胡塞尔在贝尔瑙时间手稿中也将观念对象称为“超时性对象。[…]它在时间中‘偶然’——κατα σψμβεβεκοσ(凭运气)——出现,只要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作为同一对象而‘出现’。”(同上,321)然而这种“超时性并不是说与时间没有关系,而是它们[我们在此统称为观念对象的本质对象和普遍事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本原地[着重系笔者所加]被构造起来,[…]这样不同时间状态中的被构造者都是同一的,这些都属于它们的本质。”(同上)虽然观念实体在时间中创生的体验中成为对象,但它们意向相关项方面的观念之本质,即它们必不可少的对象之构形并不会留下这种时间印迹。胡塞尔是如何理解观念对象与时间之间这种被指定的联系呢?他说到:“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本原地[着重系笔者所加]被构造起来[…]”(同上)是否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它们与时间的联系是通过体验获得的,在体验中的任一时刻它们都可以被构造起来?是什么致使这次在体验中构造出一个实在统一体,另一次又构造出一个观念统一体?从在时间中创生的构造体验所具有的不同成就出发,才能理解超时性的意义。
意向对象出现于其中的时间体验不仅具有“自身必备的内在时间形式,而且它们以某种方式在其意向对象上留下了某种时间形式,即作为其被给予方式的意向相关项的样式。”(同上,319)对于实在对象来说,这表明:“内在的素材材料被立义或统摄为超越地被意指的客观对象的被代现者,其时间形式同样被一同统摄为同属于意向对象的客观时间形式。
与实在对象不同,在观念对象那里并未发生这种统摄性的对时间形式的赋予。观念对象是在更高一级的行为中构造起来的。它们直接建立在感性行为或其它更高一级行为的基础上,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对象性。为了更好地理解可以参看观念直观的抽象和范畴直观。在主动(自发)综合中,观念对象在奠基性行为的基础上被构造为意识统一体,这样它们同一性的获得就与它们出现于其中的个别时间无关。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作为同一相同对象本原地得到把握。胡塞尔在其1920/21年的讲座《超越论逻辑学》中,造了“全时性”[22]这个词来表述这种时间形式,即在任何时候或全部时间都可以将观念对象把握为全然同一的。“全时性”[23]这个术语是对同一现象所做出的更准确的表述,同时它还可避免引起柏拉图唯心主义的误解,同一现象在贝尔瑙时间手稿中被称为“超时性”[24]。
至此,人们不难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实在对象不是也可以作为同一相同之物——在再回忆或想象,甚至可以是任何时候——反复出现吗?对此必须反驳说,胡塞尔在一些论述超时性或确切地说全时性的重要位置,不怎么引人注意地引入了本原性这个概念作为把握对象的标准。事实上,可以自发地,即主动地构造起来的观念对象与实在对象不同,其不同仅在于观念对象可在任何时候都本原地得到把握。它们可以不依赖于具体的感性被给予物,在处于内在时间中的再回忆内容和想象内容的基础上,本原地被直观到。这当然不适用于实在对象,虽然实在对象任何时候都可以在当下化行为中得到再造,但在其中它们却不是本原地被直观到。
胡塞尔的这个构想暂时看来清楚明白,但似乎仍牵涉到一个并非完全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以“毕达哥拉斯定理”作为观念对象的一个例子,它的构造需要主动的,受自我性引导的综合。如果这些综合得到正确的实行,那么伴随毕达哥拉斯定理而被意指的意义就会成为意识的客体。如果这种主动综合不符合被定义的数学意义,那么毕达哥拉斯定理并非以某种不完善的形式,以有缺陷地或错误地被思考的定理而出现,而是它根本就不出现。对观念对象的把握不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即在一种更加清晰明确的把握与一种不那么清晰明确的把握之间不存在差别;在对观念对象的再回忆,想象和本原表象之间也不存在差别。确切地说,毕达哥拉斯定理要么在其直观的客体化中现时地产生,要么就完全没有在直观上被给予。构造的进程在此总是具有一个可以或已经得到完成的形态,它的确必须得到完成,只要观念对象被给予。对此,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阐述到:“[…]自我并不像在相反的情况下那样可以使这个过程在随意的一个点上中断,那样一来,它就不会具有这种知性的对象性了。”[25]与此相比,实在对象却按其本质显示出一种渐进的直观性。这种直观性的等级着实属于实在对象最内在的本质,并且遵照透视法而进行的映射所得到的现象无非意味着,实在对象从来不能全然相即地被直观化。这种“普遍的可规定性”——为了运用康德的转向——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不仅受到视角的无穷性与规定的无限性的阻碍,而且还受到这样一种不可能性的阻碍,即无法在某个当下用一个更高级的综合囊括进各个综合。
还应对胡塞尔的观念对象之超时性或全时性的构想进行详尽补充,这种补充可以从对本原性的分析中得到,这种本原性在全部时间都能被把握到。准确地说,本原性表明了被给予性中的一种同一性,即不能对这种被给予性的任何方面再精细化或使之进一步完善。从这种完善的、数的同一性出发——不仅在被意指状态方面,也在直观被给予状态方面——有可能推出一种与胡塞尔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实在对象的同一性形式。这样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无疑自为存在着的实在对象(它们对其蕴含着实事的同一性的拥有,并不受在时间位置序列中所进行的编排的影响)首先通过客观时间中的编排而获得了它们的个体化,这是因为按其本质它们决不可能通过一种彻底得到完成的、直观的、亦即相即的构造而被统一为一种数的同一性。观念对象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它们决不可能具有实在对象的那种状态,我们也可将这种状态称为永远开敞的(semper apertum)(在决不可能得到完成并且总是片面地被给予状态的意义上,以及对新的或变更着的映射总保持开放状态的意义上)。观念对象产生但并不消逝,延续但并无变化。胡塞尔因而将它们这种主动的生成称为“发现”。它们一旦被发现,便获得了与其意义相称的永久性存在,而且先于具体意识中历史上对其首次进行的主动构造。观念对象的时间形式的另一层意义就在于此,但胡塞尔未能从现象学上对此予以补充。全时性作为一种我“随时都能本原地进行把握”的时间形式,也包含一种作为自在的超时性存在的被意指状态,“在全部时间都可以进行把握”作为一种意向活动的进行,对其的领会被限定在恒久(sempiternitas)(即永久的,在时间中随时都有可能)[26]意义上的“任何时候”这种方式上,其中被客体化了的内容的超时性自在持存着,这样在其意向相关项方面,似乎唤起了一种永恒(即超越一切时间的存在者,根本不能通过时间来规定)意义上的领会。因而胡塞尔依据时间样式的性质也将超时性作为全时性来强调,但意向相关项视线下的“永久”和“在任何时候、在全部时间”究竟应如何理解还悬而未决,如果这种理解最终维系于进行意向活动的这种全时可能性。
如果现象学构造所揭示的时间个体与全时对象之间的区别,是由原则上决不可能得到完成的构造(实在对象)与原则上总是已经完成了的构造(观念对象)之间的本质区别引起的,那么意向相关项的时间构形将从中再次获得进一步的意义。由于一次性的原初意义得到了揭示,从其中——与胡塞尔再次截然相反——可以导出客观时间位置的一次性,这种一次性将更原初的同一性形式经过变异传给了现在。为了点明这种时间形式的变异所产生的可能影响,接下来应对人的而非自然对象的一次性时间特征进行规定。
这些批评性注解仅想表明,胡塞尔关于观念对象和实在对象存在方式的构想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其基本思想的支持,从而可以通过它们意向相关项上的各种时间结构来区分不同对象类型构造的同一性综合。此外还想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应进一步发展胡塞尔时间现象学中的基本思想,并将例如人这种存在样式也囊括进去。
总而言之,在存在者的存在这条道路上,除了探究内容层次上的“何所内容”(Was-gehalt),即本质(essentia)外,康德和海德格尔还探究了不同的时间实存(existentia)方式。不只是他俩如此,胡塞尔也为研究此中关联投入了大量精力。甚至很有可能胡塞尔先于海德格尔认识到这种可能性,即通过不同的时间构形来领会存在的各种样式。胡塞尔不是像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那样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这种形而上学将终极且永恒的存在的二元性进行对置;而胡塞尔是基于意识中的时间构造来揭示存在在时间状态上的区分的。胡塞尔和早期海德格尔在这方面有着值得思考的相似之处,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样式的时间构形最终源于一种实行活动,即源于此在的绽开-境域筹划。
[1] 本文起初是2001年10月27日在科隆大学“2001胡塞尔工作日”所作的一篇报告,刊登于此的文本略有改动和缩减。
[2] Hua XXIV. 下文将用Hua表示胡塞尔全集并标明卷数,若有必要也会给出页码。
[3] Hua XXXIII.
[4]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第15版,图宾根1979,第38页。下文将用SuZ简称此书并给出页码。中译本: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第45页(中译文根据德文原文有改动)
[5] 马丁‧海德格尔,全集本第20卷,第8页。下文将用GA表示全集本并给出卷数与页码。此处及后文中的方括号系本文作者所加。
[6] 只要存在者被此在相应的行为活动限制在纯粹的现成存在上,广义的现成状态就也包括其它存在样式的存在者。
[7] 因此海德格尔所指的不仅包括人工制品和工具,也包括具有因缘联系的所有工具式的东西(Zeughafte),如一块用于镇纸的石头。
[8] 参阅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海尔曼(Friedrich-Wilhelm v. Herrmann),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基本问题〉:关于〈存在与时间〉的“第二部分”》,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91, 第17页及以下
[9] 参阅GA 24, §§20和21
[10] 本文的目的并非在于追问为什么海德格尔没有完成此项工作,抑或追问他的这项工作是否根本就是失败的。
[11] 埃德蒙德‧胡塞尔,《论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1917/18)》,R.贝耐特 (R. Bernet)和D.洛玛 (D. Lohmar)编,道特莱希/波士顿/伦敦 2001
[12] 埃德蒙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 Erfahrung und Urteil.Untersuchungen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L.兰德格雷贝编订,第6版,汉堡1985. 下文将用EU简称此书并给出页码。中译本: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中译文根据德文原文略有改动)
[13] 参阅迪特·洛玛( Dieter Lohmar), “胡塞尔《经验与判断》一书的产生和原始资料”(“Zu der Entstehung und den Ausgangsmaterialien von Edmund Husserls Werk Erfahrung und Urteil”), 载于《胡塞尔研究》( Husserl Studies)第13辑,道特莱希/波士顿/伦敦1996, 第31-71页。从这项在其它一些方面同样也富于启发的研究中可以得知,此处及下文中所给出的《经验与判断》中的诸段落皆源于贝尔瑙时间手稿。
[14] Hua XI.
[15] 马丁‧海德格尔,《我进入现象学之路》,载于《面向思的事情》,图宾根1969,第82页。中译文:陈小文译,载于《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1285页(中译文根据德文原文略有改动)。
[16] 参阅D. O. 达尔斯托姆(D. O. Dahlstrom)令人信服的阐述,载于《逻辑成见:海德格尔早期真理理论研究》,维也纳 1994,第124-127页。达尔斯托姆通过再现胡塞尔与海德格尔1917-1926年间史料文本上的相通之处,有力地反驳了R.贝耐特的观点,即“海德格尔本人对时间之领会的形成受到了胡塞尔时间意识现象学的直接影响,这种看法几乎可以不予考虑”(R.贝耐特,《有关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文本1893-1909》,汉堡 1985,第LX页)。尽管贝耐特和达尔斯托姆都没能为自己的见解提供无懈可击的论证,但我们还是觉得达尔斯托姆的立场合乎实际,即海德格尔对时间的领会极可能受到胡塞尔的影响。达尔斯托姆在其论述中援引了托马斯‧普鲁菲尔(Thomas Prufer)的一篇论文:《早期及晚期的海德格尔与阿奎那》,载于《胡塞尔与现象学传统》,R. 索科罗夫斯基(R. Sokolowski) 编,华盛顿D. C. 1989. 但普鲁菲尔对“海德格尔的缄默”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超出了史实的可确证范围。
[17] 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修订本)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140页——译者
[18] 一如前文的闭口不谈,我们在此对作为第二性“个体化原则”的空间不予考虑。
[19] 有关实在对象和观念对象同一性综合的不同样式的论述,请参阅D. 洛玛《论数学中的时间:数学对象的超时性、全时性还是非时性》( “Ueber die Zeit in der Mathematik: Ueberzeitlichkeit, Allzeitlichkeit oder Unzeitlichkeit der mathematischen Gegenstaende”), 载于《年代,现象学杂志》( Alter, Revue de phénoménologie), 1993年第一期,第403-421页,此处:第414页及以下
[20] 参阅Hua XXXIII, 第317页
[21] 可以参阅“分层模式:实在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精神层”或“表述与含义”
[22] 参阅Hua XXXI, 第31页及以下:“超时性即指全时性[…],全时性是时间的一种样式。”
[23] 关于全时性的构造请参阅克劳斯‧黑尔德(Klaus Held)《活的当下》,海牙 1966,第49-57页,以及D. 洛玛《论数学中的时间:数学对象的超时性、全时性还是非时性》,载于《年代,现象学杂志》,1993年第一期,第403-421页
[24] 在其生前发表的著作,如《笛卡尔式沉思》中也有这样的论述:“此外为了解决所谓观念对象性这种特定意义上的、自身中最重要的超越论问题。它们的超时性表明自身是全时性的,是在每一个任意的时间位置上都能任意生成并一再生成的相关物。”(Hua I, 第155页及以下)也可参阅迪特·洛玛(同上,1993)编撰的胡塞尔富有启发性的已出著作中的出处。除了《逻辑研究》和《经验与判断》,洛玛还提到了《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现象学》(Hua VI, 第172页),以及《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学》(Hua XVII, 第162页及以下,第166页及以下,第172页)
[25] 《经验与判断》,第302页。中译本: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第295页
[26] 恒久作为内时间中无止尽的延续,永恒(aeternitas)作为存在于超时性中的当下,有关这两者之间的区分请参阅奥古斯丁《忏悔录》,第7-1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