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 Tri Repetae
Autechre

1995: 1000 Fragments
Ryoji Ikeda
池田良治


1997 : Come to Daddy. Aphex Twin
Chris Cunningham
克里斯·坎宁安

1992 : Helikopter Streichquartett
Stockhausen
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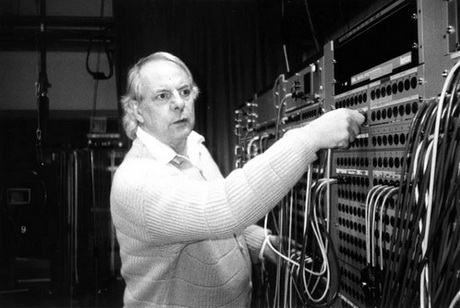
注:图片及翻译信息部分来自网络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1995 : Tri Repetae
Autechre

1995: 1000 Fragments
Ryoji Ikeda
池田良治


1997 : Come to Daddy. Aphex Twin
Chris Cunningham
克里斯·坎宁安

1992 : Helikopter Streichquartett
Stockhausen
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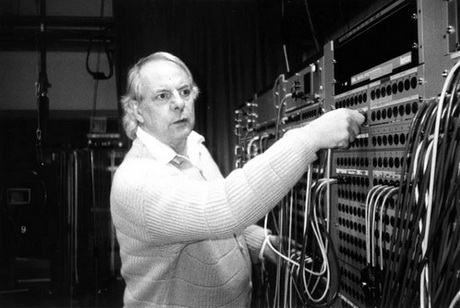
注:图片及翻译信息部分来自网络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