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创作一件新的艺术作品,我需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然后,当我进入并穿越这个世界后,作品便诞生了。”
——皮埃尔·于热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于1962年出生于巴黎,现工作生活于纽约。于热曾就读于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校(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arts décoratifs)。他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使用的“后期制作”(post-production)手法闻名,重新运用电影和大众媒体中的图像。于热创作的电影、装置和偶发事件艺术作品探索哲学思想,混淆事实与虚构,并用展览这一模式进行戏谑的实验。
于热的许多作品融合了一系列生物元素,如昆虫、动物、植物和人类,以此探索他们的行为和彼此之间的互动。这些作品成为了于热阐述复杂社会现象以及当代信仰系统的实验场。于热在欢愉与奇遇的主题中加入心理学的元素,探讨幻想与真实之间不确定的界限。他的作品通常包括多种叙事和碎片化的含义,召唤梦想、权力与征服、以及对乌托邦的探索。近年来,于热的作品开始在博物馆和传统艺术场域以外的空间展出,进而拓宽了其艺术实践的范围。
于热的作品曾参展众多国际及全国性展览。近期个展包括:2017年,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皮埃尔·于热。无题(人形面具)」(Pierre Huyghe. Untitled (Human Mask));2015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皮埃尔·于热。人形面具」(Pierre Huyghe. Human Mask);2013年,巴黎蓬皮杜中心「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巡展至科隆路德维希博物馆和洛杉矶艺术博物馆;2010年,马德里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2010年,芝加哥艺术学院「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以及2006年,伦敦泰特美术馆「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
于热也参与了众多群展,其中包括:2017年,纽约犹太博物馆「拱形:当代艺术与瓦尔特·本雅明」(The Arcades: Contemporary Art and Walter Benjamin);2016年,日本森美术馆「宇宙与艺术」(The Universe and Art);201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现代博物馆「生活本身」(Life Itself);2016年,第32届圣保罗双年展;2015年,第14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2015年,索菲娅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白火。瑞士巴塞尔艺术博物馆的现代收藏」(White Fire. The Kunstmuseum Basel Modern Collection) ;以及2013年,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博物馆「现代性?来自法国和土耳其的视角」(MODERNITY? Perspectives from France and Turkey)。
于热曾获得众多奖项,包括2017年的纳什尔雕塑奖(Nasher Prize);2015年的“库尔特·施维特斯奖”(Kurt Schwitters Prize);2013年的“哈夫特门奖”(Roswitha Haftmann Prize);2010年由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颁发的“当代艺术家奖”(Contemporary Artist Award);2002年的“雨果·博斯奖”(Hugo Boss Prize);以及2001年第49届威尼斯双年展颁发的“评审团大奖”(Special Jury Prize)。
于热的作品也被众多美术馆收藏,包括:巴黎国立现代艺术美术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伦敦泰特美术馆、科隆路德维希博物馆、路易威登基金会、皮诺基金会、卢玛基金会等。
艺术家作品
拟人手法与生态系统
▽
生态系统在于热的艺术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乐忠于将动植物纳入自己的艺术项目中,并以此探求人类能够控制自然的程度,进而引发出艺术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控制其作品的问题。于热的这类作品常常以一种复杂的系统呈现,这种系统以涉及广泛的生命形式、无生命力的事物以及科技为特点。经他编排过的有机体不仅结合了生物、技术和虚构的成分,还创造了一种供人类、动物和非生物不断演变的环境,好像显微镜下的单细胞生物或者病毒。
于热精心构建的情境会让人联想到生物圈。在这里,他还用了许多大自然的定律:变化的结构参数、群体表现以及集群发展。于热期望让观者远离“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的视角,反思与人类与这个无形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动物、植物以及矿物,以及受到威胁的环境,从而拆解和重建观者的视觉与情感认知。


▲ 《耕种》,2011-2012年,活物和死物,做的和没做的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非理性》(La déraison),2014,混凝土 大理石 供暖系统 水 植物,36 ¼ x 97 ¾ x 51 英寸。© 皮埃尔·于热,图片:皮埃尔·于热,豪瑟沃斯
《非理性》(La déraison)初看像是一座古典传统雕塑——它的原型是让-巴蒂斯特·贝洛克(Jean-Baptiste Belloc)在1931年为「 国际殖民地博览会」(Exposition Coloniale Internationale) 创作的纪念雕塑中的一件。贝洛克创作的雕塑皆以女性形象暗喻躺在殖民地之上的法国。在《非理性》的原型中,这个斜靠着、没有头部的女性雕塑代表非洲。这件纪念雕塑在1961年被损坏,但仍有一部分被保存下来,这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暴露在自然环境中。于热在自己的雕塑中刻意再现了大自然在雕塑上留下的痕迹,青苔自然地生长在雕塑之上,使雕塑变成了一小片充满生命力的土地。于热还特地为雕塑加上供暖系统,让这个看起来早已被人们遗忘的雕塑散发生命的热度。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闪烁的征程,第一幕(天气评分)》(L’Expédition scintillante, Acte 1(weather score)),2002,雪 雨 雾 编程降水,尺寸可变,© 皮埃尔·于热,图片:皮埃尔·于热,豪瑟沃斯


▲ 《Zoodram 5》,2011年,玻璃池,过滤系统,树脂面具,寄居蟹,箭蟹和玄武岩,76.2×134.62×99.06厘米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寒武纪大爆发15》(Cambrian Explosion 15),2017-2018
《寒武纪大爆发15》(Cambrian Explosion 15, 2017-18)出自于热2010年开始的一系列玻璃箱中活体海洋生态系统作品。作品的题目意指5亿年前寒武纪开始,寒武纪地层在2000多万年内突然出现众多动物化石。作品呈现了一个超现实的场面:箭蟹和马蹄蟹漫游在海葵和微生物之中。这些甲壳纲动物被认为是活化石,因此挑战着“时间是线性的”这一概念。一块漂浮的大石头冲破水的表面,好像时间被暂停于水箱之中。随着螃蟹书写着不可预测的叙事,作品本身也随之演变,持续发展、从不自我重复。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无题(人类面具)》(Untitled(Human Mask)),2014,彩色 有声,19分7秒,© 皮埃尔·于热,图片:皮埃尔·于热,豪瑟沃斯
电影《人类面具》(Untitled(Human Mask), 2014)设置于灾难后的日本福岛,讲述了一个戴着年轻女性面具的猴子服务员的日常活动。于热创作此电影的灵感来自于日本的一个真实场景——一个受过训练的猴子戴着面具,担任一名服务员。电影以2011年福岛的荒凉景色开篇,接着拍摄孤单的主人公猴子在餐馆的场景。在这个反面乌托邦的设置下,一只动物演绎出人类的遭遇,被困在一个无休止重复的无意识角色当中。影片展现出工作的单调性、仪式行为的重复性,以及灾难性未来的可能性。




▽
角色扮演与电影演绎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配音》(Dubbing),1996,彩色 有声,120分钟
在影像作品《配音》(Dubbing, 1996)中,于热在一间录音棚里放映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拍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恐怖片《鬼驱人》(Poltergeist),但他没有将摄像机集中在电影本身,而是集中在正在为这部影片配音的15名法语演员身上。作品同时探讨了投射与翻译、存在与缺席之间的关系——于热没有直接让观众看到放映的电影,而是通过配音演员的行为展现无形的投影。用于热自己的说法,《配音》是“通过叙事的解读质疑着语言与时间。”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白雪》(Blanche-Neige),1997,彩色 有声,4分钟
创作于1997年的《白雪》(Blanche-Neige)可被视为《配音》的续篇。其中,于热解开了为法语版《白雪公主》电影配音的演员露西·多琳(Lucie Dolène)的面纱。当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重新发行这部电影时,没有获得多林的许可便使用了她的声音,因此多琳将迪士尼公司告上法庭,控诉迪士尼侵权。于热的电影则记录了多琳讲述自己的这段经历。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占用你2分钟时间》(Two Minutes Out of Your Time),2000,出自「没有魂仅有壳」(No Ghost Just A Shell)展览项目
1999年,于热与法国艺术家菲利普·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购买了一个动漫人物的使用权,将其命名为“安丽”(Annlee),将语言的主观表演这一概念挪用至虚构人物的身体当中。两人随后邀请艺术家利亚姆·吉利克(Liam Gillick)、多米尼克·冈萨雷斯-福斯特(Dominique Gonzalez-Foerster)、皮埃尔·约瑟夫(Pierre Joseph)、梅里克·欧海宁(Mélik Ohanian)、乔·斯坎伦(Joe Scanlan)和里克力·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利用安丽这一形象分别创作各类作品,所有作品构成了巡回展览「没有魂仅有壳」(No Ghost Just A Shell)。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一百万个王国》(One Million Kingdoms),2001,出自「没有魂仅有壳」(No Ghost Just A Shell)展览项目
几场展览过后,于热和帕雷诺将该人物的版权转移至由安丽所有的法人实体“安丽协会”(Annlee Association),从而“保证”了她的自由和死亡。「没有魂仅有壳」建立了艺术家与展览场馆之间的关系网,颠覆了展示艺术品的传统方式。在这个项目中,相同的一张图像作为艺术家个人实践的一部分,贯穿了各式各样的场所和语境——生产、呈现与接收的多样性,在相同中表现差异。从安丽这一形象在不同作品中保持一致这一点出发,于热通过此展览项目,提出了以下问题:作者是否总是主观的?有没有可能想象出一个没有性格的人物?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主体?身份在现实、电影和艺术中是如何形成的?
▽
虚构的场域与回忆的塑造
通过混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并揭示出虚构可以像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物一样有形可触,于热的作品经常触及复杂的社会议题,如对乌托邦的渴望、大众媒体中奇观的诱惑,以及现代主义对当代价值观和信仰体系的影响。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第三记忆》(The Third Memory),2000,双频影像 有声 9分32秒,尺寸可变
于热的双频影像作品《第三记忆》(The Third Memory, 2000)由美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文艺复兴学会(The Renaissance Society)委托创作,后于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作品以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1975年的电影《热天午后》(Dog Day Afternoon)为出发点,重构了电影的场景,让所描写的人物本人、出狱后的银行抢劫犯约翰·沃特维兹(John Wojtowicz)出演,亲自讲述抢劫的故事。于热将自己重构后的图像与《热天午后》的素材并置,展现出沃特维兹的记忆已经被电影深深地改变。通过拍摄构造出的情境,于热探索了电影扭曲并塑造记忆的能力。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河滨日愚行》(Streamside Day Follies),2003,© 皮埃尔·于热
创作于2003年的《河滨日愚行》(Streamside Day Follies)讲述了三个节点之间的关系:位于纽约州哈德逊谷的一个正举办一个虚构节日的虚构社群、一部捕捉节日进程的真实电影(film verité),以及迪亚艺术基金会在曼哈顿的一个展览空间。展览涉及到第四个空间的建立,其中虚构社群、电影和展览空间汇集在此。于热设计了四面墙,通过电脑编程,会断断续续地自行闭合在一起,从而使电影《河滨日愚行》得以放映。电影结束后,墙便会分散开来。这件多面化的作品运用了一系列文化符号,包括十九世纪的乌托邦社会项目、好莱坞电影、迪士尼动画、当代小说,以及浪漫主义风景绘画,探索在建立社会仪式和传统中,意识形态与语言系统所扮演的塑造性角色。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主人与云朵》(The Host and the Cloud),2009-2010,2小时2分,© 皮埃尔·于热
电影长片《主人与云朵》(The Host and the Cloud, 2010)拍摄于巴黎国立艺术与流行传统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rts and Popular Traditions)的旧址。影片散乱、阴郁、略带科幻性质的叙事基于万圣节、情人节和劳动节的庆祝活动。在这三个节日中,一群人被放置在结合剧本行为和角色扮演的情境中。在整个博物馆内,诸如加冕礼、安魂弥撒、催眠和时装秀等仪式活动,与木偶戏、动画、音乐剧幕间节目和童话人物偶遇交替进行。资本主义的结构在南瓜灯的流水线生产、女性化妆成麦当劳叔叔和一篇有关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的文章中显而易见。电影开篇重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处决法国激进组织“直接行动”(Action Directe)的场景。影片结尾是另一个法庭场景,有关审理1993年网络社群LambdaMOO的性别暴力案件。如果第一个场面与极左政府行动有关,那么第二个场面展现了科技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于热对虚拟与现实之间模糊界限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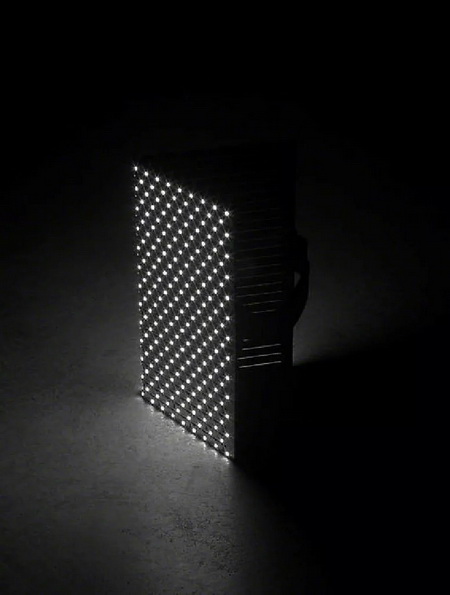


▽
公共艺术与特别展览项目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一次不是旅行的旅程》(A Journey That Wasn’t),2005,电影转换成视频,21分41秒。© 皮埃尔·于热,图片:皮埃尔·于热,威尼斯路易威登空间
2017年,于热受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官方的特别邀请,在威尼斯路易威登空间举行了一场同名个展。展览呈现了以创作于2005年的电影《一次不是旅行的旅程》(A Journey That Wasn’t)为核心的共三件作品。
《一次不是旅行的旅程》讲述了著名探险家让·路易·艾蒂安(Jean-Louis Etienne)前往南极探险的故事。电影描写了一场在南极圈乘船寻找未知岛屿的旅程,以及过程中与海岸生物的邂逅。此项目分为两个部分——一次远征,并将岛屿地形“翻译”成声音;这些声音随后变成了一支乐曲,由交响乐团在纽约中央公园的溜冰场上演奏。这部电影让观众陷入了对立的世界中:一个是纯粹的、未受到破坏的自然环境,另一个是壮观的城市化社会。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生物》(Creature),2005-2011,雕塑。© 皮埃尔·于热,图片:皮埃尔·于热,豪瑟沃斯,威尼斯路易威登空间
作为对电影诗意的补充,《生物》这个作品将独居的企鹅转化为具有合成毛皮和声音的小型玻璃纤维鸟。于热说,它不仅仅是一个雕塑,它还具备“一个独特的直觉,在遥远的一个无法触及的地方,他/她几乎消失于周围的环境之中。”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沉默的乐谱》(Silence Score),1997,一组四张数码打印 彩色铅笔。© 皮埃尔·于热,图片:皮埃尔·于热,豪瑟沃斯,威尼斯路易威登空间
与这部电影同时展出的《沉默的乐谱》为电影创造了虚幻的音乐气氛,并扰乱了观者的感知习惯。在一个特殊软件的帮助下,于热转录了四份乐谱,其中包括约翰·凯奇(John Cage)在1952年录制的无声作品《4分33秒》。依据凯奇的创作理念,音乐家将在演奏作品期间保持沉默,周围空间所产生的声音便成为了演出的作品。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屋顶花园委托作品,2015
2015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委托于热为其屋顶花园创作一件作品。于热在屋顶上挖起了20片砖,安置了一个石灰岩圆石和一个水箱。水箱里的水渗入地面上被挖起的区域,最终进入博物馆的排水系统中,从而使屋顶花园成为了一片矿物风景,以水的循环系统贯穿。这件装置探索了通过一套演变过程以及一系列复杂元素组成的网络,文化与自然资源所经历的变化。

▲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未来生命之后》(After ALife Ahead),溜冰场水泥地板 逻辑游戏 氨 砂 粘土 地下水 细菌 藻类 蜜蜂 杂色孔雀 水族馆 可切换黑玻璃 织锦芋螺 萤光鱼 孵化箱 人类癌细胞 遗传算法 增强现实 混凝土地板 自动化天花板 雨水。摄影:Ola Rindal,图片:皮埃尔·于热,豪瑟沃斯
在2017年德国明斯特雕塑展(Skulptur Projekte Münster )上,于热展出了大型装置作品《未来生命之后》(After ALife Ahead)。其中,于热发展出了一种基于时间的生物科技系统,这个系统建立在一个于2016年关闭的滑冰场中,受到生物和媒体技术的干预,需要建筑的拆解和重建。所有的进程都在一个巨大的空间中完成,它们同时也是相互依存的:有一些在孵化器的恒定分离程序中,由海拉细胞系来决定。在各种不同的影响下,细胞生长成了各种形状。织锦芋螺的多变也改变了空间的配置:比如可以影响大厅天花板上菱锥形窗户的开与关。通过深入研究土地,于热将地面转换成了一个需要向下探视的丘陵景观。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混凝土和泥土、一层层的黏土、聚苯乙烯泡沫、碎石砂砾还有冰川时代的沙子,它们都散落在地表上。这个空间是可以栖居的,适合藻类、细菌、蜂箱和孔雀等。在这里,具有生命的生物、真实和标志性的建筑和景观、有形或无形、动态与静态混合成一个不稳定的共生系统。
▽
重要美术馆及画廊展览

▲ 2013年巴黎蓬皮杜中心「皮埃尔·于热」回顾展现场图。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无题(晴雨表)》(Untitled (Weather Score)),《无题(黑色冰制舞台)》(Untitled (Black Ice Stage)),表演者,2002 - 2010。摄影:Ola Rindal,© 皮埃尔·于热,图片:皮埃尔·于热,豪瑟沃斯

▲ 2014年洛杉矶县立美术馆「皮埃尔·于热」回顾展现场图。© 皮埃尔·于热,图片:皮埃尔·于热,豪瑟沃斯

▲ 展览现场,蓬皮杜艺术中心,2013.9-2014.1,摄影Arash Nassiri

将时间维度建于雕塑之上:皮埃尔于热
本文来源:中国美术报网 2017-12-14
文/胡欣
艺术家皮埃尔·于热 (Pierre Huyghe)出生于法国巴黎,现生活工作于纽约。他的作品时常呈现出一套自我构建的复杂系统,涉及科技、无机物以及一系列对于广阔生命形式(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自身)的运用。作为今年纳什尔雕塑奖(Nasher Prize)的获得者,皮埃尔·于热在《ArtReview》上个月推出的“Power 100艺术权力百人榜”中位居第二,他的新作《未来生命之后》(After Alife Ahead,2017)在今年明斯特雕塑展(Munster Sculpture Project)上也备受瞩目。
皮埃尔·于热的创作一直致力于打破规则,从展览方式、材料与媒介等各方面不断挑战艺术界传统,寻求非常规素材在多样化的场域制造文化对峙的可能性。尽管艺术家否认其创作对于雕塑、影像等种种媒介形式负有任何的义务与使命,但其作品正源源不断地将各类实践纳入雕塑范围,拓宽着人们对于雕塑的定义。他的创作甚至使得“雕塑”一词本身显得过于单薄与狭隘。
在传统的三个维度上,皮埃尔·于热赋予作品以时间的概念,这使得其创作对于世界真实的感知与呈现变得难以琢磨。因为时间随之带来变化。于热的作品将生物、有机体、各种科技与虚拟元素相结合,试图营造一个人类、动物、单细胞生物甚至病毒之间相互依存的互动环境。
“我不是期待这些个体进行什么表演,也没有打算去定义某种联系。我创造一个初始的环境,让这一环境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提供可能。”
随时间推移,生物之间,活着的,死去的;生物与环境,偶然的,必然的……种种联系都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使艺术家的作品最终缓慢异化为一个崭新的他者,完全独立于它们的创造者而存在。于热的创作仍在以侵略性的姿态将不同参数纳入他的创作实践之中:动物,植物,人类,机器,机器人……甚至一块石头。艺术家正寻求一种方式,使其能够从任何事物中捕捉变化。
皮埃尔·于热摆脱了人类中心论的观察视角,将其艺术实践拓展到生态中心论的范畴,使人们的关注点从人类自身转移到了整个生态系统。《未耕种》(Untilled,2011-2012)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这是于热为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创作的作品。
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的讨论围绕“创伤”一词展开,意图回溯卡塞尔文献展创立之初的本意——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不同的是,由于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发起与战后欧洲的重建紧密相连,展览成为探讨人与周遭环境之关系的思考方式。而“反拟人论”(anti-anthropomorphism)作为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主题之一,旨在摒弃以人为思考中心的观点,通过将话语权力中心从人类意识形态转移至更加广泛的生命与存在,使人与构成生态系统的诸要素处于平等的位置。
《未耕种》位于公园的一处肥料堆上,由致幻类植物、一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97-1982)的雕塑复制品与一只前腿被染成亮粉红色、名叫“人类”的狗组成。为了强调个体(有生命的、无生命的)之间的共生关系,艺术家将一个蜂巢移植到石制雕像头部,而在展览期间,蜂巢的增长速度已经使其头部被完全包裹起来。

▲ 皮埃尔·于热,《未耕种》,生命体与无生命体,人造物与自然物,尺寸可变,2011-2012 Photo: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 皮埃尔·于热,《未耕种》,生命体与无生命体,人造物与自然物,尺寸可变,2011-2012 Photo from the Internet
艺术家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这一场所:人们在此处处理废弃之物——那些被定义为“死的”,或者是“没用的”东西。在这里,被弃物原始的文化与意义被抽离,与人的关系变得无关紧要。这使得赋予它们新的意义成为可能——它们自身成为创作者。对于艺术家而言,它们与出现在公园的其他普通物件无异——都来自历史,也将封存于历史:一尊塑像,一条长椅,一盏路灯,一只动物,一个人,它(他)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渗透到关于生命与矿物的真实当中,如同地质演变,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见证。作品《未耕种》中的一切要素看上去都不可控制:植物的生长过程,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人类与霉菌都是这些变化与偶然的旁观者、记录者。在这里,人类成为客体,与其他个体(包括霉菌)、能量共同作为平等的部分构成一个更加广阔的整体——而事实也是如此。
皮埃尔·于热善于构建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他在日本南部进行的项目与卡塞尔文献展无异,但进一步为作品设计了一款专门的手机应用软件,将各要素之间的能量交互直接视觉化。其作品中的每一个要素就像密布于宏大的生态系统中的微小血管,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与交流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各要素自身。对于艺术家而言,单个个体的意义与影响力是恒定不变的,将不同的个体(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并置就像启动一架由不同大小的齿轮组成的机器,能够生成多种未知的影响力。作品《Zoodram 4》在水族箱里构建了一个虚拟的海洋生态系统:一只以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的雕塑复制品《沉睡的缪斯》(Sleeping Muse)为壳的寄居蟹在水中缓慢移动。水族馆作为一个汇集全世界不同海洋物种的虚拟自然场域令艺术家着迷。对艺术家而言,这是一个发生关系分离与断裂的悬置空间。

▲ 皮埃尔·于热,《Zoodram》, 2011 Courtesy of Pierre Huyghe
就这一点来说,艺术家认为水族馆与博物馆不无类似。不同类型的个体被并置于同一时空,彼此无法真正产生关联。分离是博物馆不可避免的性质。更严重的是,博物馆的繁文缛节可以完全剥夺一件作品的生命力。这也是为何艺术家一直致力于在博物馆之外为其作品寻找空间——寻找一个富有连贯性的场所,并强调“在场”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展览不应该为一个预先设定的模式存在,而应该独立地处于变化之中。

▲ 皮埃尔·于热,《未来生命之后》,2017
早在明斯特雕塑展三年以前,皮埃尔·于热表示,“我要在我所希望的地方种植一件作品。”最终,艺术家选择了一处远离明斯特中心,于2016年关闭的废弃滑冰场。在这里,通过对原始建筑的摧毁与重构,以及生物科技与媒体科技的交互,于热构建了一个“时基性”的生态系统。通过不断地向下挖掘,艺术家将滑冰场的地面改造成一处低于地平面的微型丘陵地貌。在挖掘过程中,不同的土质层、混凝土、塑料泡沫、碎石甚至冰川时期的沙砾在仅仅几米深的地下被找到,散落在残余的破碎地表周围。这是一片被水藻、细菌、蜂群与虚构的孔雀入住的空间。不同的生命形式:群体的,个体的;建筑结构:真实的,虚拟的,象征的;化学反应:可见的,不可见的;能量形态:凝结的,流动的……都在一种极不稳定的共生关系中相互纠缠。
甚至对于地表的切割也不是孤立与无规律的。它受到滑冰场天花板未来主义风格纹样的启发,并且从阿基米德的十四巧板拼图(由一个正方形分割出的十四块大小形状各异的三角)中获得灵感。皮埃尔·于热在地板上重新绘制出新的格纹图案,并严格按照这一系统进行切割。这使得滑冰场既不类似于一个普通的建筑工地,也不像一个简单的考古现场。
在这个巨大的场域中,隐秘的生命暗含其中,并根据一种潜藏的机制运行,所有要素的运转都相互依存。恒温箱中不断分裂的海拉细胞系 (Hela cell line)(海拉细胞系是第一株人类分离培养的可无限增殖的细胞系,被来自全球的科研者广泛使用)会触发AR成像;滑冰场天花板上倒金字塔形的天窗一开一合,其频率是根据水族箱中一种海螺的三角形螺纹确立的。

▲ 皮埃尔·于热,《未来生命之后》,2017,Photo: Valentinas Klimasauskas
参观者可以顺路面步入残破的废墟,也会被突然出现的、布满水藻与真菌的水洼拦截去路。下雨天开合的天窗使雨水倾泻而下,海藻会持续生长。景观不会停止改变——就像作品的名称一样,作品最终会独自发展,直至与初始状态仅剩一丝关联。
这个耗费了数十万欧元的项目在明斯特雕塑展结束后随即面临着被摧毁。如此短暂的寿命对于皮埃尔·于热而言也颇具哲学意味。这是规则的一部分。“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正因为我马上就会摧毁它。你需要做出选择。”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