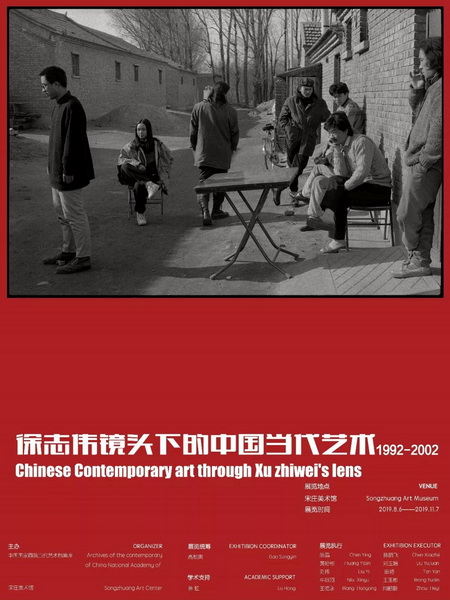吕澎 朱朱
由于“改造历史”展览的工作量巨大,并且不断因为外界和展览本身的原因而发生工作上的调整,这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因此,有效的分工和组织就成为展览进行的必要条件。
“改造历史”展览负责与艺术家联络的工作人员现在有四人,负责人是刘珍。刘珍是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陈默教授的研究生,大学是德语专业。但是,她非常喜欢艺术,所以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艺术家的圈子里,并且通过调查与访问收集并写作一些相关的文章。尽管她和她的团队仍然缺乏足够的经验,并且也会在实际的工作中遭遇困难,但是,她们(全部是女生)始终充满生气与热情地工作着。
由于“改造历史”展览的目标是将近十年里的重要艺术家和艺术现象尽可能全面而完整地呈现出来,为我们思考和研究中国当代艺术提供一次现场机会,而不是提出一个特别主题目标的展览。这样,我们就自然不会放弃寻找我们认为值得将他们的作品放进展览中的艺术家。在确定参展艺术家名单的过程中,有很多情况需要报告:
1、有大量艺术家(主要是年轻艺术家)自荐希望参加“改造历史”展览,而实际情况是,的确有很多年轻艺术家被我们放进了参展艺术家的名单中;
2、展览有一个由年轻批评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他们每个人都向策展人推荐了十位甚至更多的年轻艺术家。需要提示的是,由二十位年轻批评家分别推荐的艺术家共有150多位,重复推荐的艺术家很少,表现出缺乏更多的共识,这也许说明今天的艺术现象更加个人化,潮流性的特征越来越被碎化的问题给减弱,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艺术更加丰富多样呢?
3、当然,大多数参展艺术家是由策展人确定的。一个突出的情况是,大多数艺术家是提供新的作品,绘画作品往往尺寸很大,并且很多是多联画。由于作品新,所以,能够想象,未来的现场一定是很让人提神的。在材料与形式上,囊括了绘画、雕塑、装置、影像和图片等,有些艺术家甚至是同时提供绘画和影像或者装置作品的。这样,我们将在未来的展厅里看到不同样式、语言和材料的艺术作品,由于新作品很多,也就会让观众对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有全方位的了解。
4、仍然不断地有朋友和机构在推荐艺术家参加“改造历史”展览,也有艺术家继续自荐,希望参加展览,我们非常感谢这些朋友、机构和艺术家对展览的认可与支持,请充分理解他们参加展览的愿望,只是,由于策展人有自己的学术、实际操作和其他方面的考虑,也就不可能让每一个希望参加展览的艺术家得到满足。不过不要紧,如果是好的艺术家,总是会有机会让观众看到你的作品的。无论如何,为了尽可能地不要忽略好的艺术家,我们将最终选择和确定参展艺术家名单的时间放在了2月28日。
5、也有少数艺术家担心大型展览是否会影响到观众对自己的作品的注意和很好地被观看。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尽可能通过空间的扩大、展览的设计、灯光的讲究以及针对作品进行的特殊安排,来让所有的艺术家的作品有充分的展示。当然,这不是艺术家的个人展览,但是,我们尽可能地为艺术家准备充足的展线和空间,让艺术家的作品有系统和更丰富的展出,以便充分呈现每一位艺术家的艺术想法与观念。
6、这次台湾艺术家的参展名单,原则上由高千惠确定,她负责了台湾和香港地区艺术家的甄选工作,目前估计,将有二十多位港台艺术家参加“改造历史”展览。这个板块将是本次展览中的重要部分,对于那些了解1949年以来的历史的人来说,他们知道这次港台艺术家的集体参展将意味着什么。观众将在未来的展览出版物中读到高千惠女士关于台湾三十年艺术的归纳与介绍。我们也希望这次台湾艺术家的参加将成为两岸艺术交流的一个转折点。
在后面与艺术家的工作联系中,展览的工作人员将继续竭尽全力为艺术家服务,他们将继续带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对工作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做好展览的筹备工作。如果在工作中有什么问题与困难,请不要犹豫给我们的团队指出来,我们一定会为尽可能满足参展艺术家的要求而改进缺点、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