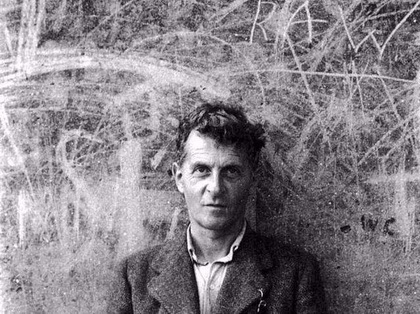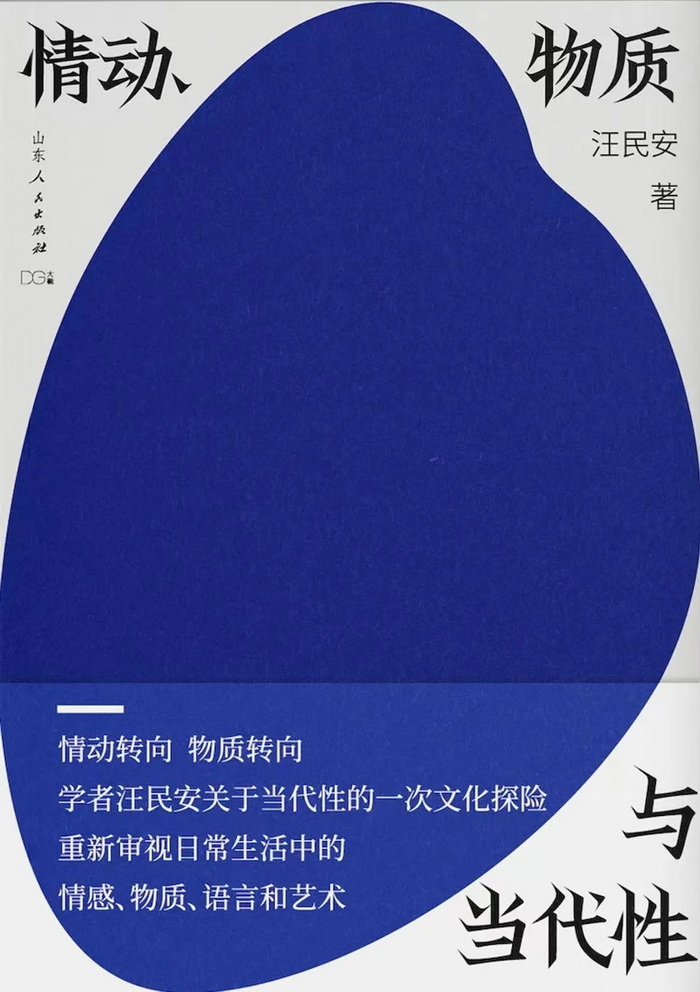
情动、物质与当代性
作者: 汪民安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22-10
页数:312
装帧:平装
ISBN: 9787209136969
目 录
I 情动
何谓情动
友谊,语言与沉默
真理与犬儒主义
论俯视
培根与当代艺术的肉身转向
Ⅱ 物质
物的转向
符号价值与商品拜物教
论垃圾
巴洛克 :弯曲的世界
Ⅲ 当代性
什么是当代
游荡与现代性经验
何谓赤裸生命
从国家理性到生命政治
再现的解体 :福柯论绘画
后记
后 记
这本书是我近几年的论文合集,但这些论文之间并非没有关联。就像书名所表明的,它涉及到情动,物质和当代性等几个主题。情动和物质是今天两个竞争性的理论潮流,前者以一种迂回间接的方式重新将目光投向了人和主体这些看上去已经陈旧的概念;而后者则试图更激进地去摧毁人文主义意义上的人和主体,它们是“人之死”更暴躁的版本。这是理论在今天围绕人而出现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分叉。如今的理论内部充满着各种搏斗,理论靠这些搏斗来繁衍。不过,我的这本书远没有展示今天理论纷争的复杂性。之所以编选这个合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和我十几年前的另一个合集《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相呼应。这两个不同的合集多少也反应了我理论趣味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身体和空间这样的主题已经过时了,相反,它们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出现了新的形态,它们仍旧是这个时代核心性的理论问题——它们被后人类和数字化技术这些更大的理论框架所吸收,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锻造和重塑了这些理论框架,我对它们的新近发展仍旧充满了兴趣。而情动(感)和物质这样的主题已经吸引了我很久——我是在完成了两部小书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前几年的《论家用电器》是探讨物质的,刚刚出版的《论爱欲》则是探讨情动(感)的。不过,我并不是在情动转向和物质转向这样的理论潮流的挟裹中去写这两本书的,我也没有依照严格的理论模式去从事我的研究。相反,我是出于经验、兴趣以及某种理论直觉去写这两本书的,我也总是试图驯化理论的格栅性——实际上,关于情动和物质的诸种理论本身就各执一词,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模型。我不担心我是否正确地运用和解释了某种理论,我担心的是我在运用和解释某种理论时到底有没有意思。我的理想是去激活理论,让它流动起来,并且可以到处运转,甚至将它拖到它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将理论进行封闭性的还原解释实际上是对理论的扼杀。
如果说,《论家用电器》和《论爱欲》这两本书是对(新)物质理论和情动理论的一个直觉式的呼应,那么眼下的这本书就是对我所理解的情动转向和物质转向的解释和运用。如果说身体理论和空间理论是在几十年前的后现代氛围下展开的,那么,情动理论和各种有关物的理论很显然被笼罩在当代性的氛围中——如今后现代这个词已经很少被提及了,人们更多愿意用语焉不详的当代性这个概念来命名此时此刻。我在书中也试图解释了何谓当代性。
感谢陈卫的信任,正是他建议我出版这本书;也感谢陈树泳为本书所做的繁琐的编辑工作。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两个学生高畅和王艳秋,她们帮助了我很多。在我的这本书以及我的其他研究中,都留下了她们耐心的工作痕迹。
汪民安
2022年7月26日
何谓“情动”?
见本书第一章
一
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对身体有特殊的理解。他不单纯是从身体内部来讨论身体,而是将身体放在和其他身体之间的关系中来讨论。这是身体(物体)和身体(物体)之间的关系:“一个物体(身体)之动或静必定为另一个物体所决定,而这个物体之动或静,又为另一个物体所决定,而这个物体之动或静也是这样依次被决定,如此类推,以至无穷”(斯宾诺莎 57)。“人体自身,在许多情形下是为外界物体所激动”(60)“人身能在许多情形下移动外界物体,且能在许多情形下支配外界物体”(61)。人甚至能被不同的外界身体(物体)所同时激动。在另一个地方,斯宾诺莎更加感性地说到:“我们在许多情形下,为外界的原因所扰攘,我们徘徊动摇,不知我们的前途与命运,有如海洋中的波浪,为相反的风力所动荡”(149)。
这就是说,人的身体总是被外界的身体(物体)所扰攘,所挑动,所刺激。人的身体总是同外界的身体(外界的人或者物)发生感触(身体并非一种独立的自主之物,它总是处在一种关系中)。斯宾诺莎就将情感理解为这种“身体的感触”,正是这种身体的感触产生了情感。比如,我碰到了一个人,或者我遇上了一件事,就是一个感触,一个遭遇产生了感触。这就是情感的诞生。情感诞生于身体的感触经验。
这种感触产生了什么样的情感呢?情感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斯宾诺莎说,大体上来说主要有两种类型:快乐和悲苦。我碰到了一个人或一个物,我感到快乐;我碰到了另一个人或者物,我感到不快乐,我感到悲愁或痛苦。这就是身体感触引发的情感——大体上来说,不是悲苦,就是快乐。或者说,悲苦和快乐同时兼备,有时候悲苦的比例大,有时候快乐的比例大,有时候二者旗鼓相当。痛苦和快乐这些情绪的变化,“随人的身体的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常常是互相反对的,而人却被它们拖拽着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不知道他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前进。”
但是,感到快乐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或者说,感到痛苦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呢?快乐或痛苦是这样的情感:“快乐与痛苦乃是足以增加或减少,助长或妨碍一个人保持他自己的存在的力量或努力的情感”(148)。这是快乐或痛苦的力量实践,具体地说,“一切情绪都与欲望,快乐,或痛苦相关联,痛苦乃是表示心灵的活动力量之被减少或被限制的情绪,所以只要心灵感受痛苦,则它的思想的力量,这就是说,它的活动的力量便被减少或受到限制”(148)。相反,只要心灵感到快乐,则它的活动力量,行动的力量,存在的力量就增加。“我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这些情感或感触的观念同时亦随之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97)。这是斯宾诺莎和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反复宣称的,情感和身体的力量密切相关。快乐的时候,身体之力增加;痛苦的时候,身体力量受限制,就受到贬损。这种力量的增加也可以说是一种主动,主动的心灵是没有痛苦的,只有快乐。在主动之中,在施与之中,在对他物(身体)的施与力量中,能感受快乐。快乐、主动、施与和活动力量的增加是一体的。反过来,被施与和受影响,悲苦,被动和活动力量的减弱是一体的。一旦处于受影响的状态,身体就会无能为力,毫无肯定性,“代表着我们的奴役状态,易言之,这是我们行动力量的最低级状态”(《斯宾诺莎》 224)。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足球场上的运动员,当攻破对方球门的时候,他们是主动的,他们感到快乐,同时,他们会跳跃,他们像火球一样跳跃起来——他们的活动力、他们的存在力就增加。他们的主动性,活动力和欢乐就会同时爆炸。而被攻进球门的一方呢?他们充满被动,脸色愁苦,垂头丧气,步履蹒跚,运动的能力和存在的活力一扫而空。每一场足球比赛的结局都是这样一个生动的场面。这是情动(affect)的两种形状不同的力,强力和无能为力,主动力和被动力,欢乐之力和悲苦之力。实际上,德勒兹早就在尼采那里发现了这两种力。对尼采来说,权力意志就是力和力的斗争关系,就是主动力和被动力的永恒斗争关系。
二
快乐和愁苦这两种情感,本身并非是静态的。它们都是一个过程。用斯宾诺莎的说法是,快乐是一个人从较小的圆满到较大的圆满的过程,痛苦是一个人从较大的圆满到较小的圆满的过程。痛苦和快乐都是一个运动过程,它们本身充满着变化,痛苦的过程是力的缩减的过程,快乐的过程是力的增加的过程。不仅如此,快乐和痛苦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等级落差。快乐会向痛苦转化,痛苦也会向快乐转化,正是这个落差导致了流变,也一定会产生流变。没有一个球队永远只是攻入对方大门,它也会被对方攻入大门。它们总是会被来回攻入。因此,情感,存在的活力也会来回变化。就此,没有一种情感是固定的,这就是情感的变化。一个人的情感总是根据不同的际遇而发生不同的变化,他总是在悲苦和快乐之间发生变化——德勒兹就是把这种情感的流变称之为affect:我这节课上的老师是我暗恋的对象,我上他的课我感到快乐,我充满力量,但是下一节课是我讨厌的老师,是故意刁难学生的老师,我在他的课上充满悲愁,我无精打采。我在这两节课之间因为同不同老师发生遭遇而产生情感变化和身体之力的变化。——我们反复说过了,情感的变化,同时意味着存在之力或活动之力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德勒兹理解的affect(我们姑且将它翻译为“情动”),“情动:存在之力(force)或行动之能力(puissance)的连续流变”(《万塞讷》 6)。情感因为际遇,因为同各种各样的对象发生感触而变化。这种情感的变化或者运动,既可以是痛苦的持续强化,也可以是快乐的持续强化;既可以是从痛苦到快乐的运动变化,也可以是从快乐到痛苦的运动变化。总之,从快乐到痛苦到快乐再到痛苦,情感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化中。快乐和痛苦这两种相反的情绪甚至常常混淆、交融在一起,它们有各种各样的组合关系,有无限多的组合关系。痛苦或快乐有时候存在于同一种际遇之中——巴塔耶生动地分析过这种矛盾情感:相互抵触的情感——比如吸引和厌恶,狂喜和痛苦——同时存在于一种经验中。而斯宾诺莎给的例子是:痒。痒就是痛苦和快乐交织在一起的经验。
这个affect(情感,情动)既是心灵的(悲愁或者快乐,也即思想之力),毫无疑问也是身体的(活动之力)。或者说,它将身体和心灵融合在一起了(痛苦和身体之力的衰减是同时发生的,快乐和身体之力的强化也是同时发生的)。斯宾诺莎说,“心灵的命令不是别的,而是欲望本身,而欲望亦随身体情况之不同而不同。因为每一个人所做的事,都是基于他的情感。……这一切足以明白指出,心灵的命令,欲望和身体的决定,在性质上,是同时发生的,或者也可以说是同一的东西”(102)。欲望、心灵的命令和身体的决定,三者是同一的。这就是情动(感)行为。情感行为将身心统一在一起。斯宾诺莎认为欲望是人的本质本身。何谓人的本质?本质“被认作人的任何一个情感所决定而发出某种行为”(150),人的本质就是一种情感决定的行为,这也就是欲望。欲望意味着情感驱使去做,欲望就是情感行为。“所以欲望一字,我认为是指人的一切努力、本能、冲动,意愿等情绪,这些情绪随人身体的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常常是互相对立的,而人却被它们拖曳着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不知道他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前进”(151)。欲望是人的本质,这就是说,affect(情动)乃是人的本质。如果说,“欲望的意义可以把人性中一切努力,即我们称为冲动、意志、欲望或本能等总括在一起”的话,那么,“欲望就是人的本质”,因为,情感所驱动的行为,就是欲望,就是人的本质。
这样,我们可以从affect(情动,或者情感行为和情感变化)的角度来界定一个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他的情感变化,我们可以从情感,情感运动,情感变化的方式来确定一个人的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说,人是一个情感存在,一个始终在发生变化的情感存在。人的存在就是情感活动,affect是人的生存样式(存在之力)。而这个情感既是身体性的(活动之力),也是心灵的(思想之力)。欲望和情感行为是人的本质,这意味着,人不应该被还原为一种对象和观念,就是说,人不应该被确定和还原为一个存在者,就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人应该从存在而非存在者的角度去断定,人应该从他的冲动欲望,从他的情感活动去判定。而不是像柏拉图主义那样将它纳入到更高一级更抽象的概念系统中,它不是一个被表象之物或者被派生之物。在此,斯宾诺莎和德勒兹要讨论的,不是人(身体)是什么?而是人(身体)做什么?能做什么?我们应该从人的动作和谓语,应该从人的存在方式的角度来断定人。
三
17世纪的斯宾诺莎讲这些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对他的同代人笛卡尔的批评。笛卡尔认为心灵和身体可以分开,心灵可以管制身体,心灵是决定性之物。对笛卡尔来说,人是一个心灵的存在。人“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笛卡尔 26)。但是,对斯宾诺莎来说,情感则将身体、心灵合二为一,情感之中包含身体,情感是身体的感触。因此,一个生命,一个主体,不再是一个笛卡尔式的心灵主体(“我思故我在”),而是一个情感主体,一个将身心融合在一起的主体。这是对笛卡尔身心二分的批评。此外,我们只能从情感的角度(而不是心灵的角度)来看待一个主体,一个生命,或者说,只能从情感(或欲望)来给人下定义,来确定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欲望,是情感行为和经验,是行动,是生存——而不是笛卡尔那种安静的“我思”。这样,斯宾诺莎除了破除笛卡尔的二分法之外,他还破除了笛卡尔有关人的存在者的定义(我思),人的本质只能从它的行为和作为中去界定,而不是“我思”这样的静态的存在者的角度去下定义。在此,情动(affect)取代了“我思”。简单地说,我们要从人的行动来界定人,而不是从人的特性来界定人,或者说,对于斯宾诺莎或德勒兹而言,人的特性(本质)就是它的行动。因此,“身体的结构(组成方式)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就等同于“一个身体能够做什么?”这样的问题。“一个身体的结构就是在其之中诸多关系的组合。一个身体能做什么符应于这个身体可被影响的能力之界限与本性”(《斯宾诺莎》 216)。身体,只能在诸身体的关系中,只能在同其他诸身体的相互影响中,只能在它对其他身体的行动中,去寻找它的组织和结构。身体,不应该囚禁在身体内部。
人的本质就是它的所作所为,也就是欲望的冲动,是动态的情感活动。斯宾诺莎的这一论断,在尼采那里,就变成了生命就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就意味着权力总是和权力处在斗争和对抗之中,权力总是关系中的权力,权力总是有它的反动力,权力总是力图战胜其他的权力。而在德勒兹那里,就变成了生命就是“欲望机器”,欲望机器的特征就是欲望之间永恒的连接,永恒的生产,永恒的创造和永恒的流动,欲望通过流动而同其他的欲望发生关联——这不就是斯宾诺莎的情感运动(affect)的特征吗?它们都永恒流变,毫无中断;这也是尼采权力意志的特征:力和能量永恒轮回,此消彼长。就此,情动(斯宾诺莎),权力意志(尼采),欲望机器(德勒兹),有一种令人吃惊的亲密谱系:它们都是对生命的描述,并由此界定了存在的特征,界定了人的本质。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身体和心灵并未彼此分离。斯宾诺莎明确地说,心灵不是对身体的管控,身体也不是对心灵的管控,它们谁也控制不了谁(斯宾诺莎 99)。这与其意味着它们的相互分离,毋宁说意味着它们的相互同一。身心的活动是同一的,它们统一在力的概念中;最后,生命就是力的无穷无尽的变化。这种力(存在之力或活动之力)在斯宾诺莎那里是跟情感结合在一起,在尼采那里,是跟意志结合在一起,在德勒兹那里,是跟欲望结合在一起。也可以说,情感,意志,欲望都是力,或者说,它们都是力的内容,是力的具体化形式。这一由斯宾诺莎开拓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和经验论是对意识哲学和理性主义的强大偏离。
这是斯宾诺莎—尼采—德勒兹对人的定义。这也是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康德和现象学的回应。如果说,斯宾诺莎的哲学是为了对抗他的同代人笛卡尔的话,我们可以将德勒兹和他同时代的结构主义对立起来。德勒兹的这个时代,正是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和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结构主义时代。对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结构主义者来说,主体当然和意识、心灵无关——这是他对笛卡尔传统的摆脱,但是,主体也与力无关,主体没有力,没有意志,没有情感,没有欲望,主体被结构吞噬了,是无所不在的结构在决定和操纵主体,主体是深陷结构牢笼中的主体,是野蛮而超验的结构的一个效应——这和德勒兹沸腾的欲望主体,和那个永恒变易四处串联充满勃勃生机的欲望机器是多么的南辕北辙!对阿尔都塞来说,主体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产物,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校,媒体,各种意识形态的宣讲和神话)塑造出来的。在阿尔都塞这里,主体虽然不是结构主义的效应,但是,主体是意识形态的效应——阿尔都塞仍旧置身于笛卡尔的传统,他相信主体是一个意识的存在,控制了意识就控制了主体。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德勒兹这是对福柯的回应,或者说,是对福柯的补充和呼应。如果说,阿尔都塞相信控制了意识就控制了主体的话,福柯则更多地相信,控制了身体就控制了主体。我们可以以学校为例来简要地指出福柯和阿尔都塞的差异。阿尔都塞认为学校的教育知识,教育课本,可以对学生进行控制,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操纵,这是对学生的大脑统治,统治了这些意识和大脑,就能统治学生的主体性,或者说,就能打造出学生的主体性。而福柯则认为,学校的体制,学校的管理方式,学校的纪律,也即是学校对学生身体的各种各样的规训——而不仅是学校课堂上的知识灌输——可以控制学生。通过纪律控制学生的身体,就可以造就学生的主体性。在此,主体被认为是身体的存在。如果说,阿尔都塞倾向于认为是意识决定身体的话,福柯则倾向于认为身体决定意识。如果说,阿尔都塞相信人仍旧是一个意识存在的话,福柯更多地相信,人是一个身体存在。在阿尔都塞那里,是意识形态召唤出一个主体,在福柯那里,是权力塑造一个主体。但无论是阿尔都塞,还是(早期的)福柯,都承认,人是一个被动之物,它要么是被意识形态塑造,要么是被权力塑造。
我们已经看到了,斯宾诺莎和德勒兹不是在意识和身体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而是将意识(心灵)和身体融为一体,融入到情感之中。情感行动(欲望)同时囊括了意识和身体。人既不是一个心灵(意识)存在,也不是一个身体存在,而是一个情感存在。更重要的是,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效应,不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寂静之物,而是一个情感的流变过程,是一个永恒的流变过程——这进一步地同形形色色的结构主义者、福柯和阿尔都塞区别开来。后三者都强调主体的静态性和被动性。而德勒兹强调的是情感的流变,强调的是人和人(物),身体和身体(物体)之间的平行感触。正是这种身体之间的感触和际遇,才形成了一个身体的状态。如果说,福柯的权力/身体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主体都是在一种不对称的构架中发生关系,是支配和抵抗,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的话,斯宾诺莎和德勒兹则强调一个内在性关系,一个贯通性的平面关系。身体和身体(物体)之间没有等级,没有操纵,没有统治,相反,它们是相互的感触,是一种内在性的没有缝隙的接壤,是接壤的刺激和招惹,是关联性的一波一波的煽动,是触碰之后的回音和共鸣。主体(身体)的情态(affection)来自这种相互之间的触碰和感染。这种情感关系并不寄托在权力的对抗技术和意识形态的询唤技术中,它仅仅是身体和身体触碰后的厌恶和吸引,是夹带痛苦的憎恨和充满魅力的吸引。我们再举一个家庭教育的例子。如果父母总是跟孩子灌输各种各样的“意义”,从而让孩子理解和接受这些意义,并且根据这些意义来自觉行事的话,这就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方式;如果父母制定规则,违反这些规则就给予严厉的惩罚,通过体罚的方式来管教孩子从而让他们不得不驯服的话,这就是福柯的规训方式;如果父母通过自己的情感触动,也即是所谓言传身教来打动孩子和影响孩子的话,这就是德勒兹的情动方式。人们可以在金庸小说里面的丐帮中,在《三国演义》中刘关张的桃园结义中尤其是三顾茅庐的故事中,在水泊梁山的草寇兄弟中,在各种类型的非法黑帮江湖中(我们有大量的香港黑帮片为证),都可以看到是情动(情感)在构造主体,主体正是在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感染中形成的。是情动(情感)在发挥主导作用,是情动(情感)构造了主体性,是情动(情感)最初串联起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构成了一个内在性平面,一个非等级性的平滑空间。这个空间无关意识形态,无关权力,甚至无关利益。或者说,意识形态、权力和利益是奠定在这种情动(感)根基之上的。这个共同体的组织者是个充满魅力之人,他的组织技术是以情动人,他有强烈的感染力(无论是刘备还是宋江都是感染性的超凡魅力之人)。事实上,许多大选中的政治家并非依靠理念获胜的,而是依靠他的情动(情感)魅力获胜。这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反过来,我们也会看到相互排斥的身体,每个人都会遭遇到敌人的身体,令他莫名地厌恶的身体,令他想与之战斗的身体。很多情况下,我们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对立,不是因为利益的对立而反对敌人,而是因为身体的对立而反对敌人。或许因为身体的对抗和情感的排斥而产生了战斗。
四
如果我们都是对外的随时敞开的情感主体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情感自动机(auto-affection),“作为情感自动机,在我们之中始终存在着接续的观念,伴随着此种接续,我们的行动能力或存在之力也在一条连续线上以一种连续的方式得以增强或减弱。这就是我们所谓的affectus,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存(exister)”(《万塞讷》 8)。这种接续的连续线正是生成(becoming)之线。生成意味着绵延,没有任何中断的绵延。情感在生成/流变,行动力和存在力也在生成流变,我们也可以说,生成不再是抽象的宇宙大法,它获得了具体的内容。什么在生成/流变?是情感在生成/流变,是存在之力在生成/流变,是欲望在生成/流变。这到底还是回到了生命本身。这个主体/生命的存在是情感,而情感则在流变,是永恒的生成流变,是一条连续线上的生成流变。情感和力和欲望就在这种柏格森式的绵延不绝的线索中流变。情感既在时间中流变,也取代了在柏格森那里的时间的主角位置。这种流变和生成,使得情感永不确定,它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聚集于一身,它们同时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们处在从潜能向现实的永恒转化中,它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保有一种持续的撞击。也就是说,情感的流变中既有着趋势,也充满着强度。“斯宾诺莎关于情感的问题,提供了将运动,趋势和强度这些概念交织在一起的方式:在什么意义上,身体和它自身的变化一致,在什么意义上它的变化与它的潜在可能一致”(马苏米 20)。
因此,情感的生成/流变,并非一种空洞的生成。它们有一种内在的张力和强度。尽管不存在着时间的终点,但是,它存在着强度的限度。快乐能够无限地增加吗?活动之力生存之力能够无限地强化吗?反过来,悲苦能够无限地强化吗?有没有一种无限度的悲苦?或者无限度的快乐?这是德勒兹跟随斯宾诺莎提出来的问题。情感总是一种感染和被感染,承受和被承受的过程。但是,一个人有自己的情感的承受限度,跨越了这个限度,就是失败,终结或者死亡。所以,一个人务必认识自己的情感极限,也就是说,最大的情感强度。只有这样方可称得上明智。根据斯宾诺莎,我们是从情感活动来界定人的本质,但是,情感活动有它的强度,有它的承受能力,因此,德勒兹更进一步地补充说,“每个事物,无论物体还是灵魂,都是由某种承受情感的力量所界定”(《万塞讷》 13)。情感不仅在活动在流变,它还有其强度和极限,它有影响和承受的极限。我们要明确这点,这至关重要:嗑药会令人产生巨大的快乐,高强度的快乐,但是,无限量的嗑药就是情感强度极限的突破,它会令人气绝身亡,存在之力超出自己的极限就会崩溃。一顿美食,令人胃口打开,但是,如果狼吞虎咽,放纵自己的嘴巴,就会让胃爆炸。同样,不幸的遭遇,比如我们碰上了SARS病毒,我们的身体之力就会衰减,存在之力和活动之力就会急剧下坠,直至衰竭。我们接二连三地遭遇不幸,就会被悲愁所感染,被痛苦所吞噬,深陷忧郁,直至从高楼坠毁——我们可以想象德勒兹晚年所遭遇的痛苦,他的身体痛苦,肺的痛苦,难于呼吸的痛苦超过他了情感耐受的极限,以至于他从楼上坠落。痛苦和悲愁最终毁灭了一切,不仅是身体,而且是当代最伟大和最奇诡的哲学——德勒兹的经验和他的哲学有一种悲剧性的吻合。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情感强度的极限何在。我们不能越过这个极限——无论是快乐的极限还是痛苦的极限。
但是,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悲苦,在什么情况下会快乐呢?“不难理解,那个物体/身体之所以能令你产生悲苦的情动,唯一前提是它对你的作用处于一种关系之中,而后者与你自身的关系不合”(17)。相反,一种快乐的情动,即是施与你身体情动的身体/物体与你相吻合相适应。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独裁者和神父是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的,他们站在绝对高位,影响你,打动你,甚至是抚慰你,但你完全没有和他们相和相协调的机会。他们站得那么高,就是试图让你垂头丧气,低沉,下坠,从而失去生命活力和存在之力,让你彻底失去主动性。让你处在一种被奴役的状态。这就是“地狱般的同伴,暴君和神父,生活的可怕的‘判官’”之所为。“他们创立了对悲伤,对束缚或无能,对死亡的崇拜。他们不停地抛出悲伤符号,并将其强加给别人,他们将这些符号视为理想和欢乐,呈现给那些病入膏肓的灵魂”(《批评》319)。但是,我们已经反复地说过了,快乐和悲愁这两种对立的情感往往交织在一起。我们同时承受不同的身体(物体)的影响,因此,我们常常会同时感到快乐和悲愁。我们在一个瞬间同某一个身体(物体)相适应,同另一个身体(物体)不适应。或者,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一个身体(物体)作用于我们,但是它会给我们同时带来快乐和忧愁,它在某方面和我们的身体相合,在另一方面和我们的身体不相合。
因此,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做?也就是说,身体该如何做?身体应该同身体做斗争,“在这斗争中,符号与符号相互对抗,情感与情感相互碰撞,好让一点点欢乐能得到保存,而这欢乐能让我们走出阴影,改换类型。符号语言的喊叫声铭刻下了这一激情的斗争,欢乐和悲伤的斗争,力量的强化和弱化的斗争”(319)。应该让积极的情动同消极的情动做斗争,让快乐战胜悲愁,让喜悦的光明驱散痛苦的阴影。让我们坚持一种快乐的唯物主义伦理学。这是从斯宾诺莎到尼采到德勒兹的伦理学要求。何谓伦理学?伦理和道德的区别在于,道德是法则,是教义,是规范,它逼问我们应不应该去做,它拷问我们这样做合乎道德吗?而伦理则是技术,是行为,是实践,它不是逼问我们该不该做?而是逼问我们,如何去做?怎样行动?斯宾诺莎,尼采,德勒兹告诉我们如何去做?去驱赶悲苦,保持快乐,强化力量,放声大笑,让爽朗大笑压倒那些令人心碎的啜泣。
或许,这就是德勒兹对海德格尔的隐秘回应。尽管他们都关注生存和存在(而非存在者),尽管都关注情感,尽管都将情感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但是,海德格尔难道不是一个悲苦哲学家吗?他不是对畏,烦,焦虑更着迷吗?在他那里,死亡一直盘踞在人们的心头成为下坠的重负。但是,对德勒兹(以及尼采)来说,唯一重要的,就是生活的方式。唯一重要的,就是对生命的沉思,而哲学只能是一种对生命的沉思,而远非一种对于死亡的沉思。它的操作旨在令死亡最终仅影响到我身上相对最微小的成分,也即,仅将其作为一种有害的际遇来体验。众所周知,当一个身体疲惫之时,陷入有害际遇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只要我还年轻,死亡对于我就确实是身外之物,确实是一个外源的偶发事件,除非是那些内发的疾病的情形。”(《万塞讷》 20)
而对海德格尔来说,死亡对我们的纠缠无穷无尽,那里没有快乐只有悲苦。对德勒兹说,我们需要快乐而无需悲愁。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德勒兹离世之际所写的极其简短的纪念文章中,敏锐地指出了这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的区别:“两人用一种极端的勇气思考了生存,以及作为此在的人,此在只是其存在的方式罢了。但海德格尔的根本调音属于一种紧张的、几乎金属一般的苦恼,在那里,一切的本己性和每一个瞬间缔结起来,成为了有待完成的使命。相反,没有什么比一种感受更好地表达了德勒兹的根本调音,德勒兹喜欢用一个英文词来称呼这一感受:自我享受(self-enjoyment)。”
参考文献
阿甘本:《除了人和狗》,白轻译,载《解放报》199 5年11月7日。互联网。2016年 12月 11日。 [Agamben, Giorgio. “Except Men and Dogs.” Trans. Bai Qing. Libération. 7 Nov. 1995. Web. 11 Dec. 2016.]
德勒兹:《德勒兹在万塞讷的斯宾诺莎课程(1978—1981)记录》,姜宇辉译,载汪民安编《生产·德勒兹与情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第 3 -22页。 [Deleuze, Gilles. “Les Cours sur Spinoza Vincennes, 1978-1981.” Trans. Jiang Yuhui. Producing. Vol. 11. Ed. Wang Minan. Nanjing: Jiangsu Renmin, 2016. 3-22.]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