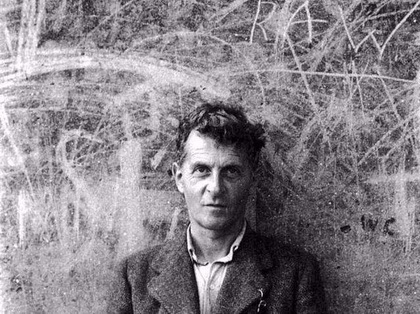本体论装置(下)
文︱阿甘本
译︱蓝江
1.12对“曾去成为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应是:在一个主体(sub-iectum),一个位于其之下的非本质的实存物与一个非实存的本质之间既然存在区分,那么如何能理解独特的实存?在这里,这是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出的问题,在那里,苏格拉底说源始的单纯元素并不具有定义(logos),但可以被命名(onomasai monon,201a 1ff.)在《形而上学》(1043b 24)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的弟子们提出了这道“难题”,他们认为我们只能对合成实体给出定义,但无法给出单纯实体的定义。
这个问题非常主要,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引导所有研究用的逻辑工具必须概括如下:“‘为什么’的问题经常会以如下方式提出:‘为什么某物是(或归属于,hyparchei)另一样东西’”(1041a, 11ff.)。也就是说,它消除了所有这一类的问题:用“为什么某物是(属于)另一样东西”的形式说明了“为什么某物是某物”(这样,并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而是“通过何种方式,让一个人成为这样或那样的生命存在物”,不是“为什么一座房子是一座房子”,而是“通过何种方式,让这些材料、砖块和房瓦成为一座房子”)。
一旦某物在谓述上没有指向另一样东西,这个装置就会遇上麻烦,当我们问道:“人是什么?”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一个简单的表达(haplos legesthai; 1041b 2),这个表达不能分析成主语和谓语。对于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给出的解决方案说明了ti en einai恰恰是用来理解单纯存在物或源始实质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什么是房子?”——必须以如下的形式来提问:“为什么这些东西叫做房子?”这或许是“因为所出现的东西(或归属于它们的东西)曾是房子的存在物(hoti hyparchei ho en oikiai einai)”(1041b 5–6)。在“曾是房子的存在物”(ho en oikiai einai)这个表达中,让我们联想起了ti en einai,过去时的“en”当然代表着房子是我们业已知道并十分明晰的实存着的某物(在几行字之前,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实存的东西十分明晰”(hoti hyparchei, dei delon einai)1041a 22)。但如果我们不理解这种实存方式在根本上是时间性的,并具有一个过去,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装置的功能。
1.13现在,如果我们问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年代顺序的时间问题(仿佛预先存在着某个主体可能用小时或天来衡量),而是类似于操作时间的东西,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时间,即心灵用它来实现了预设主体及其本质之间的关联。正因为如此,对ti en einai的两种可能的翻译都应得到坚持:“对X来说,去成为什么”指的是预设的主体(hypokeimenon),“是其所曾是”则试图把握它,让主体和本质保持一致。让它们能够保持一致的就是时间:“对于X来说,就是它曾去成为的东西”。这种装置对存在物进行的区分就是让存在物发生运动,让它具有了时间。本体论装置也是一种时间化的装置。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这是一种内在于主体的时间,从康德开始,他们以自动感触(autoaffection)的形式来思考这种时间。当海德格尔写道:“作为纯粹自身感触的时间构成了主体性的根本结构”(Heidegger 7, §34),我们不要忘了,通过暗含的与格,通过ti en einai中过去时的“en”,已经在主体(hypokeimenon,拉丁语译文的subiectum),在曾为现代主体性的逻辑位置上,亚里士多德已经指出了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时间。
1.14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清晰地说清楚在ti en einai这个表达中,将时间引入存在的问题。然而,当他解释(《形而上学》,1028a 30ff.)在何种意义上,本质(ousia)在知识(gnosei)上,在时间顺序(chronoi)上,是源始的(protos),是首要的。按照这个概念,因为在所有东西的概念中都出现了这个东西的本质(ousia),根据知识,因为一旦我们知道了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便可以更好地认识某物。对这个优先地位的第三个方面的解释,即时间上的解释,似乎仍然付之阙如。取而代之的是,亚里士多德用如下说法来概括了思想的任务:“事实上,当下和古老的问题已经被提出,它通常是怀疑的主题,即本质是什么”(kai de kai to palai te kai nyn kai aei zetoumenon kai aei aporoumenon, ti to on, touto esti tis he ousia)。按照逻辑顺序,如果这个句子可以解读为说明了源始实质的时间意义,那么它不可能只涉及年代顺序的时间。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的隐隐地引用了柏拉图《智者篇》中的一段话,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也将它作为题记:“当你们用到‘存在着’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pro tou)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eporekamen)。”(柏拉图, 《智者篇》244a)。存在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想去把握它,就会把它区分为我们相信我们能理解的“之前”(palai)和成为问题的“当下”(nyn)。对存在的理解,也就是说,已经产生了时间(海德格尔再一次提出了存在问题,这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的复活,并始终与他的问题完全一致)。
1.15 本体论装置是亚里士多德留给西方哲学传统的遗产,它将存在划分成本质和实存,并将时间导入了存在,这种装置就是语言的作品。语言将存在者主观化为主体(hypokeimenon),这就是让我们言说得以成的根基,即让装置运转起来。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主体(hypokeimenon)通常已经被专用名词所命名(如苏格拉底、爱玛),或者白代词“这”所指示。那么ti en einai,即“对于爱玛来说,曾是爱玛的东西”,表达了在实体及其语言中的存在物之间运行的关系。
由于让自己脱离了谓述,独特的存在物如同被预设的主体(sub-iectum,所有的话语都建立在预设基础上的主体基础上)一般退回到过去之中。作为我们言说根基的并确定了什么东西不能言说的存在物通常已经被预设了,通常拥有一个“它曾经是什么”的形式。在这样被预设的存在物中,主体一方面坚持它的优先地位,另一方面又是难以触及的。用玻姆的话来说,它之所以是无法触及的是因为——与此同时,尽管——它的优先地位,他之所以具有优先地位是因为——与此同时,尽管——它的无法触及性(Boehm, R., pp. 210–211)。正如黑格尔用意义的辩证法来理解《精神现象学》开篇的确定性一样,过去恰恰是让我们在语言中直接将此时此刻理解为时间,理解为“历史”的东西。言说独特存在物的不可能性——除非对它进行命名——就会产生时间,并将存在物吸纳到时间当中。(黑格尔的认为绝对之物就是主体,而不是实体,这恰恰意味着:在预设中,作为hypokeimenon的“主体”被消灭了,被推到后台成为预设,与此同时通过辩证法和时间,将它理解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体)。于是,他揭示了语言的预设结构,并将它变成辩证法的内核。谢林反而试图去寻找能抓住和中性化语言学预设的方法,但他没有成功。
.jpg)
1.16 现在,我们能理解,当我们肯定了本体论从根本上与人类发生学有关时,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与此同时,关键在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装置——或者在更一般意义上,在于本体论的历史演变。在这个装置中,仿佛在所有的新的历史衰落汇总一样,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联,即向智人(Homo sapiens)物种的生物,将人类的发生过程展现为“历史”。将纯粹实存之物(其是)与本质(所是)分离开阿里,在它们之间塞入了时间和运动,本体论装置重新实现并重复着人类发生事件,在行为以及认识的层面上重新开启和界定了每一个时代,通过做出某种限定,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被视为历史上的优先性,人类能够做出行为,并决定了人类能认识什么,能说什么。
按照特定的语言预设结构(按照马拉美的准确概括,“语言就是通过否定了其他一切原则来发展自己的原则”——亦即它将所有的源始之物变成了一个预设),在人类发生过程中,语言事件预设了在人类发生之前的非语言和非人的存在。也就是说,装置必须在生物的主观化形式下来把握,将它预设为我们言说的基础,也是语言从一开始就预设了并奠定了它的接触。在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中,主体(hypokeimenon),即纯粹的“其是”,命名了预设,即独特的不可谓述的实存,它必须同时被排斥并被包容在装置之中。在这个意义上,ti en einai的“曾是”(en)是一个更古老的过去,比所有的动词的过去时都要古老,因为它指向的是语言事件的源初结构。在名词之下(尤其是专有名词,所有的名词最开始都是专有名词),存在物始终已经被语言预设去指向语言。正如黑格尔曾十分完美地理解了在先性(precedence)在这里就是关键所在,它不是年代顺序的在先性,而是一种语言学预设的后果。
于是,这就是主体- hypokeimenon的状态的模糊性:一方面,由于主体不可言说,只能被命名和被指示,因此它被排斥,另一方面,只有在它的基础上,所有其他东西才能被言说。在这个意义上,这就是“其是”和“所是”之间的区分:ti en einai的表达试图消除这个分裂,为了消除它而包含着它(在中世纪的拉丁语表达quod quid erat esse,这个表达将“其是”(quod est)和“所是”(quid est)结合起来的意图十分明显)。
א 按照亚里士多德在《灵魂论》415b 13中提出的公理(“对于生命体而言,存在就是活着”(to de zen tois zosi to einai estin)),他以完全类比的方式,将存在层次上的问题转化为生命层次上的问题。和存在物一样,“我们也可以用诸多方式来谈论生命体”(pleonachos de legomenou tou zen; 《灵魂论》, 413a 24),在这里,其中的一个意思——营养性生命活植物性生命——与其他意思不同,成为其他意思的预设。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说过,营养性生命成为必须被城邦排斥出去的东西——与此同时也将它包含于其中——即将单纯的生命同获得政治上资格的生命区别开来。本体论和政治是完全对应的。
1.17 柏拉图的本体论范式则完全不同。他是第一个发现了语言预设结构的人,并将这个发现作为他的哲学思想的根基。下面这段摘自于《理想国》(511b)中的段落中(这段话非常有名,但也经常遭到误读),柏拉图用辩证的方法来描述:
那么也理解了可理解之物的其他部分,我的意思是指,语言本身(autos ho logos)要依赖于会话的潜能(tei tou dialegesthai dynamei)所能触及到(haptetai)的东西。它并不是将这些预设(hypotheseis,从词源学意义上说“那就是被置于其下,被当成基础的东西”)当成原型(archai),而是真正作为预设——作为一个站立于其上的垫脚石,让我们能触及到非预设的东西(anypotheton),通常万物的原理,一旦触及到它(hapsamenos autes),就会反转回来,把握从它那里得出的东西,可以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可见物,仅仅依赖于理念本身而得出结论,从理念到理念,并终结于理念之中。
语言的力量就在于将原型(archai)变成预设(“假说”,即词语预设作为参照的东西)。这就是在所有非哲学的话语中,我们所做的事情,在非哲学的话语中,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名称指向了某种非语言的东西,因此,我们将这个非语言的东西当成给定的东西,当成我们从此出发去探索知识的原点。相反,哲学家是这样意中人,他们意识到了语言的预设的力量,他们并不是将假说看成是原型,而是看成了预设,只能将这些预设看成是立足点来触及那些非预设的东西(anypotheton)。没有一丁点含糊其辞,重要的是,要理解柏拉图的方法与神秘实践没有丝毫关系,而是严格地限定在语言范围之中(正如他坚定不移地指出,关键在于“语言本身通过会话的潜能所能触及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意识到语言(logos)的预设的力量——它将思想必须触及的实在,变成了由一个名称或定义所指称的给定物——通过在非预设事物中使用语言,也即是说,使用了非参照性的方式(正因为如此,一旦涉及到关键问题,柏拉图宁可求助于神话和笑谈)认可并消灭了预设的假说(柏拉图称之为“阴影”(skiai)和“影像”(eikones),《理想国》510e)。
也就是说,哲学家将语言从它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他们不会将这些假说当成自然而然的东西,并试图从这些假说——我们知道,这些假说就是指意性质的词语——走向非预设的东西。这既是从阴影下解放出来的词语的理念,它不会预设出某种给定物的原型,而是试图触及它,仿佛它并没有被名称和话语所预设一般。哲学话语通常也只能由那些非预设的词语来推动,从感性的参照系下解放出来,柏拉图称之为理念,重要的是,他通常会在前面加上一个形容词“本身”(autos)的名词来表达这一点:如圆本身((autos ho kyklos,《书简七》342a-b),物本身。在这里的物本身并不是一种蒙昧不清的,并非由语言所预设的非语言的东西,而是一旦我们注意到语言的预设性力量,语言便会从它的阴影下解放出来。“圆本身”就是“圆”这个词,因为它不仅仅指向了那个感觉上的圆形,而且也因为它本身也表示着它。唯有当我们消除了语言的预设性力量,我们才有可能让沉默的事物呈现出来:物本身和语言本身(autos ho logos)都与这一点有关——他们仅仅通过意指关系和再现关系的空缺统一起来(一个词只能通过一个再现性的空缺来表示它自己——于是“触碰”的隐喻:这个理念是,词语并不指意,而是“触碰”。也就是说,在接触中发生,它展现出某物,同时也揭示了它自己——回想一下《灵魂论》的423b 15对于触碰的界定,即它不是“通过媒介(metaxy)”而是“同时作为媒体”来感知。)
在这个意义上,科耶夫是对的,他说道,哲学是一种话语,在谈论某物的时候,也谈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正在谈论某物。然而,显而易见,这种说法并没有完全表达出哲学的任务,因为这只是一个出发点,从此开始,各种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的角度才成为可能。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只有消灭了语言的预设性力量,我们才能触及非预设的东西,而亚里士多德——他之后就是黑格尔——则相反,他们辩证法的基础恰恰就是语言的预设性力量。
1.18 本体论所思考的存在物,是被言说的存在物,在语言中被追问的存在物,也就是说,在根本上它是一种本体-逻辑。在亚里士多德的装置中,在做出区分之后,这一点一览无余,即区分了主体(hypokeimenon),即置于其下作为根基的东西(被命名或被指示的独特存在物,它之前没有被一个主体言说,而是成为了所有话语的预设)和在它的预设基础上言说的东西。在ti en einai中,亚里士多德试图思考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将被他区分开来的东西再次联系起来:存在物就是曾经在语言中并被语言所预设的东西。也就是说:实存和同一性是彼此意志的——或者说,它们通过时间达成一致。
这样,这个装置,即作为历史优先性的装置,为西方历史开启了一项任务,这个任务既是思辨的,也是政治的:如果存在物在语言中被区分,且难以挽回地分裂了,如果可以思考独特实存之物的同一性,那么这种既被区分,又彼此关联的同一性关系,也有可能奠定了一个政治秩序,一个城邦,不仅仅是一个动物的牧场。
但是,真的存在这样一种存在的关联(既彼此区分,又相互统一)吗?或者说在存在追踪有着明显的无法弥合的裂口?这个统一体产生了一个过去,并为了让它不至于存在明显的问题,需要引入时间。在ti en einai中,拥有这样的形式:“对于这个实存物而言,它曾经是什么(或怎样活着)”。过去衡量着时间,而时间必然会让自己慢慢浸入到作为主体(hypokeimenon,这个实存物,tode ti,或第一主体)的存在实存规定和在存在中所保留的东西,存在物与自身的同一性之间。借助时间的方式,实存被等同于本质。也就是说,存在与实存之间的同一性关系是一个历史-政治任务。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考古学任务,因为它必须要理解是一个过去(“曾是”)。由于历史试图接近当下,那么历史通常已经成为了考古学。本体论装置由于是在年代顺序上发生的,也是一种“历史发生学”,他生产出历史,并让历史运转起来,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获得历史。政治与本体论,本体论装置和政治装置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因为它们为了实现它们自己,需要彼此依存,相辅相成。
א 在这个意义上,存在和历史是密切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这里也证成了本雅明的公理,按照本雅明的说法,所有拥有自然本性的东西(即存在物)都有着历史。再看一遍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说法,“自然正在通向自身的路上”,我们可以说,历史就是自然通常自身的道路本身(和日常生活中的说法不同,它并不是某种与自己相分离的东西)。
1.19 在《神圣人》第一卷的末尾,我在政治的时代状态和本体论的状况之间做了类比,这个类比是在一个激进危机的基础上界定的,这场危机挑战了我们可以将本体论-政治装置的各个项区别开来并关联起来的可能性:
今天,在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界定中,bios恰恰是作为本质处于zoe之中,即处在(leigt)实存之中。谢林认为一个存在物仅仅就是它的纯粹实存,在这个思想中表达了他的思想最典型的范例。不过,一个bios何以仅仅是它自己的zoe呢?一种生命形式如何把握构成西方形而上学任何和难题的“单一性”(haplos)呢?(Agamben 4, pp. 210–211/188)
实存与本质,实存存在物和系词存在物,zoe和bios在今天被完全分开,或者说完全彼此崩裂了,将它们关联起来的历史任务似乎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神圣人的赤裸生命是一个无法还原的本位(hypostasis),本位出现在它们之间,并证明了不可能将它们等同起来,也不可能将它们区分开来:“对X来说,它曾经是什么或怎样生活”现在仅仅是赤裸生活。同样,在时间中——既是年代顺序时间,也是操作时间——它们曾被联系在一起,现在时间不能再被理解为历史任务的中介,即在这个中介中,某个存在物可以实现与自己的同一性关系,人类可以保障他们作为人的条件,也就是说,维持他们的政治性实存。亚里士多德本体论专制在大约两千年的时间里保障了西方的生命和政治,它现在无法再具有历史的优先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不会再在时间中反思从语言和存在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谋求稳定的人类发生过程。已经达到了世俗化的顶点,本体论(或神学)向历史的投射似乎变得不可能。
א 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试图——他恰好与亚里士多德的模式完全对应——将存在理解为时间,但他最后失败了。在他对康德的解释中,海德格尔肯定了时间是一种内在张力的形式,是一种纯粹的自身感触,他将时间等同于主我(I)。但恰恰因为如此,主我无法在时间之中理解自己。时间和空间一样,让经验成为可能的恰恰是我们无法体会到时间和空间,它仅仅揭示了它的自身体验的不可能性。为了理解主我和实践,所以就产生了偏差。这个偏差就是赤裸生命,它不可能与自我完全一致,在某种意义上,它经常会迷失,从来不会过上真正的生活。或者如果你们喜欢可以说,去生活恰恰就是这种自身体验的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性让某个人的实存和存在达成一致(这就是詹姆斯小说的奥秘所在:我们之所以能生活,就是因为我们迷失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可以表达出亚里士多德的装置的意图,即“成为你所是”的格言(稍微更改一下:“成为你们所是”),因为他赋予时间了一项永远没有尽头的任务,这就是悖谬所在。按照科耶夫的说法,这句格言毋宁重新用如下方式表述:“成为你向来所不是”(或“成为你从未成为的东西”)。只有以疯癫为代价,尼采才能在形而上学的历史终结处,相信他能够在《瞧,这个人》中说明“人如何变成那个人之所是”(wie man wird, was man ist)。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