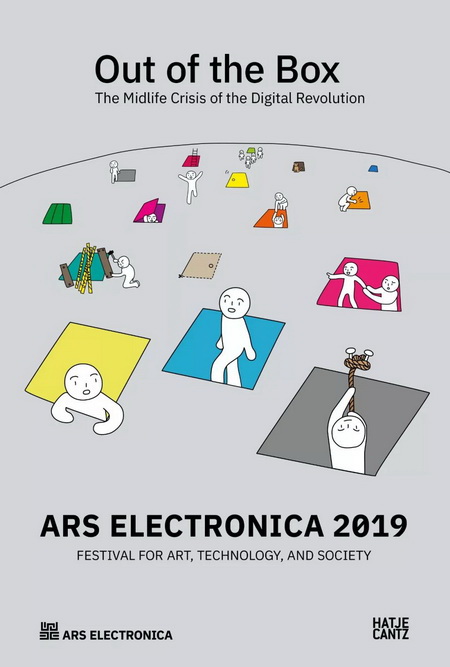如果你没有去到展览的现场,很难想象这个展览的效果如何。进入美术馆的现场,要从一个像桥一样的无数重拱门经过,你会被巨大的气流声所震住,转而观察它的造型。在这里边听觉作用于视觉。装置发出的声音就像强力水龙头或者直升飞机从头顶上划过,所以进来的人都没法不看看顶。来自荷兰的艺术家埃德文•万德•海德创作的《气流声场》无论从气势上或者是声效上都有惊人的表现。
托奥运的福,中国美术馆破天荒的举办新媒体艺术展。据说,这也是目前为止世界最大规模的一次新媒体艺术展。有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100多位艺术家参加。作品占满了美术馆9个展厅,整整一楼一层的空间,官方提供的数据展览占用4500平方米的室内空间展厅和2000平方米的室外空间,规模确实不小!
按照作品的大体类型,展览作品粗略的被划分为“身临其境”、“情感数字”、“现实重组”、“无所不在”四个部分。但是进入展厅,作品布置上并非按照这些单元来安排的。展览的现场显得更加灵活和多变。
娱乐和游戏心态
进入展厅,迎面而来的是一个用有机片围合起来的类似漩涡一样造型的有数百个带有各种图标的LED嵌板的作品《信息漩涡》,在一片红光闪烁中,人进入其中。这是近距离感受霓虹灯流动电子招牌的绝好机会,你可以感受到一点喜庆的色彩,一些都市化的气氛,从那些一个个明确的直观符号里边,我们可以感受到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所带给人们的一些“hi”的感觉。它告诉我们这就是新媒体艺术展。
从《信息漩涡》的旁边进入第二个展厅,是一件命名为《拿走》的作品,这是一个入门仪式,这个作品毫无疑问应该放在展厅的入口:迎面而来的是两个庞大的投影屏幕,右边的屏幕播放的是观众进入展厅的记录,左边的屏幕会截取进入画面的其中某位观众给他作出评价或者将多位观众的头像进行排列组合等,甚是好玩。观众会在摄像头范围内蹿来蹿去。这件作品是典型的气氛型作品。

声音绘画 金基哲 韩国 2001—2008 铅笔 纸 声音传动
《物体BVS》这件作品,会让你感受到一个艺术家天才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艺术家通过改良一个单人三维射击游戏,加入了一个虚拟现实的装置和动态的物体,艺术家把显示屏背后的故事立体化。作品重要的不是你参与玩耍游戏的快感,而是绕到图像视频的背后,你会看到发声装置。根据游戏的发展进程,玩家在遥控终端使用遥控设备时,会触动到装置产生机械运动,发出声音,灯光调节等。作者将机械化的、技术化的产品还原为手工和日常用品的概念。这些简单和熟悉的事物进入了诗话的语言,比如用在里边的扳手,电吹风,台灯,口缸等,为作品增加了不少亲和力。因为这种“土的办法”。参观的一位观众感言说:“太先进了”。
很多人在排队等着玩《北京加速器》这件作品:观者坐上后,使用手柄操作,使眼睛前方的显示屏小全景的速度和位置与大全景呼应吻合,观众根据自己的承受力,来调整速度。在旋转和图片的快速播报中,参与体验的人会有“目眩”的感觉。
《ZGODLOCATOR/第ZLL版》这个作品也是一个互动的作品,与其他的不同,它是一个小的可以俯视的作品,作品本身发出的一些怪声,让你有走过来看一看,玩一玩的心态。有一位十多岁的小孩说:“这件作品应该放在科技馆才对。”这位小孩判断的大体感觉是对的。艺术跟科学有时候真的是走得太近。这件作品是根据计算机硬盘上的磁原理来组合带有磁性的金属微粒。这些微粒通过磁刺激反应产生变形,观众可以通过旋转按钮来改变图案。

《没有地方》与其他热闹的作品相比,他是一件安静的作品,他属于一个单独的世界,也正是如此,作品被安放在一个单独的展厅,人们进入作品中,在作品的包围里,在你周边滚动的是一些各种各样的人为的、自然、历史的、当代的奇观,通过摄像头传出来。6个大视频,观众可以坐在里边慢慢地感受。“作品是一种休息”谁说得准呢?!
《飞艇攻击》这个作品很过瘾,很多气球在一个空间里飞,类似沙袋的外形,而另外一个被改良的气球在风扇的带动下在一个空间里边横冲直撞,他的轨道优美,类似被编程设计过。与《十六只鸟》的作品类似,人进入作品中间,观众对伸手可及的作品并没有放过,但大家对于“飞艇”都表示客气。看见他冲过来,人就躲闪了。不过,我认为对这个作品很好的体验是你进入其中,然后闭上眼睛,等待攻击,或者走神在无意之中,你会听到响声,然后猛一抬头,着实吓着!
到了《铁床之路》,就像进到了病房,十几个床有什么特别的呢?作品类似我们常见的按摩椅。电脑编程控制床架的升高降落,头部靠垫的部分起伏明显,这是“现代版”的病床。不过,有一些功能还要改善,你说呢?
在《永远年轻》这件作品中我们找到一些神秘感。这与片中传出的声音以及昏暗的灯光所设置。这个作品的人物特征,很难用一个现代人的概念来讨论,处理的手法是动画。作品充满金属感,这是一个能留下你细细看完的作品,作品动画与拍摄相结合,虽然语言不通,但却能够把握剧情的进展。旁边一位观众发出声音:“感觉有点像《骇客帝国》”。道具、服装都很精致,色调,光感都有专业的品质,在人物的处理上具有创造性,“唯美”这个词开始出现,是音乐、光与影的赞歌。这是一个关于死亡与重生的故事,权力与服从的较量。
整个展览犹如一个大型的互动装置或者说游乐场,人在里边迷失,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在里边呆上一整天。展览里边好玩的作品确实太多,在这里不容一一数出。
观念的有效性
上边的评述,无非都是一些戏言罢了,大家不要往心上去。如果大家觉得看到作品,却担心把握不好,最好就是去买上一本与这个展览相关的口袋书或者租用解说器。那里边会有一些简短的关于艺术创作背景以及作品的构造和主旨是什么的介绍。愿意那样做的人应该算是好观众!不过误读是允许的,艺术由过去有距离的观看,到参与,观众进入到作品里边,成为艺术的一部分。艺术由过去的单一视觉感受,到现在的视听结合,产生互动强调观众的参与感,向综合体验型转换,在这个展览中这一类型的作品占据了80%以上。面对这样的作品,观众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作者那样说,我也可以偏不那样想。每个人在其中都可以吸收自己认可的部分。
不过,顾及批评的严肃性。我们可以就某件作品展开讨论。比如加拿大大卫•洛克比的《拿走》这件作品,我前边所说的并非是作者的本意,作者的本意是:“左侧从地面以及墙面等多角度共同搜集参观者的足迹,……众多图像制造出一种混乱的火热的场面,既可以被理解成与统计学有关的展览策划(大部分的人选择站在哪里?人们会走动吗?),也可以看作是针对每一个参观者的参观纪录。这些图像具有高度社会化含义,并且极为混乱。右侧(即右侧的屏幕上)是为参观者准备的目录,……他们的头像会被放大,同时会出现评论他们的形容词(例如‘饥饿的’、‘相关联的’、‘可信任的’)。最后参观的200位观众的头像被排列成矩阵,……右侧的这种展示充满解析,同时也是高度秩序化的甚至是让人产生一种胁迫感。”可以看出这真是复杂,人们如果要把意思都弄明白,也会想回家去睡觉了。作品的观念并没有能够像作者想象的那样,可以完美的传达出去。观念在没有完成之前就失去了观众(参与者)。从观念来说,这件作品无疑是失败的;又比如:《情感动物》——作品像半个土豆一样的东西,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摸上去有粘糊糊的感觉,可能是材料本身,也可能是碰得人多了。这件作品只是看是不能够传达作者的意思的,需要有人去挤压它。看说明才知道,原来艺术家这个“土豆”是一个机器人,挤压后,“水从藏在作品基座上的水缸中流出”,我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可能轻按已经不能够出水了,有人用拳头去挤压,旁边就有观众说“他痛了,这么用力干什么?!”作品的观念直白的真像一杯白开水!而艺术家所表达的是“作品充满了创作力的直觉表达,是艺术家与观众跨越科学与艺术的逻辑。作品使人们在情绪上体验到了自然领域的‘潮湿’概念与电子领域的‘干燥’概念。”——我真的是要晕了;还有《对视》那件作品,图象确实太小了,艺术家所要表达的诡异的感觉,观众在没有能够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前就开始去寻找新的兴趣点……

当然,也会有很突出的作品,比如前边我所提到的《物体BVS》,人们围绕着作品转一圈就会发现这些意义的层面。作品有揪心的吸引力。再比如《叙述之声》,这是史诗型的作品。观众进入展厅,就想坐下来观看,就像看戏(这种感觉与艺术家的设定是一致的,这是一出“源自格陵兰岛的录像皮影戏”),立体的现场有真实感,在一定的程序控制下主角一一出现。这是一个集图像、雕塑、声音和录像多维一体的活动装置或者说音像合成作品,作品由陈旧的机械于新的技术构成,音响和灯光得效果都运用出色。这件作品与多数新媒体作品不同,装置部分每个局部和单件作品雕塑感都很强,是件伟大的作品。作品打破和分离了通常的规则,打破原有形式,从结构、时间和空间的构成上体现出了新的创意性;在音乐和视频等的合奏下,能够共同营造一个好的氛围。艺术家用了三年的时间,在作品的形式和空间以及音效的运用中多次实验,才有了如此不同寻常的组合。看这件作品会有源自生命和意识流的冲动,人性的部分得以显露。
统观整个展览,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些作品总是在具体与抽象之间、在静态与动态之间,象征的或者异化的在平面或者立体的呈现下,通过实物与数字化的运用、概念化和方法论的合成里边,艺术家都有着不俗的表现。我们没有必要在“作者之死”或者是“读者之死”之间无休止的纠缠下去。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正是这种多元面貌,为我们展开了艺术本身宽广的胸襟。
在这种新型的体验型的作品里边,我认为我们很难用固一的观念去追加一件作品的价值。如果每件作品的背后都有社会的或者人生的现实意义的指向,那么人们就会很累。就像我们去迪士尼乐园,我们不是去为接受教育和反省自身去的,我们是去happy的。看新媒体艺术展,在国人的心目中这还是新的东西,尽管在国外已经不新了,很多隔行的人,就可以带着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好奇心进来,进入不同于我们日常在家守着电视机看的,在电影院看的作品,进入这种数字化的、手工与机械合成的这样一个体验馆,这何尝不是现实社会给人添加了各种各样的压力之后,一种放松和解压的方式。艺术是让人愉悦的艺术而不是让人紧张。艺术被过度的哲学化所粉饰,艺术还原为“愉悦”,有其必要性。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谈,从观众对一个展览的期待值或者艺术家对观众的期待值,在这一个展览里边都会得到一个好的平衡点。创作论和接受论的区分有利展览的传播的有效发挥。新媒体艺术展区别于游乐场、区别于风情园,就在于它的范畴始终是 “艺术的”。对于这个展览的推介词其实我只是想说:这个展览要不要看?回答是肯定的!
关于艺术创作以及艺术家的话题
技术化是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创作的显著特征之一。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的是,这个时代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在现代化的征程上也体验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技术运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高科技产品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台电视的发展,从我们每天都依赖的手机款式和功能不断更新,我们体会到了这种科学带给我们的惊奇。我们在怀疑这些产品的供应商们过于了解和把握我们的消费心理而频频出新的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了在潮流的屁股后面只能是紧追不舍,我们不得不叹服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惊奇。

飞艇攻击 知识机器人研究小组 瑞士 2005 室内飞艇,15个气球,音响系统
这一点上,科学与艺术显现出了惊奇的一致性。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让人们将他等同于艺术。这也是新媒体艺术在科技文明产生以来得以产生发展壮大,也就是这些年来技术革命,高科技含量被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频繁运用的原因所在。正因为技术与艺术本身的纠缠,对于艺术品中的技术问题,近年来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比如,技术是否重要的问题。技术固然重要,没有技术就没有实现表达的可能性。或者说技术运用得如何,很大程度会影响到作品的好坏。持技术并不重要这一观点的人,大多来自于作品的完成需要借助“外力”。
由于技术的发展,艺术家原有的技术基础没有能够跟上,在这一现实处境下,艺术家请技术人员来协助完成,成为一个必然。当然,这不是最好的选择,或者说不是产生一件好作品的最佳处方,从这次参展的艺术作品看,很多作品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果。比如创作《飞艇攻击》的是知识机器人研究小组;《没有地方》是分别来自英国、美国、瑞典的马瑞克•瓦尔克扎克、马丁•瓦丁伯格罗利•索罗门、乔纳森•芬博格四人合作的作品;《物体BVS》是exonemo小组合作完成的。整个展览45件作品中就有10件是以合作或者小组的名义创作的。强强联合符合这个社会的时代精神。这样合作的好处是发挥每个成员的专项所常,这也是新媒体艺术领域出现的一个重要特征。个体的局限性在未来的社会中会越来越明显。这是我的断言。
从这次国外参展艺术家的出身来看,他们来自工程师、机械师、平面设计师的种种领域,比如,亚当•萨姆莱•费斯彻(Adam Somlai-Fischer)是建筑师和交互设计师;马瑞克•瓦尔克扎克(MarekWalcazk)是一名建筑师;马丁•瓦丁伯格(Martin Wattenberg)是一位新厄米提艺术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彭特•斯约林(Bengt Sjolen)是软件和硬件的设计师;伊夫•奈特扎米视觉设计专业毕业……
艺术家产生的群体已经不在限制于艺术院校的毕业生了,“人人都是艺术家”,英雄不问出处。重要的是一个艺术家将想法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材料也不是一个限制,任何材料都可以纳入艺术创作的范畴,那么新媒体,也不是一个重要的值得讨论的范畴了,艺术媒材的问题不再是一个重点,重要的是艺术家如何创造作品的结构和形式的同时怎样赋予一件作品以生命力。

就国内的艺术家而言,更多的是限制于观念艺术的泥潭,在作品观念之后如何向数字化和媒体化转型,这是国内艺术家的困境。在人人都可以“艺术”的时候,这种激进的精神只是在原有的旧的美术系统产生,这一系统的艺术家失去了好好学习技术和创作一件作品必须的动手能力的阶段。所以,相比之下,国内的艺术家在这次展览里边,就技术运用的层面来说,就弱一些。比如,缪晓春的作品《虚拟最终审判》,他的作品与其它动态型的作品相比,放在新媒体的展览上,他的作品自然显得弱了。杜震君的作品也显得过于图解和生硬化。如果作品本身都不能够抓住观众,那么观念就离得更远了。
怎样引起高科技人才的艺术创作热情,怎么运用他们自身的技术优势,创作出具有时代特征和艺术气质的作品,在国内来说可能还需要一个阶段。我们所看到的物理现象的运用、化学反应等都被运用到了艺术创作之中,今天手法和材料都不会受到限制。今天是一个不问英雄出处的年代。在这些花花绿绿的新媒体艺术时代,好的艺术重要的是如何超越艺术自身,艺术如何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时代意义的探寻,怎样才能够从艺术里边实现大文化上的前瞻性与使命感。这也是我们去看这个展览的作品,除了体验、评判之外,调动起创作的热情,也是一个收获和目的所在吧!中国美术馆这个展览的到来,必将会产生一些催生的作用。

我们也应该给予开创这一艺术领域的先驱正名。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就是艺术史的问题。比如,来自美国的华人艺术家蔡文颖,这次展览中看他的作品不怎么样(这次他做的作品《双泉•北京》是用两个水环安放在高处,水往下滴落,通过高频率闪烁灯的照亮,产生了水与光的合影。在这个展览里边,他的作品显得过于简单。)但是他。他已经80多岁了,他于1953年美国机械工程和艺术专业毕业,自二十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创作由电子和计算机控制的雕塑。蔡文颖的作品已经在世界各地的一流博物馆展出并被收藏,其中包括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巴黎的蓬皮杜中心和伦敦的泰德美术馆。他的雕塑利用金属、玻璃纤维、和光,来重现职务状的有机形体,在颤动和眩目中,配合周围黄精种的声音和音乐翩翩起舞。学术界的评定是这样的:“蔡文颖对世界的贡献,在于他能用他开创的动感雕塑(cyberneticsculpture),捕捉和再现了大自然的辉煌。”某些作品,我们需要还原到历史的处境当中去。
正是在这样一些一代代的艺人之间所创作的作品中,我们得以窥见不同时期艺术发展的思想脉络,他们对文化的反思以及艺术语言的探索,他们在艺术社会化、公益化的道路上所点燃的星星之火,他们在自我与责任之间的锲而不舍都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这种艺术的自由精神和天下为“美”,使我们这个时代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显得更加充盈和高贵。
林善文2008/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