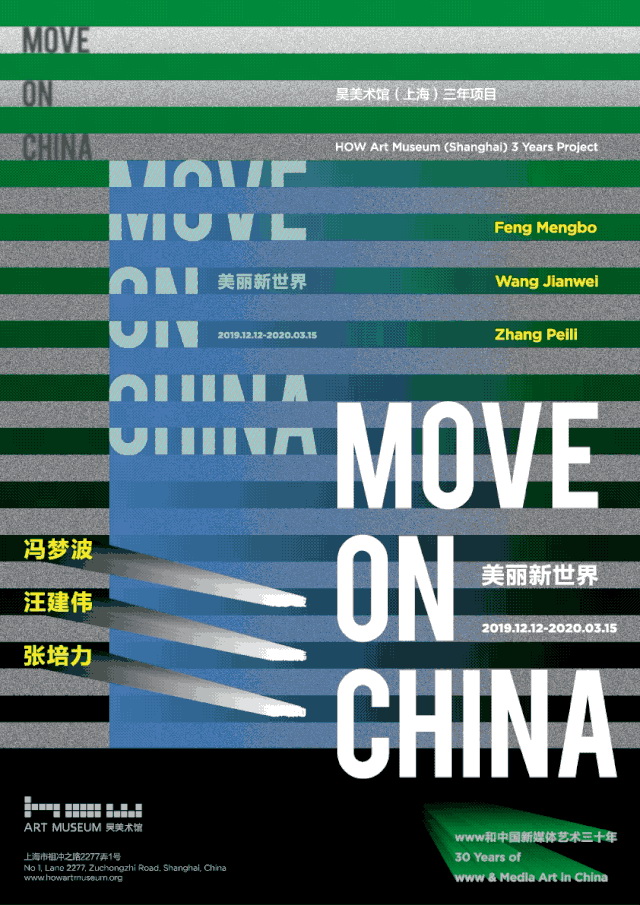Massimiliano Gioni
Massimiliano Gioni,这位去年十月在新美术馆上任总策展人的人,并非把全部关注的重心放在那些时髦的玩意儿上。他既不是被钉在某个“ism”理论钉板上的老古板,也无心和詹姆士·弗兰科或者拉瑞·高古轩等人称兄道弟。事实上,他自己表示,想要挖掘在切尔西或布鲁克林之外的艺术:“我最早来到纽约的时候,对于所感受的东西都非常有兴趣,尽可能地多学多看。如今我倒是很想知道纽约有什么没有的。”
这听上去就像美术馆的长期信条(比如“新艺术,新想法”)。如果说他真的能把活力带到那些画廊中去,Gioni将是新美术馆急切需要的那个人。自从新美术馆2007年在Bowery重建,这座34岁的建筑总是令人心里没底儿似的。又冷又小的展厅对比建筑外观的闪亮,成为众人诟病的重点。很明显,艺术内部人士的金钱政策依然起效:一个专门为希腊亿万富翁Dakis Joannou所做的展览恶评如潮,但是画廊还是得靠着这些人,比如Gavin Brown。Gioni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就像呼吸了一口正直的新鲜空气一样,被认为能够拯救这所生病了的机构。“如果他做不了,那么在现阶段就没人能做了。”一位主策展人这样说。
新美术馆,这所没有一个常设展的机构,几乎是站在了流行艺术与艺术世界的孤岛中间(从一定程度上说,比起美术馆,它更像一个体积很大的画廊)。Gioni努力把他的身份从一些东西中抽离出来:“有许多与我的构想相符的东西,也有必须去对抗的。”他做的两个展览,一是对住在伦敦的观念艺术家Gustav Metzger的致敬。这位艺术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人们所熟知,成就即是造就了艺术,并逐渐摧毁了它。另外一个是对于泰国导演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的致敬,他的电影梦幻并带有冥想的意味,并非适合所有人。
“他的角色很重要,”独立策展人Francesco Bonami说。他也是在2003年提议让Gioni组织威尼斯双年展小馆的倡议者:“一定程度上说,美国艺术有它目光短浅的一方面。Gioni正在与它的封闭性作斗争。”这么说的还有Gioni的好友和合作者、艺术家Maurizio Cattelan:“他十分想让艺术馆成为更好的地方,能展示更多不被立即理解的、未知的东西,并与那些已知的形成平衡。他知道纽约缺什么,以及新美术馆少了些什么。”

Gioni on the New Museum's terrace, next to Isa Genzken's Rose II (2007)
这可能是因为,Gioni并非生来就在艺术行业。他出生在米兰郊外附近的一个小城,打个比喻,就像是纽瓦克市(美国新泽西州港市)。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组过一个受到Sonic Youth影响的乐队,并出售自己做的艺术T恤。“那儿有很多迷人的怪人,人们都接受他们。”Gioni这样形容他的少年时代。在西20号大街,他和几个朋友鼓捣了一个画廊名叫Wrong Gallery。刚开始的时候,它很简陋,只有上着锁的大玻璃橱窗。“没有要卖的,”Gioni说。他和他的伙伴能免费租用那个空间,条件是他们要展出这块地主人妻子的油画作品。
他们在里面开展的项目既有失体统又趣味横生。从声音装置到光线作品,还有房顶上写着“去你妈的,我们关门了”的贴纸,逐渐,这个小空间得到的关注越来越大,甚至那些策展人也开始有兴趣。2006年他们参加了柏林双年展,以及后来在韩国光州的一个双年展。The Wrong Gallery本身甚至被搬进了泰特美术馆呆了几年,自从它被从切尔西驱逐出去之后(它在2008年关的门)。
尽管Gioni是圈内人关注的热点,他自己还是有点儿孤独。他读了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书,比如《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些纳博科夫。“我认为把钱花在书上,与花在机票上同等重要。我很讨厌人们认为策展人就是个全世界范围的观光者。尽管这是你需要做的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它当然更包括学识以及研究工作。”他把那些能够飞来飞去的机会视为自己能看到更多古怪、被忽略的,以及暂时掩埋在地下的新艺术。
Gioni的下一个展览依然走的是上两回的路数,但是可能更宽阔一点。他说他想这个展览的事儿已经很久了。展览名为“Ostalgia”(编者注:直译为“骨痛”,但可能是从“乡愁”nostolgia这个词来的一个文字游戏),即将于7月14日开幕,将展出许多不为人知的欧洲艺术家的作品,主题是关于前苏维埃联盟。“最近,我对于那些被遗忘的东西很感兴趣,”Gioni说,“它们并不令人感到愉悦。在纽约,潜意识里,有种‘需要取悦什么’的趋势存在在这儿——太多了。我不想弄一些能让人们说出‘嘿伙计,一块儿来!’这样话的东西。在当今世界最终想要玩儿得彻底或激进,要么令人无聊,要么就得尝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