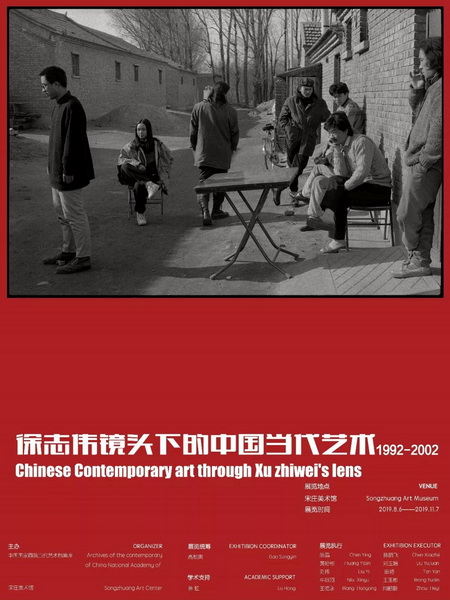本文译自Hal Foster, Rosalind Krauss, Yve-Alain Bois and Benjamin Buchloh, Art Since 1900: Modernism, Anti-modernism, Post-modernism,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2005, pp.22-31。选自沈语冰、张晓剑主编:《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文选》,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8年。
1.jpg)
▲ 本雅明·布赫洛
艺术的社会史
本雅明·布赫洛/著
诸葛沂/译︱沈语冰/校
新近的艺术史包括一些截然不同的批评模式(例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社会艺术史及女性主义),它们以各种形式相融、整合,这种状况在70年代以来的美国、英国艺术史家的著作中格外显著。假若并非完全无意义,这一状况有时使得坚持方法的纯粹一致性变得困难了,也就是说,难以在研究中独守某种单一的方法论立场。这些不同的独立分支,及其结合方式的复杂性,首先指向了那些宣称在艺术史阐述过程中,应将某一种特定模式视为唯一正当的圭臬或应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问题本质。而我们对各种方法论立场进行整合的尝试,同样消除了早期的理论苛刻,在先前的历史性分析和阐释的过程中,这种理论上的苛刻曾导致一定程度上的精密性。在方法折中主义越来越错综复杂、丛结交织的情况下,这种精密性现在看来已经不复存在了。
方法之源
所有这些模式在最初被构想时,都是为了取代那些早期的人文主义的(主观的)批评和阐释手段。这些模式得以创立,是受到那样一种渴望的激发:能够在更为稳固扎实的科学基础上采取方法和理解,来研究所有种类的文化生产;而不是受到另一类方法的刺激:这些方法对19世纪晚期各种各样或多或少主观的批评方法都存在着依赖,诸如传记式的、心理层面的,以及历史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
正如早期俄国形式主义者使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结构成为他们自己努力理解文化表征的构成与功能的模型一样,随后的那些试图以精神分析观点来阐释艺术作品的史学家,也设法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著作中找到艺术主题构成的地图。这两种模式的支持者争辩到,他们能对审美生产和接受过程产生可证实的理解,并且承诺,要在无论是对语言常规还是潜意识系统的运用中,将艺术作品的“含义”(meaning)锚定下来,他们坚持认为,审美的或诗的含义的产生方式,类似于其他语言常规和叙事结构(例如民间故事),或者,依照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Carl Jung)的理论术语,类似于玩笑与梦,症状和创伤。
艺术的社会史,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最初诞生时,便怀有类似的野心,即想要使艺术作品的分析与阐释变得更严格、更可检验。最为重要的是,早期的艺术社会史家[如英-德人弗朗西斯·克林金德(Francis Klingender,1907-1955)和英-匈牙利人弗里德里克·安塔尔(Frederick Antal,1887-1954)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将文化表征安置于现存的社会交往结构中,主要是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精神生产领域之中。毕竟,社会艺术史的哲学启示来自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最初针对的目的,就不仅仅是去分析和解释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联,同样也促使历史的书写本身——书写的历史性——成为社会与政治变迁的更大课题。
社会艺术史的这种批评分析的课题创造出了许多核心概念,我将进一步讨论它们;我也将尝试给出它们原初的定义,以及随后对这些概念的修改,以便认识到社会艺术史的术语递增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部分地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哲学概念的发展分化。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一些核心概念被提出来讨论的原因,并非因为它们在21世纪初是重要的,而是,恰恰相反,因为它们被弃之不用了,在现今和刚刚过去的年代里消亡了。这是因为,它的某些分析模式所坚信的方法就像所有其他方法论模式一样,已经过分武断了,尽管它们在20世纪的不同时刻,一度在艺术史的阐释和书写中占据短暂的支配地位。
自律性
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生)已经大体上界定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构成,而这公共领域里的文化实践的发展,就如同主体分化的社会进程一样,导致资产阶级个体性的历史建构。这些进程确保了个体的特性和历史地位,是一个自我决定和自治的主体。资产阶级身份的必要条件之一,便是主体体验审美自律性的能力,即非功利地体验审美快感。
这个审美自律性的概念便成为资产阶级主体性分化的必要组成,就像它也是文化生产的必要组成一样,这些文化生产遵循审美自律性的固有技术与程序特性,最终导向媒体特质的现代主义正统性。不出意科,在欧洲现代主义的第一个50年间,自律性发挥了基础概念的作用。从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计划,到马奈(Manet)将绘画视为感知的自反性(self-reflexivity)方案的观念,自律性美学的观点在19世纪80年代的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的诗学中达到顶点。唯美主义认为艺术作品是由纯粹自足和自反的体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将它看作是19世纪的艺术神学(theology of art)——创造出来的,这一观点导向了20世纪早期形式主义思想中的类似观念,后来这些观念成为形式主义批评家和历史学家论述绘画的自反性的套话。其范围从罗杰·弗莱(Roger Fry)对后印象主义的回应——特别是对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的作品——到丹尼尔-亨利·卡恩维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的分析立体派的新康德主义理论,再到克莱门特·格林柏格(Clement Greenberg,1909-1994)战后年代诞生的著作。任何试图将自律性转变为一个审美体验的超历史的、永恒的、即使不是本体论的前提条件的企图,无论如何都是很成问题的。当我们作细致的历史性考察时,便会清楚地发现,审美自律性本身的概念构成就远不是自主的。这是首当其冲的一点,因为自律性美学已经由启蒙运动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的超然/无利害关系(Disinterestedness)概念的总体性哲学框架所决定,尽管它同时又被用来反对随着商业资产阶级兴起而产生的经验的粗俗的工具化倾向。
在文化表征的领域里,自律性膜拜将语言和艺术的实践从神话和宗教思维中解放出来,几乎就像将文化表征从屈服于封建赞助人严格控制下谄媚奉承的政治附庸性和经济依赖性中解脱出来一样。当自律性膜拜随着资产阶级主体性从贵族和宗教的统治霸权中破茧而出时,自律性同样将那赞助的神权政治和等级制度视为有着它们自身的现实性。现代主义的自律性美学以此建构起社会和主体的界域,在此界域中,一种反对功利活动现实的对立观点,可以以开放性的否定、拒绝的艺术行动,来自由清楚地进行表达。然而,吊诡的是,这些作为抵制的行动——其不可避免的状况,就像普遍规律中的极端例外——却确证了总体工具化的体制。或许有必要确切地阐述这种悖论,即一种自律性美学成为自由开放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情境中非工具性经验的高度工具化的形式。
19世纪(从马奈到马拉美)是自律性美学的关键时期,对这一时期的真正考察将会使人认识到,正是这个悖论才成为他们绘画或诗歌天赋的事实上的塑形结构。既将现代主义表征定义为一种批判性的自我反思的高级形式,同时也将他们封闭而玄奥的创作之道视为对新兴的工具化了的表征的大众文化形式的吸收与反抗。这是很典型的,自律性观念不仅由资产阶级合理性的工具逻辑塑造而成,同时也抵制这种逻辑,在文化生产的领域,通过笃信经验主义的临界点,严格地执行这种理性要求。由此,自律性美学是促成对艺术作品体验的最根本转变的原因之一,本雅明30年代的文章,将这种转变称为从膜拜价值(cult-value)到展示价值(exhibition-value)的历史转化。他的这些文章已被普遍认为是艺术社会史的哲学理论的奠基性文本。
自律性观念同样把艺术品新的分配形式理想化了,而今,艺术品业已成为一种资产阶级物品和奢侈品市场中自由流通的商品了。因而,自主性美学由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逻辑产生,实际上又反抗这种逻辑。其实,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泰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1903-1969)在60年代仍然继续坚持艺术独立和审美自律,吊诡的是,这种自律性只能在艺术品的商品结构中发生。
反美学
彼得·比格尔(Peter Bürger,1936年生),在他那部重要的——尽管成问题的——著作《先锋派理论》(Theory of the Avant-Garde,1974)中声称,1913年的反美学(antiaesthetic)实践的全新闪现,是作为对审美自律的反抗而出现的。然而——依照比格尔的思路——立体主义之后的历史上的先锋派通常企图“将艺术整合进生活”,并质疑自律的“艺术体制”。比格尔察觉到,这种反美学理想居于达达主义、俄国构成主义和法国超现实主义叛逆运动的思想中心。然而,与其关注一个模糊构想出来的艺术与生活的结合(这种结合从未在任何历史时刻被令人满意地定义过),或关注对艺术体制本质颇为抽象的争辩,此时更有裨益的,恐怕还是关注这些先锋实践者自身所宣传的策略:尤其是对观众和观看中介的观念发起根本改变的策略,以及推翻资产阶级注重交换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审美等级制的策略,也许更重要的,是为国际无产阶级公共领域构想一种文化实践形式,这种公共领域在先进工业民族国家里刚刚兴起。
这一途径并不仅仅只能让我们更充分地鉴别这些前卫艺术活动,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一种技术复制美学(与自律性美学针锋相对)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开始幻灭的时代,即20年代的那一时刻崛起了。这种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起初被新兴的无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进步力量(如苏联初期和魏码共和国时的情景)所取代,其后则被大众文化公共领域的崛起而取代,或者由30年代的极权主义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形式,或者由文化工业和公开展览的战后体制所取代,这种文化工业和公开展览的体制,是随着美国的霸权主义与欧洲重建中很大程度上居于从属地位的文化建设而出现的。
这种反美学在各个层面上消解了自律性美学:它以技术复制替代了原创性,它破坏了一件作品的灵韵(aura),以及审美体验的沉思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对交往行为与共时性集体感知的渴望。反美学[如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的作品]将其艺术实践界定为临时性和地缘具体性的(而非永恒的),界定为参与式的(而非一种独有的知识优越形式的品质)。反美学在进行运作时,亦类同于一种实用美学来进行[例如,在苏联生产主义者(Productivists)的作品中],将艺术作品放置于一个承担许多生产功能的社会背景中,比如信息和教育或政治启蒙的功能,满足新形成的工业无产阶级观众文化上的自我构造的需要,这些观众先前既在文化生产层面上,也在文化接受层面上,被排斥在文化表征之外。
阶级、中介和激进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首要前提即为阶级和阶级意识的概念——它们是推动历史进程的最重要因素。在历史上的不同时刻,阶级都是历史、社会和政治变迁(例如,贵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20世纪最强大的阶级——小资产阶级,吊诡的是,它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阐释最忽视的阶级)的动力。马克思论证过,阶级自身由唯一的关键条件来定义:主体与生产资料相关的联系情况。
因而,生产资料的特别占有(或者,更重要的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控制)正是18世纪晚期和整个19世纪资产阶级阶级认同的构成条件。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无产阶级的鉴别条件则是,他们永远在经济、法律和社交上被阻绝,而而无法得到生产资料(当然,同时也包括教育资料以及对改进的专业技能的习得)。
有关阶级概念的问题,是艺术的社会史的中心议题,它关系到艺术家的阶级认同,也关系到与现代社会里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斗争保持文化上的团结以及模仿上的艺术认同,能否真的导致对革命运动或反革命运动的政治支持行为。对种种文化上的阶级同盟,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经常抱着相当的怀疑态度。然而,这种阶级同盟模式实际上决定了所有具有政治动机的现代性的艺术生产,因为即使有,也只有很少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真的来自那时的无产阶级生存条件。当我们考虑到独立艺术家的意识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变得激进起来时(例如1848年革命、1917年革命或1968年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当我们考虑到艺术家有可能在那样一个历史时刻,假想自己与被压迫阶级站在一起时,阶级认同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起来。但是,稍后,随着他们文化整合意识的唤醒,同样是这些艺术家,便有可能成为统治秩序的同谋,或主动肯定统治秩序,并完全成为维护文化合法性的供应商。
这同样指明了这样一个必要的洞见,即艺术生产的语域与政治激进主义或明或暗的关联,要比一般设想的艺术政治化论辩富有更为无限的多样性。我们不只是仅仅在一种政治意识或激进活动家的实践,与另一种肯定的、霸权文化[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美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所称]之间进行选择。然而,通过文化表征,我们可以看到,霸权文化的功能显然是去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及其知觉与行为模式,而对立性文化实践则表明抵抗这种等级思想,颠覆经验的特权形式,动摇视觉和知觉的统治体制,正如它们也能大规模地、明确地动摇霸权力量的统治观念一样。
假如我们承认文化生产的某些形式承担了中介功能(亦即,信息和教化的功能,临界控制和反制信息的功能),那么艺术的社会史面对的问题,是最危险(即使还不是达于危急状态)的洞见之一:假如文化生产形式要使其审美判断形式与政治团结及阶级同盟的状况取得一致,那么,一定只能举出很少几个英雄人物,在这些人物中身上,阶级意识、中介及革命同盟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确实可以确定的。这些例子包括19世纪的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和奥诺雷·杜米埃尔(Honoré Daumier),20世纪上半叶的凯特·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和约翰·哈特菲尔德,还有如20世纪后半叶的玛莎·罗斯勒(Martha Rosle)、汉斯·哈克(Hans Haacke)和阿兰·塞库拉(Allan Sekula)。
因此,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即服从阶级利益与政治革命意识充其量只能被视为现代性审美实践的一个例外,而不是必要条件,这就给社会艺术史家留下了一个艰难的选择。换句话说,要么就不去考虑那种现代主义任何特殊时刻最真实的艺术实践,无视这些艺术家及其作品,因为它们缺乏信奉、阶级意识和政治正确性;要么承认众多其他标准(除了政治与社会历史标准外),也进入(对艺术品的)历史与批评性分析过程的必要性。
由于无产阶级唯一的生产资料就是他或她自己的劳动力,它可以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拿来出卖,通过供给主体的劳动力,为实业资产阶级或股份企业生产出非凡增值的剩余价值,因而,劳动和劳动者这一景况,正是19世纪以来的激进艺术家们,从古斯塔夫·库尔贝到20世纪的生产主义者所面对的。然而,在极大程度上,他们并不是在图像志(iconography)层面上去正视它(实际上,他们几乎不表现异化劳动,这是现代主义的规则),相反,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永恒问题,即工业生产的劳动和文化生产的劳动是否可以、也应该联系起来,而且,果真如此的话,又如何联系——是类比的?辩证对立的?还是相互补充的?抑或相互排斥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最大范围内将这种联系理论化(社会艺术史家试图接受这种理论化):从断定主体构成是使用价值生产必不可少的因素的那种生产至上-实用主义美学(如苏联生产主义者与德国包豪斯、风格派运动),到一种明确的反生产主义(counterproductivity)美学(如超现实主义同时期的艺术实践),它否定“劳动即价值”(labor-as-value),拒绝任何艺术领域里的买卖行为。这种美学将艺术实践视为一种体验,在这种体验中,那种未经异化的和无用功的存在的历史可能性会闪光呈现,无论是对仪式、游戏与儿童嬉戏的那种狂喜的初次体验,还是欢梦重温。
既然如此,现代主义通常避免对异化劳动进行直接表现,这一点就绝不是偶然的了,除了一些激进摄影师的作品,比如路易斯·海因(Lewis Hine),他将废除童工作为其摄影计划的基本动机。相比之下,每当20世纪的绘画或摄影赞美劳动力或强壮有力的工人时,人们很有可能——也可以——肯定,他与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站在一起,无论是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还是社团法人(corporate)国家。将屈服于异化的体力劳动的身体进行英雄化处理,是为了灌输对令人难于忍受的奴役状况的集体尊敬;在对那种劳动的虚假称颂中,它也被用来使那种本来应该从其潜在的改变的角度(即使不是从其最终被消灭的角度)加以批判性分析的东西中立化。相反,将艺术实践当作游戏般的反抗,从而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不仅认识不到作为集体经验的主导形式的异化劳动的普遍性,也过早地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将艺术实践降低到完全从现实原则中毫无意义地排除出去的地步。
意识形态:反映和调和
意识形态的概念,在乔治·卢卡奇(Gyorgy Lukács,1885-1971)的美学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创立了20世纪最具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理论。虽然很少涉及艺术的视觉生产,卢卡奇的理论还是在其发展的第二阶段,亦即四五十年代里,大大地影响了社会艺术史的形成,特别是卢卡奇的同道,匈牙利人阿诺德·豪塞尔(Arnold Hauser,1892-1978 )和奥地利人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菲舍尔(Ernst Fischer,1889-1972)。
卢卡奇理论的关键概念即反映(reflection),它在经济和政治基础的驱动力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当机械的联系。意识形态被定义为意识的颠倒形式,或者——更坏的——只不过是一种虚假意识。此外,“反映”的概念主张,文化表征的现象,最终不过是一个特定历史时刻的阶级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的次要现象,尽管人们后来对反映的理解总是背离这些机械论的假说。卢卡奇的分析事实上已主张文化生产类似于以辩证历史的方式运作,他将某些文化表征(例如,资产阶级小说及现实主义方案)看成是资产阶级进步力量的文化精粹。然而,在进一步发展一种无产阶级的美学时,卢卡奇变成了反动思想的拥趸,辩称道,对资产阶级文化遗产的维护肯定将是新兴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内部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卢卡奇的论述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务,最终既要维护进步资产阶级阶段的实际已被背叛了的革命潜力,同时又要为一种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奠定基础,这种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已经真正取代了文化生产的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
从60年代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化以来,美学家和艺术史家不仅区分了意识形态的全部理论,而且还详尽阐述了文化生产一般是如何联系到意识形态机器的。艺术实践到底是在意识形态表征之内还是之外运作,这一问题从70年代以来尤其吸引了社会艺术史家,因为他们所赞同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一,所以他们给出了许多迥然不同的解答。比方说,那些追随美国艺术史家迈耶尔·夏皮罗(Meyer Schapiro,1904-1996)早期马克思主义阶级的批评模式的社会艺术史家,继续认为文化表征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利益的镜像反映,并在此观念下进行批评(例如,夏皮罗认为,印象主义便是有闲、持股资产阶级的文化表征)。根据夏皮罗所论,这些文化表征产品,并不仅仅清晰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普遍心态;他们也赋予其文化权力,来宣扬和维护其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合法性。
其他研究者则将迈耶尔·夏皮罗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的社会史当作出发点,同时也接受了他在晚期作品中发展出来的复杂观念。他考虑到了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远为复杂的问题,在他的论述中,他认识到,美学形态是相对自律的,并非完全依赖或适合意识形态利益(例如,在夏皮罗随后转向一种早期抽象主义符号学时,这一发展非常明显)。一种更复杂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后果之一,便是尝试将艺术表现当成是特定历史时刻的辩证力量。换句话说,在特定情形下,一种特殊实践也许能很好地阐明一种进步意识的高涨,这种进步意识不仅是一个独立艺术家的,同样也来自于一个赞助者阶层的内部,并且也体现了依照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轨迹和不断膨胀的社会、经济正义的自我界定[例如,托马斯·克劳(Thomas Crow,1948年生)的经典论文《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odernism and Mass Culture”),它写到了新印象主义点彩派的风格特色,从与激进无政府主义政治的关联到一种优雅从容的风格遽变中,所体现出来的辩证观念]。
70年代的社会艺术史家,如克劳和T.J.克拉克(T.J.Clark,1945年生),将文化表征的生产看作既依赖于阶级意识形态,又是反意识形态模式的生成。因而,对于19世纪现代主义绘画,及其在更广大的意识形态生产机制中的命运变迁的最全面论述,我们仍然能够在克拉克——这位20世纪晚期最重要的社会艺术史家关于意识形态问题复杂而日益细腻化的阐述中找到。例如,在克拉克对杜米埃尔和库尔贝的论述中,意识形态与绘画之间的关系仍然被构想为一种辩证关系,这种关系是卢卡奇在对18、19世纪的文学的解释中所暗示的:它是资产阶级进步力量在完成法国大革命与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文化的承诺时,走向自己的成年的体现。
相比之下,克拉克的晚期作品《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ellowers,1984),并没有讨论以下极端的难题:即将马奈和修拉的作品置于与一个社会的特定部分的进步力量之间清晰而又富有活力的关系之中。毋宁说,克拉克所面对的,是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和艺术生产之间新发现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以及怎样把这种复杂的任务融入到那个时候他业已发展起来的社会艺术史的方法论之中。毫无疑问,这种理论危机多半源于克拉克对马克思主义拉康学派的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作品的发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仍然保留了最富有成效的部分,特别是在它以相对自主的立场在意识形态整体中处理审美和艺术的历史现象的那种能力。这并不仅仅因为,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理论化为一个语言表征的整体,主体在其中以拉康所称的象征秩序的政治形式来加以构建。也许更重要的是,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所有表征领域的亚区域)的整体性,与将艺术表征(以及科学知识)从意识形态表征的整体性中明确予以豁免之间所作的区分。
流行文化对抗大众文化
社会艺术史家之间最重要的论战问题之一,便是所谓的高级艺术(high art)或前卫艺术实践是如何与新兴的现代性大众文化形态联系起来的。尽管,可想而知,这些形态持续变化着(因为表征系统的两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断重置的),但仍保留着难解的争论,其结果通常表明了大众文化批评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形式。阿多诺的著作对大众文化形态作了最强烈的拒绝,他对爵士乐臭名昭著的咒骂现在已被普遍认为是不光彩的,是欧洲中心论亚历山大主义的一种形式——最糟糕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者对他极其鄙视的音乐现象实际上根本一无所知所造成的。
对于大众文化现象进行讨论的相反言路,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著作中,他对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作了至关重要的区分,形成一个富有成效的有益理论,促成了其后文化史家的尝试,如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1932年生),他们声称一种在分析大众文化现象时无限分层的方法。霍尔主张,美学家和艺术史家在从革命与解放到倒退与反动之间所产生的风格现象的逐渐演变中所察觉到的辩证运动,同样也可以在大众文化生产中察觉到:在这里,在工业化的文化适应过程中,从最初的反对与背离,到最终的确认,一种永恒的摆动总是发生着。霍尔也似是而非、貌似可信地指出,要克服欧洲中心的文化霸权论(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先锋派),第一步就应知道,不同的观众,是以不同的传统结构、语言习俗和相互作用的行为模式来交流的。因此,根据新的文化研究路径,观众身份和体验的特殊性,应该凌驾于所有主张之上——这些主张作为审美评价的普遍有效的准则,既神圣又独裁——也就是说,这种等级制的法典化,其最终和潜在的目标都是为了保留对白种男性资产阶级文化至高无上的优势的确证。
升华与反升华
威廉斯和霍尔所精心创立的文化研究模式,以及随后知名的学者,如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为今天所从事的文化研究领域的绝大多数著作打下了基础。即使据我们所知,阿多诺并没有与任何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打过笔仗,但他的反驳无疑将是对他们计划的谴责,非难他们的计划是一种将反升华(desublimation)延伸进美学体验的真正中心——思想观念和反思评价——的计划。对于阿多诺来说,“反升华”使得对主体性的破坏更进一步内在化了;其基本方案是要摧毁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的进程,摧毁对政治自决和抵制的渴望,最终完全受晚期资本主义需求控制而消灭体验本身。
另一位相当与众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以几乎迥异的方法来设想“去升华”概念的,他主张,美学体验的结构由两方面来构成,一个是那种对暗中破坏性压抑机制的渴望,另一个则是对生成一个从需要和工具性需求中解放出来的生活的预期时刻的渴望。马尔库塞“爱欲解放论”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美学,正好完全处在了阿多诺禁欲主义的否定辩证法美学的另一极,阿多诺并非没有公开驳斥马尔库塞,他被认为对马尔库塞思想中的美国式享乐主义消费文化具有绝对震憾性的威慑力量。
不管马尔库塞对“去升华”的重新定义会产生什么样的衍生物,无疑,在二战前后的先锋派实践中,显然可以找到大量迹象。在所有的现代性中,艺术策略都拒斥且否定那种精湛技艺、卓越的技巧,以及与历史典范公认标准相一致的既成规则。它们否定任何时代审美的特权地位,并以所有去技术化的手段来贬低它,通过求助于一种卑琐或低俗文化的图解,或通过对创作过程和材料的凸显,将那种被压抑、被否定的肉体体验,重新置于艺术体验的空间之中。
新前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社会艺术史的书写之中的主要争论之一,起源于一种普遍存在的非同步性状况。一方面,美国批评家尤其渴望建立20世纪第一个支配性的前卫文化;然而,在这一方案的实施过程中,他们未能认识到,重建前卫文化模式的那种困难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影响到在此种情况下生产出的作品状况,也同样会甚至更深刻地影响到有关它的批评性、历史性的评论写作。
在阿多诺晚期的现代主义著作《美学理论》(Aesthetic Theory,1970)中,自律性这一概念保留为中心角色。不同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晚期现代主义美学那重新鼓吹概念的美学观点,阿多诺的美学是以一种双重否定原则来运作的 。一方面,阿多诺的晚期现代主义否定了进入自律性美学重建通道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已随着法西斯主义和大屠杀所造成的创伤以及资产阶级主体的最终破坏而毁灭。另一方面,阿多诺的美学同样又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革命态度促成艺术实践政治化的可能性。依照阿多诺的理论,政治化的艺术只能充当一种借口,阻止真正的政治变化,因为在战后文化重建时期,要建立一种革命的政治环境,事实上并不能达到。
相比较而言,美国新现代主义和彼得·比格尔所说的新前卫(neo-avant-garde)的实践——很明显是由格林伯格与他的信徒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1939年生)所鼓吹倡导的——只有以系统的东拼西凑(geschichtsklitterung)为代价才能维系其结论,是试图站在取胜者的利益的视角来书写历史,却完全否认前面讨论过的、在高级艺术与前卫文化的概念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转型(例如,达达、俄国和苏联前卫艺术的遗产)。更糟糕的是,这些批评家并不能认识到,大屠杀之后的文化生产,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连接起现代主义绘画和雕塑的余脉。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模式(最显著的,便是他的断言,奥斯威辛之后写抒情诗是不可能的),他的美学理论——公然反对格林伯格的新现代主义——主张重新思考一般文化的不确定状态的不可避免的必要性。
看来,在阶级、政治利益和表征的文化形式之间已经稳固地建立起了调停关系,因而相应也可证实的历史情境中,艺术社会史的力量与成就最为明显。围绕着那种现代性的革命的和基本的情状,他们那种重新叙述的独特能力,造就了社会艺术史家对现代主义第一个百年最引人注目的诠释,从托马斯·克洛著作中的大卫,到T.J.克拉克作品里写到的立体主义的兴起。
然而,当它们面对先锋派实践的历史涌现时,如抽象、拼贴、达达,或杜尚的作品(杜尚最隐秘的目的是积极地毁坏传统的主-客关系,显示出对传统体验模式的破坏),社会艺术史无论是在叙述的层面上,还是在图画再现的层面上,想要坚持融贯的叙事性解释的努力,在最好的情况下,要么出现不协调,要么与手头的结构和形态学相互扞挌;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就像虚假的复原。一旦分化与分裂的极端形式成为首要的正式关切,其中后资产阶级(postbourgeois)主体性可以找到其相关的造型残余,那么重新将总体性视野强加于历史现象的渴望,在其意义与经验结构的实施过程中,有时就会显得保守倒退,在其他时候,则会显得妄想偏执。毕竟,这些艺术实践的彻底性,不仅包含着它们对那种总体性视野的拒绝,也体现出其句法和结构的表达,在这种表达中,叙述和造型都是很难获得的。假如意义仍然可以完全获得,那么人们一定会要求解释,这种解释必定会超越规定性的因果关系框架结构之外。
注:本雅明·布赫洛(Benjam in Buchloh,1941-),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出生于德国,《十月》杂志编辑,哈佛大学梅隆现代艺术教授。面对自律的现代艺术无力对抗霸道的文化工业的困境,布赫洛自1970年代开始从两方面展开了新前卫叙事。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从抵制商品化、抵制与艺术体制共谋的角度来解释新前卫艺术;另一方面,在解释新前卫的同时,批判其他当代艺术丢掉了艺术的否定性特质,如美国的极少主义艺术。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