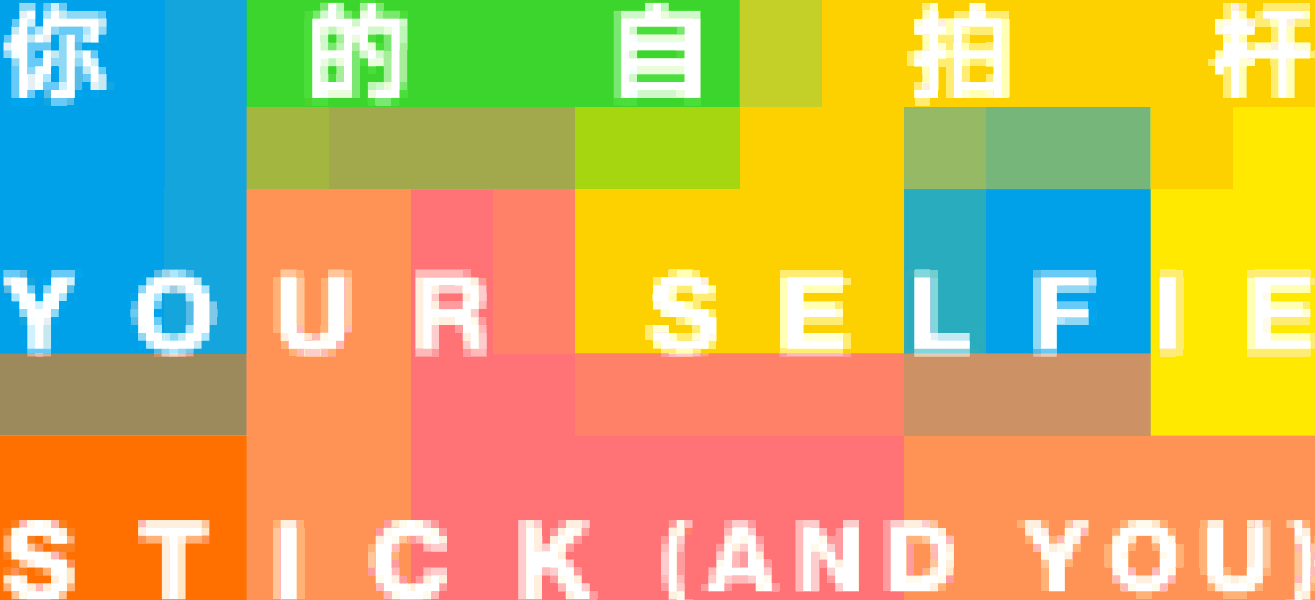
年度主题:你的自拍杆
Curatorial Theme: Your Selfie Stick (and You)
时间:2017年12月2日至2018年1月2日
地点:广东 · 连州
Time: Dec.2nd, 2017 - Jan.2nd, 2018
Venue: Lianzhou, Guangdong
总监
段煜婷 (中国)
年度学术主持
王南溟(中国)
主题展策展人
桑德拉·冒纳克(西班牙)
乔安娜·蕾韩(美国)
张冰(中国)
策展团队
温迪·瓦曲丝(美国)
罗伯特·普雷基(美国)
露西尔·丽博芝(法国/日本)
仲西祐介(日本)
彼得·普夫伦德(瑞士)
郭小晖(中国/英国)
海杰(中国)
周琰(中国/加拿大)
Director
Duan Yuting(China)
President of Academic Committee
Wang Nanming(China)
Theme Exhibition Curators
Sandra Maunac (Spain)
Joanna Lehan (USA)
Zhang Bing(China)
Curatorial Team
Wendy Watriss (USA)
Robert Pledge (USA)
Lucille Reyboz (France/Japan)
Yusuke Nakanishi (Japan)
Peter Prfunder (Switzerland)
Guo Xiaohui(China/UK)
Hai Jie (China)
Zhou Yan (China/Canada)
你的自拍杆
文︱段煜婷(连州摄影博物馆联合馆长、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总监)
“你的自拍杆”?似曾相识的话语,是的,它正是2008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主题“我的照相机”的延续,在当年过度追新逐异的声浪下,我们提出让摄影恢复本真的观看;时间过去了仅仅九年,时代却已经发生了巨变,这个变化就是我们放下了照相机,拿起了“自拍杆”。
2000年9月,夏普公司推出这个星球上的第一款拍照手机“J-SH04”,虽然只有区区的11万像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效应,但谁也不曾想到数年后手机会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摄影行为方式。不仅如此,随着以iPhone、ipad为代表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具有轻便、多功能、高效、移动互联种种特征的新一代工具的诞生,使得手机在能拍照的同时兼具互联网移动终端的功能,极大地加速了图片的生产与处理,衍生出社交媒体、图像分享平台等各种APP软件,并被人们广泛应用,人类的通讯、传播方式又得到了一次巨大的发展。
“自拍杆”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全新的摄影配件,表面上看,它的产生是为方便手机摄影而对我们肢体的一种延长,是更大程度地解放人们拍照的束缚。随着新的技术方式的产生,摄影师们也开始不约而同地借势,装备、筛选工具,尝试进一步延展摄影这一媒介的边界。而新的角度与观看方式由此诞生,但却并不意味着一种颠覆,或是一种更加个人化的视角,它使得“我”可以随时介入这个“世界”。也许,再没有一种方法能被否定或被扭转,每一种方法都被不断更新,在艺术家的手中相互杂交、汇合:是更远又更近的距离,是专业而业余的手段,是个体探索着集体的劳作,是程序模仿着人力而人力模仿着程序。被以此方式捕获的我们与这世界的图像,也得以从方法的牢狱中抽离,不再恰如其分,而顺应化作更纷繁的象征与符号。
这是图像的微小革命,它发生在艺术与科技交织成的这片神经网络的每一个节点——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社交媒体、图像分享平台、网络文化与语言,以及我们所说的“自拍杆”。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