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t Stage Singapore 2014
文︱何思衍
“艺术登陆新加坡”(Art Stage Singapore) 的创始人及总监洛伦佐·鲁道夫(Lorenzo Rudolf)是一个艺博会巨头——他曾于1991年至2000年任巴塞尔艺术展的总监,并将巴塞尔拓展至迈尔密(后者于2002年开始运营)。2007年鲁道夫创办了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SHContemporary),但出于各种原因,在2009他便很快退出了该艺博会。而他的最新项目,“艺术登陆新加坡”,已经成为了东南亚当代艺术博览会之中的佼佼者。燃点和鲁道夫谈起他在上海的日子,以及他对上海艺术界的观察。同时他还聊到在新加坡创办艺博会的挑战和潜力,以及艺博会中策展项目的缘由。
何思衍:你一手促成了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的开办。或许我们可以从对它的回顾开始谈起?
洛伦佐·鲁道夫:当我们2007年在上海开办艺博会的时候,上海有着一种开始逐渐兴起的感觉。我还记得我们在衡量应该在北京还是上海办展时,最终选定了上海。因为我们相信,从长远的角度上看,尤其是针对国际市场方向而言,上海应是不二之选。尽管当时所有的风向都指向北京——那是画廊和艺术家的聚集之处等等,但我们仍觉得当时的上海正在崭露头角。之后,正如大家所知,我们离开了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当时正值金融危机,泡沫破裂,百废待兴。这也说明艺术市场离转移到香港也仅有一步之遥。而从那以后的好几年,上海的艺术市场环境就一片沉寂。
而在近两年来,我们似乎可以察觉上海发生了不少变化。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也能感受到上海如同一张白纸,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整座城市也有着向前迈进的愿景,在政府支持下出现了不少转机。先是私人美术馆的蓬勃发展,到现在一个季度就有着五六个艺博会的情形!但这是不现实的,我想最终只有那么一两个艺博会可以有着稳固的位置。
我曾到西岸博览会和其总监周铁海聊天。西岸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做得很好,空间搭得也不错,没有刻意朝宏大的方向发展,这也理所当然。中国画廊和国际画廊的数量比例上也有着良好的平衡。尽管我对其设计没有太多好感,但周铁海在这方面可能有自己的考虑。无论如何,我认为这对一个艺博会而言是一个不错的开始。看到这样的活动,你就可以相信上海对自身充满信心,这不仅是一种来自本土的信心,更是国际上的信心。
我也参加了龙美术馆和余德耀美术馆的开幕。要知道这两者可不是什么小空间,他们丝毫没有掩饰自己收藏的意思。而这也将把他们带入公共美术馆的级别,在亚洲这正是普遍现象。
亚洲没有多少顶尖的公共美术馆。新加坡、日本、韩国可能都有那么一两个,在亚洲最重要的美术馆往往还是私人的。而中国有着新一代的藏家,他们手中也有不错国内国际收藏,还有资金建立美术馆,并借此取代了公共美术馆的作用和地位。坐拥诸多私人美术馆和艺博会,十年之后的上海必将成为一座蓬勃的艺术城市。
但还有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税务,如果税收方面能得以减压,上海必将势不可挡。
何:在我看来,这里既有艺博会,又有美术馆。无论艺博会的发展走向如何,藏家们也会不断建立美术馆。
鲁道夫:最近我在首尔听当地行业聊起韩国市场呈下降趋势,而艺博会的销售成绩也在下滑,在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仔细分析一下亚洲的几个不同市场——韩国疲软,印度平稳,而中国却在不断运转,这三者之间有怎样的区别呢?
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社会和市场的运转模式。在韩国,整个艺术市场依仗着六七个超级大买家。如果他们中的其中一个暂缓买入,那市场必将面临缺口。在印度,社会分化尤其之大,上层阶级中有着一个极富群体,接着是一个较小的中产阶级,和大部分的贫困阶层。而在中国,尽管没有像余德耀、乔志兵和王薇这样的收藏巨鳄,但却有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开始收藏艺术品。
何:是这样的吗?我认识其中一些,但。。。
鲁:这才刚刚开始,社会阶层金字塔的顶层仍是中产阶级。昨天我和周铁海好好聊了一番,他发现在买买买的藏家多为40-50岁的中年阶层,他们为跨国企业工作,或是有着自己的资产。他们是空中飞人,有的还有海外留学经历——这正是这个不断发展的藏家群体的面貌,而他们也是社会中的上流中产。
就算是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具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不仅是一个顶尖阶层,才会促生一个强盛的买家群体。而在中国,中产阶级正不断增长,这也会促进中国市场的不断发展。
何:我想再聊聊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可能当时你看到了中国的商机,但只能说时机并不成熟。
鲁:两者兼有。我来到中国的原因相当明确:一是中国的经济增势迅猛,人人都在谈论中国,而那正是打开沟通途径的时候。我们当时的想法,是采用两步渐进的策略。我们首先想在上海办一场艺博会,然后在香港办另一个,两者时间错开,但同处一个品牌。一年做当代,下一年则做现代。这样一来我们既能把握住香港的市场,又能培养上海的市场。我们的意大利合伙人,本应去锁定香港市场,最终没有成功,而那也促使了我们的退出。但你可以预期到成功的可能性,我仍认为那是个正确的思考方式。
而现在形势已变。我觉得上海仍有不少的提升空间。香港仅有的优势在于税收政策和办事模式。但这两者在未来的中国大陆都会发生改变。尤其是从长远眼光上看,上海前途无量,中国必将在经济上起到更重要的主导地位,而其品味也将变得更为国际化,中产阶级群体也势必增长。这都是促成一个强盛市场的重要因素。

Art Stage Singapore 2014, Lorenzo Rudolf and Dr Oei Hong Djien
何:在我看来,外国人在中国总是很难办事。这其中牵扯到关系、语言、和人脉……想必你也是感同身受。
鲁:可以这样说,无论你到哪里,都要去适应当地的办事方法。你不能走到那里然后说,噢我知道这件事唯一的解决办法。在中国最困难的部分,除却你所聊到的那些,是你需要一个中国合伙人,一个你可以完全信赖的合伙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当你在诸如艺博会这样的环境中,尤其是在我们当时进军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合伙人完全了解我们的想法和计划。而那正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但在那之后我们开始左右逢源,认识到了给我们指出明路的合伙人。有些时候是我们的合伙人没能和本土合作对象搞好关系。合伙人之间必须建立起一个公开和互相尊重的关系。不然必然带来摩擦,而万一有什么差错,得利的永远是中国合伙人。但我认为这正是值得去建立的东西,在中国想要经商,首先得会交朋友。如果你去纽约,你就需要适应纽约的规则。
何:在中国办事是否比别处要更难呢?
鲁:的确如此。为什么在新加坡或是香港一切都要简单不少?因为它们已经适应了西方商业体系,所以一些事情比较好谈,不需要去遵守中国的办事方法,但这并不意味这一定是更好的模式。
回到你刚才说中国问题。只要入了门,做起事来也没那么麻烦。可能在某些行业,当你好不容易建立起了一套体系,中国人立马全权夺走,落下你一事无成。所以你必须要:一先发制人、二谨慎选择、三做具体的事,让对方无处可师。
而至于我们为什么要离开?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我们当时面临着不少麻烦,而主要的原因还得怪我们自己。在当下看来,中国和外资的合作正变得愈发开放和明朗。而说到底,如果想要办成一件事,就需要双方都倾尽全力。那才是制胜的唯一法宝。

Art Stage Singapore, Southeast Asia Platform, Anurendra Jegadeva, Wei-Ling Gallery
何:让我们聊聊新加坡。新加坡是否给予“艺术登陆新加坡”以支持呢?当地政府在支持艺术体系方面有什么是做的比较好的?
鲁:当地政府有着不错的愿景。新加坡政府想将城市打造成亚洲乃至全球当代艺术和文化的中心之一,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东南亚地区。他们也深知当代艺术有着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资金投入相当给力的原因。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不同的人才。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家,他们正在建造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这将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美术馆,有着最大的东南亚艺术收藏。
我们也被看做是着整个过程的催化剂之一。我们推开机会之门,引入人才。而在艺博会开办后,经历了漫长的讨论,我们决定建立起一个艺术区——吉尔曼军营艺术区(Gillman Barracks)。但借此你也能观察当地产业的运作方式:他们建成了艺术区,却没能良好的运营——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区没能正常运作的原因。
至今为止新加坡仍旧认为他们可以用从上至下的方式建立起一个文化坐标。不幸的是这仅仅是一厢情愿。如果艺术和文化得以昌盛发展,那首先就需要自由的环境。政府可以建设起环境,但却无力亲手培养整个艺术氛围。
新加坡在过去的五十年迅速发展成为了全球一线城市。正如建造一栋乐高积木塔一样,一砖一瓦,各负所需。这样的成绩固然使人惊叹,但仅有硬件仍不够,软件体系也必须跟上。而这就是我们所处的阶段——个转变之中的阶段——它同样也也需要人才的更新换代。
从那以后已经建立起了两座美术馆,现在第三座美术馆即将开放。我们总是可以讨论为什么会有偏差,同时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反思、学习。但总体来说,大方向是正确的。
新加坡处于这个艺术发展蓬勃地域的中心。这不仅仅是跟艺博会有关,同样也和这个地区有着紧密联系,从印尼到菲律宾,整个东南亚艺术界有着颇为成熟的艺术环境。印尼有着不少艺术家,这也和整个国家的历史有关。现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在涌现出不少新艺术。但这些地方所缺乏的正是基础设施。缺乏正规的美术馆,也没有任何扶持艺术创作的基底,许多画廊缺乏竞争力。而以上这些问题在新加坡都不是问题。某种角度上而言,新加坡正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唯一足以成为中心的地方。

Art Stage Singapore 2014, India Platform curator Bose Krishnamachari and artist Sakshi Gupta
何:但新加坡也有言论自由限制和审查制度的问题。还有你所说的关于资金支持的问题等。
鲁:至于审核制度,在我看来过去的五年我们只经历了两起自上而下的审核事件,最后两者都算作自我审核。这只能说明有些事情其实不做更好。
尤其是当我们从西方这个有着悠久革命和个人主义传统的文化来到这里,我们无法在此进行对比,更不能在中国。
何:我想在中国,审核制度并不是要被逐渐废弃的东西。他们也在把新加坡当成学习对象,看看这个有审查制度的发达国家是如何运作的。
鲁:当然,新加坡的统治阶级仍是中国人。但随着全球通讯和互联网的发展,有些事情是无法被重新更改的,问题在于社会要如何去看待这些问题。若是建立起这样的审核体系,万事俱细、监督国民,那你总会担心出问题的那一天。
就像是家长和孩子的关系一样。他们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他们想要教育并培养孩子,但他们也需要意识到孩子们也会想要自由。家长此时所能做的,就是去给孩子们独立的空间。
何:但是,你知道中国家长是怎么样的。
鲁:[笑], 你懂的。

Art Stage Singapore 2014, Entang Wiharso, “Crush Me #2”, ARNDT
何:上次印尼馆是如何策划的,是否是收到了些负面评价?
鲁:其实一切很简单。印尼长久以来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有着极高的销售成绩,一些作品甚至可以卖到百万美元以上。在香港的拍卖市场,印尼藏家也在买入印尼的作品,而这个市场也运转地非常成熟。印尼市场的繁荣得益于艺术家在印尼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和苏卡诺总理和印尼革命有关。他在革命中的同僚有不少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从那以后,在上层阶级里,艺术家便有了较高的地位,而这也是为什么印尼市场会如此繁荣。买家数量较大,他们往往自发组织。有些年轻的藏家也是通过老藏家介绍到圈子内的。
尽管印尼有着一个极大的市场,但这个市场仍是本土的。收藏家和艺术家直接进行交易,他们甚至无需画廊做中介。
而在这个全球化的环境中:艺博会和画廊各有其作用。这些印尼的艺术家开始意识到,尽管他们在国内是天王巨星,有着别墅跑车,现在他们有了打开国际市场的机会。然而问题是,他们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的扶持,他们还没有画廊去支持他们,去投资他们。于是当时的我们面临着一个奇怪的情形。整个艺术圈都在向我们寻求帮助。
于是我们便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遭遇了这个奇特的现象,这在欧美很少出现:我们是给画廊卖展位空间来支持画廊呢?还是去扶持这些艺术家呢?我们当时需要做个决定,若是去帮助艺术家,那就将会有很大一批的印尼画廊与我们为敌。我们若是不那样做,那印尼市场也只会原地踏步。最终我们决定和画廊合作支持艺术家。有些画廊加入了进来,而另外一些则没有。这些有关艺博会作用和新加坡国情的讨论,最终都获得了成功。我们为艺术家带来了不少机会,许多印尼艺术家开始在西方美术馆展出,还有不少进入了西方收藏,例如古根海姆和泰特。那些参与进来的画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另外的画廊至今仍十分懊恼。
但如果印度尼西亚想要打开国际市场,就必然需要画廊的介入。当然,考虑到印尼长久以来的模式,肯定会需要许多时间来改变。我们需要去寻找艺术家,并将他们带入市场。我们没法像西方办艺博会那样,首先这里没有那么多画廊,其次,画廊也没有在投资。我们需要寻求新的商业模式,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这条路的原因。
何:那印尼馆今年也会有吗?
鲁:那只是一次性的活动。但我们觉得主旨没错,所以这回会有一场策展后的销售展览。这其中有着好几处优势。首先:你可以对艺术家进行推广和定位,这是在画廊展位中仅用一两件作品所做不到的事。我们将借助东南亚主题的大展馆,不分国家,它代表的就是东南亚。
我们所做的不仅仅是将亚洲画廊聚集到一起,而是促使亚洲艺术互相了解对方,同样也是将亚洲介绍给西方。这也是为什么去年我们建立了除开东南亚馆以外的六七个国家馆,包括: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而在每个国家,我们都找来其顶尖的策展人,让他们自由发挥,唯一的要求是每个艺术家、每件作品背后必须要有代理画廊,这意味着作品是参与交易,有画廊在另一头扶持。那个模式非常成功,有意思的是,每个策展人都希望策划出一个极好的国家馆,他们遂找来藏家帮助,的确相当奏效。尽管那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所看重的是展示并解释展览与作品。

Art Stage Singapore 2014, “Nothing to Wait” For by Chun Kai Feng, FOST Gallery at SEA Platform
何:所以策展人必须要从参与画廊中挑选作品?
鲁:并非如此,他们完全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选择不会受到参展因素的限制。而画廊可以通过一件作品或是一个项目来参与到平台中,它们同时也可以向策展人推荐作品。
何:那谁负责掏钱呢?
鲁:画廊们。画廊并不是在买展位,而是通过支付参与费的形式。参与费可以填补艺博会60%的支出,另外的40%由赞助商提供。
何:印尼ArtJog是不是你们的竞争对手呢?
鲁:我们之间不存在竞争。ArtJog有着自己的特色。其所在地日惹市在印尼艺术圈有着重要地位。如果你去到日惹市,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艺术家们好比天王巨星。而这正是他们的身份,在那儿没有画廊的身影,所有的资源都在艺术家手上,他们甚至有着自己的展览中心来为年轻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整个活动都是由艺术家带头的。而ArtJog也只能在日惹市这样一个特殊的氛围之中运转,若是照搬其模式到巴厘或是雅加达,那肯定会变味。但与此同时日惹市却又像是个不毛之地,它并不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位置偏远却独具韵味。
何:在我看来,每年的艺博会你都在试图尝试展览的新途径。
鲁:可以说我并不是在尝试新途径,而是在应对新现实。同时我也认为艺博会需要更富创意,我们因此不断地需要思考新方法。我们往往会想到所谓香港与新加坡之争,艺术巴塞尔香港是什么?它是业界最大的艺博会,与任何大品牌一样有着全球化的运作模式。就好比Gucci在东京开的店卖的仍是Gucci的包。
而我们是一个小而年轻的艺博会,同时也清楚得敢为人先。要是有一年我们的某个尝试成功了,那明年很可能在香港看到一样的模式。我们需要不断创新,同时也乐在其中。
2015年会有一个有主题性的策展项目,我们不想走国家馆的形式,其次,我们也不想局限在亚洲当代艺术的框架里。亚洲的现代艺术是和西方体系紧紧相关的。放眼印度、中国、印尼和日本,你会看到不少相似的作品,他们有着类似的根源,但却各成体系。我们想要一步一步地打开亚洲现代艺术的市场。
与此同时,恰逢新加坡建国50周年,我们将会有一场大团聚。许多艺术家和画廊都会参与进来,共襄盛举。

Art Stage Singapore 2014, artist Darbotz at Mizuma Gallery

Art Stage Singapore 2014, entrance arch, “The Continuous Gate” by Joko Dwi Avianto

Art Stage Singapore 2014, China Platform Curator Huang D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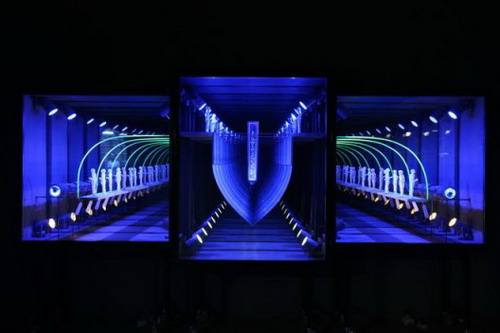
Art Stage Singapore 2014, Southeast Asia Platform, Mark Justiniani at The Drawing Room
何:如今的潮流是小型艺博会,而我们是否对大型艺博会不那么待见了呢?
鲁:我想是的。巴塞尔艺术展只可能是一场大的艺博会,那是它的根本所在。如果有着巴塞尔这样的艺博会,其它的艺博会注定无法与其竞争。但不可能在每个国际大都市中都有大型艺博会。
同时大家都在飞来飞去,如果我去到上海,我可不想看到柏林的画廊在做些什么。但若是一名中国观众,可能就会想看看外国画廊会带来什么。我想这其中的平衡相当关键,而这也和地域紧紧相连。
我想在亚洲有着一股自信。他们所期待的是亚洲与世界旗鼓相当,并不只是国际艺博会圈中的一份子而已。到头来,亚洲需要一个自己的巴塞尔,和巴塞尔一样专业、重要,但有着自己的亚洲背景。在香港巴塞尔,表面上看有着一半西方画廊和一般亚洲画廊,但若是西方画廊有着亚洲画廊三倍的展位大小,那这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不一样的。
但与此同时我也要为巴塞尔说句好话。在他们背后有着成百上千的画廊不断催促他们打开亚洲市场。他们难道可以轻易拒绝吗?没那么简单。
我想亚洲想要得到重视,这在将来更会是如此。日后定会有亚洲藏家想如同西方藏家一样,把他们收藏的亚洲艺术家推向国际市场尖端的情形。到了那一天,平衡就会真正的出现。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