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
西方当代艺术中的佛教影响之一:美国当代艺术家比尔·维奥拉
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 1951-),是美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之一,尤其在新媒体领域。他学美术出身,但从美术学校毕业后又学过一段时间音乐,因此他和录音、电视、电脑等媒体接触较早,也和新媒体的主将白南准等人颇有往来。他虽是个美国人,却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东方的宗教,借此让自己的艺术可以进入更深更大的境界。他的作品主题常常是涉及人的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最真实的生命内容。因此他创作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意义和宽广的覆盖面,使得他在美国的当代艺术界声誉卓著。他是1995年威尼斯双年展的美国代表艺术家,展出的“深藏的秘密”,是行为与新媒体相结合的系列当代作品,挖掘人们深藏的情感表现。1997年美国温迪美术馆为他举办了个人大型回顾展,并在国际上巡回展览。2000年,他被选入“美国艺术科学院”。2009年他获得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国际大奖,这个奖项颁发给“其创作的作品为发展文化,科学和人生价值方面有卓越贡献的人。”西班牙还为其出版了个人传记。
(以下三图为维奥拉多媒体作品,借图像表达人的生存苦痛,或者水与火等基本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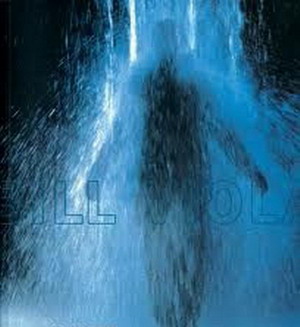

维奥拉访谈
——采访者为芝加哥艺术学院美术馆策展人玛丽女士,访谈节译自《当代艺术中的佛教思想》
(Buddha Mind in Contemporary Art, Edited by Jacquelynn Baas and Mary Jane Jacob,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2004)
问:请说说你是如何对佛教感兴趣的,又是如何使其进入你艺术创作中的?
我在1960年代末上大学。那是个社会变革的年代,这个变革的一部分便是重新注重精神的训练,古代的东方宗教如印度教和佛教在美国年青人的文化中第一次自由地传播,我在校园里参加了几次冥想训练并开始阅读有关的书籍,像《西藏生死书》。不过我第一次与佛教相遇是在1980年,当时我得到了一个日本美国友好协会的资助,携妻到日本住了一段日子。日本发达的技术和发达的传统文化,在我看来是最理想的一个地方了。
我首先想要学习的是“禅艺术”,那是我在书上看来的日本十五世纪的大画家雪舟的传统水墨画,但找到一个这样的老师并不易。当然,这就像一个日本艺术家来到西方要学习伦勃朗的画法,而这些艺术家早就死了。最后,一个日本朋友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你这么做根本不对,你为何不去一座寺庙,学习禅?然后,你做的任何东西就是禅艺术了。”这一下仿佛让我在一向熟悉的路上踢到石头了。我倏然意识到,我所珍视的艺术该是为另一些事服务的—一些更大更深入的事。直到那个时候,我对成功艺术的定义是在画廊,美术馆,或者一些另类空间的展览范围内作为标准来衡量的。在日本,我这个看法开始被改变,它下降到艺术与生活为伍,它将成为来自生存质量的一种实践,一种让思想往深处去,一种让制作者精神成长的事物,而不再是看一件作品本身有什么样的优点,或它在展示上有什么成功。艺术应当做更重要的事,然后才有其他的东西。这个启迪改变了我的人生。
另一个体验坚定了我的这个想法。那是在东京的株式会社艺术馆,看一个来自京都寺庙的艺术物品展。当我们站在一排真人大小的菩萨像前,正在读旁边的文字说明什么的,却有一个日本小老太太,越过我们直接走到菩萨像的跟前,向每一尊菩萨像默默地鞠躬祈祷,然后把一条丝巾献在塑像伸出的手上。我被惊呆了:这可是个美术馆哦!而美术馆的警卫对此不加干涉,也让我惊讶不已。在这个时刻,艺术落实于生活,艺术对于生活产生作用正在这些展品上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我油然感到,一直以来自己就象一个人一直在夸奖电脑的外形如何好,却从来没有把电脑打开过一样。
还有一个契机是,1980年跟我参加同一个项目的美国艺术家James Phillips给我看了一本书,是Anada K.Coomaraswamy写的《艺术中自然的形态变化》(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in Art), 这本书完全改变了我对于艺术的看法。 Coomaraswamy是锡兰(今斯里兰卡)的一位优秀的宗教学者和哲学家,也是个艺术史家,他对于中西方宗教很有研究,也非常懂得印度的传统和东方的艺术。他批评西方对于艺术分析和展览的体制化,他非常知道,那些单个的艺术品其实不是独立的审美物,而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和精神传承中的一个部件。
他在移居美国后,开始研究西方文化的精神根源。Coomaraswamy在他的书中这么发问:‘为什么要展览艺术作品?是被要求去阅读了解艺术家和美术馆的职业性吗?他还说,“美术馆不过是我们存放一些我们会忘记该怎么用的东西的地方。”他还说,“除了‘视觉艺术’这个称谓,所有的艺术再现的是非视觉的东西。”
Coomaraswamy对于我在日本所碰到的艺术困惑时期实在是帮助很大,不过这还不是我得到的最重要,最有益的启示。我和妻子在日本遇到禅师才是最重要的启示。我俩都对禅修有兴趣,我们在东京最终找到了一个云游的禅师田中。田中是一个具有鲜活的独立精神的人,他不住寺庙,却四处云游,他几乎不懂英文,但我跟他的交流却是最深入的。
田中竟可以算是一个艺术家,他做起事来是自由、直接、毫无顾忌的。他常说“不用技巧,不用想法”。常有这样的情况,当我们在任何地方--在火车上,或者在咖啡馆,他会突然叫道,“灵感来了,灵感来了,纸,纸。”然后他会抓起笔来飞快地勾勒出一个达摩的脸,因为这时要画脸的冲动出现了。这是艺术自己要进入你的感觉—是在它需要的时候,不是在你要它的时候-这真是令人难忘,充满启迪。我还非常清楚地看到,跟禅师同处一室,就像身处他的祖师面前,而他的祖师也处于自己的祖师面前……这是一个没有中断的长链,一直通到佛陀那里。这是个活着的传承,是我在禅宗的书上读到的谱系,现在,这里存在着的就是,那是活生生的,正直视着我的脸,并朗声大笑。
一天,田中禅师突然对我们说,“佛陀并不完美!”,我们听了大惊失色。然后我就想,是啊,这就是为何佛陀感到人生不完美、为何离开自己富有的宫廷之家、自己去体验生活,了解人生,他置身于这个不完美中,让我们认识到不完美就是人类的本质,这是无数人类行为的源头:新观念,新生活,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努力,我们需要成长。而完美则在不可企及处闪耀着,那是我要从事艺术的原因,事实上,那就是艺术存在的理由。
在日本的时候,我们的许多体验都围绕着实践。这就是所有那些我们碰到的,读到的佛教徒们的作为,这跟理论无涉。当然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做的事情从艺术的实践角度是可以描述的。但是在这个艺术学院化的时代,艺术的训练已经移到社会群体之外,移到一个受保护的大学区域,(这把原是现实世界中传授的方式,变成了一个在类似实验室环境中的理论观察)实践这个词现在已经不再带有同样的鲜活意义了。
当我面对、置身日本艺术传统语境时,我开始看出传统不再是一个来自过去的,人为痕迹很重的模式。当田中禅师惊喜出声,并画出达摩像时,他无疑是和他热爱的两位日本禅画师白隐(1686-1769)和仙厓(1750-1837)相连,然而他也联系着并图解着当下的时刻,当代生活的领域。就像他不断对我们说的,过去和现在是一体的。而实践是贯穿其中的引线,是它把我对于佛教的新体会和我将拿人生作为实践的艺术家连接起来。
问:你艺术中最有力度的部分是你对时间的运用,你怎么感受时间的?这远超过技术之力。你总是通过世俗的材料,比如一个孩子的庆生派对,或一些极端的情形,比如幻觉,来使时间变得可以触摸和感知。
我喜欢谈论时间和慢镜头。你瞧,尽管我和高科技打交道,但我的作品中没有什么是过去不曾出现过的。时间的压缩和延展就是两例,比如人们在经历了车祸之后,其描述很像慢镜头,或者就像他们是旁观者,视线与这个事件平行。有一些事情发生得极快,超出了人的感知,在这种地方你就碰到了感知能力的局限了。然后又有些时候事情发生得极其缓慢,慢到你几乎感知不到,但你知道这个发生在那里。因此,当我在作品中用慢镜头时,就是某些范围内我们所熟悉的一些东西。
不管我们是在谈论长短,快慢,大小,冷热—所有这些我们对周遭的观察都只和我们身体有关。你去想想自然之中的极端状况看,从行星爆炸到山体在亿万年中的渐渐风化--你就能意识到我们的感知力够有多么有限。就像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兼画家布莱克(William Blacke 1757-1827)说的,如果能把感知的途径清扫干净,那么一切事情就会以它的实相呈现给人了—永恒的实相。然而,人的意识和大脑是那种收集资料并作处理的机器之象征,它能把那种超越了生命的更大的事物纳入有符号代表的知识结构中,并以此去作理解或者是操控和歪曲其本质。即使是对不可感知的东西也如此。我们一样也是把这个方式赋予人所操控的技术手段,让它们具有同样的功能容量。这就是这些新媒体的能力所在—先是记录在时间中进行的感受,然后,延展或压缩这些感受,记录时间,或者操纵形象和声音—这便是这类新媒体最初吸引我的地方。
若在禅堂静坐50分钟,时间的呈现方式会叫人难以置信。一只小鸟在外面的叫声可以变成巨大无比的磁力。当时间和空间被开放出来时,突然之间,你会获得巨大的场所。在静下来的时候,你会有了主意、想法、或者神启,这是你在匆忙的时刻不可能获得的。我们的生命需要像这样完全无染的那种时光,所以我们绝对需要去营造出这种空间,特别是我们如今处在时间紧迫感的世界中—或者是我们的精神感到窒息的世界中。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化的世界,这种世界的存在方式已经弥漫了我们大部分的精神空间,迫使我们快些,再快些,然后去做成一种商业进行买卖交易。我们现在需要重新来界定时间,把它从“时间就是金钱”和倡导时间的最高的利用率中把时间夺回来。给它充分的空间,让它用另一种方式流淌,我们需把时间为自己赢回来,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呼吸,让我们嘈杂的头脑安定下来,平静下来。这就是艺术所能做的,就是今天的美术馆所该展示的。
问: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作品,能够给与观众超越的体验,就像佛陀的教诲那样,能够引导人进入自我超越的过程,一条通向解脱之路。
物理世界中的所有事情,包括艺术,都能提供一个出口,从烦恼中摆脱。因此艺术家对观众要下的功夫其实比对作品下的功夫要大才对。艺术作品让不可视的那种力量视觉化了,并且了解一般人也许不了解这些不可视的部分,因此它具有特别的地位。这就是艺术特殊的力量,运用这力量是有艺术才华之人的责任:把一些形象带到这个世界,让观看者受益。
长久以来人们去教堂,看受人尊敬的圣母玛丽亚像。其实这并不是要去体验一位妇女的丧子之痛,而是去和这个形象分享自己的痛苦悲伤,而它能承受所有的人类苦难。换句话说,他们是把自己的故事带到这个形象跟前,而不是相反。观众带来的故事可以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体量巨大的损失、灾难,或者是个人私下里的痛苦和焦虑。但是在所有的情况中,他们都需要寻求安慰、同情和潜在的转化可能性。这一来,观看者就成为这个形象所投射的一个屏幕了。
我觉得你也可以说这个世界就是艺术家的屏幕,我们都把自己的意识向外投射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在以都市为中心的生活,等于是人们生活在投射了许多人思想的人造物和设计出来的结构之中。我想许多艺术家面对这个世界,做他们的作品时来源是很深的潜意识层面。吊诡的是,展示这作品的举动和它影响人的部分,事实上又是在一个完全清楚的意识层面。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出入的过程,在古代文化描述的可视与不可视两个世界出入的过程,就是精神体验的定义之一。我在常常为不知如何为这类东西赋形之时,由衷觉得,当代艺术家真的需要非常清楚他们作品中的精神内涵,清楚自己的作品在一个巨大传承中的位置,而这个传承是直溯我们生命源头的。
如今在这个科技无处不在的世界中,东方和西方的传统缠在一起了。事实上,这还真要感谢我所运用的这些媒介,所有的传统和文化在一起互相碰撞,而且还很激烈,而过去由时间和距离而来的缓冲,现在不复存在了。现在导致人们害怕,暴力行为以及人的受苦之因都在于此。当我们进入千禧年时,信念的系统可以导致人们发狂,比如开了飞机去撞击高楼,让无辜的人丧生,或者是战争贩子,在电视这样的公共媒体上声嘶力竭地说假话,以激发人们的恐惧和仇恨。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如今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比以前彼此之间倒是更为靠近了。
作为艺术家,我认为人们在艺术上的实践活动是一种世界性语言,这和宗教实践具有共性。是这种共性而非个性让我们理解彼此。人们所能领会理解的视觉元素并无需共同的社会政治背景才可以分享。人们都拥有神话,拥有心灵的对话。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作为个体是可以分享事情之实相的—这即是人类共有的感受力。
生,死,喜乐,希望,害怕,悔恨,受苦,创造,神启—就存在于这种非实体的层面中,在这个领域,诗歌比事实更有发言权。我相信,这种传承的保持者,这种艺术和精神的实践原则,在我们如今所处的生存现状中已经是非常关键,非常需要了。

桑福德·比格斯(Sanford Biggers)
方当代艺术中的佛教影响(二):美国艺术家桑福德·比格斯
桑福德·比格斯(Sanford Biggers 1970-),美国著名当代艺术家,他是一个跨学科,多面手类型的人,同时制作电影、录像、装置、雕塑、音乐和表演。他毕业于芝加哥艺术学院。 他在1992-94年赴日本教授英文并开始学佛习禅。他创作的作品在2000年左右在美国艺术界展露头角,受到批评界的注意。他的行为或多媒体作品在伦敦泰特美术馆,在温蒂双年展等重要展览中倍受关注。2009年他获得了美国专为黑人艺术家而设的“威廉强生奖”,同年他还是美国“杰克沃金美术国际大赛”中最后入围的三个候选艺术家之。“杰克沃金美术国际大赛”(Jack Wolg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Fine Arts)是全球的艺术奖项中的最大奖项之一。
以下是比格斯作品选登:




桑福德·比格斯更多作品信息:http://blog.artintern.net/blogs/articleinfo/xinwen/243612
比格斯访谈
(采访者为芝加哥艺术学院美术馆策展人玛丽女士,访谈译自《当代艺术中的佛教思想》)
问: 你何时对佛教产生兴趣?是你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吗?
我是1992年从大学一毕业直接去日本的。在大学期间,我作为校际交流学生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学习。当时有个同学从东京打电话给我,他觉得我应该毕业后去日本,因此我在毕业后设法申请参加了日本美国的交流教育项目,就到了名古屋一边教英文一边学日文,在日本呆了两年。在这两年中我对禅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开始阅读老子的《道德经》。这阅读让我非常开窍。不过我拿这个去和朋友分享时,他们却感到困惑不解;我想,这是一种颇难言传的东西吧。
问:你现在做打坐冥想的训练吗?
我一直都在做,是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对我来说听爵士乐就像打坐。声音,特别是咒语和持颂,就会引出打坐冥想的那种气氛。不过爵士乐通常是一个音乐家或一群音乐家沉迷进了音乐里。我是能在戴耳机听音乐时也让自己完全进入“空”境-对我而言空就是忘我,我能真切地感到自己在音符之间穿梭,置身于和谐、颤动的声波空隙中,音乐家也是在那种地方忘情忘我的。这对我就类似打坐冥想了。
问:当你参加我们的“开悟之会”时(Awake Consortium Meeting--玛丽女士和巴斯女士在2002-2004两年中,在北加州举办的一个佛教与艺术结合的社会项目,类似一个学习班,讨论会,艺术家和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一起打坐,讨论,寻求开悟-译者注),你曾说过,爵士乐就像禅。
这是以它的自发即兴而言的。那些了不起的爵士乐手在即兴的状态中,就是那种……完全的当下。他们并不知道下一步的演奏往哪里去,但在乐队中总会有人给出一个线索,大家就跟了上去。就像考尔荃(John William Coltrane 1926 – 1967 美国著名的黑人爵士乐手-译者注) 他就是达到了“无”的境界。我从考尔荃得来的印象是,他在弄音乐不是为了声音,而是为“行”,为“法”,为冥想入定在吹他那个铜管号的。就像给他写传的作者们说的那样,他的所作所为全在这种地方。他在抵制吸毒之后,就不停地实践训练,在演奏会前他做,在演奏会后他做,在演奏会中他也做。这就是他要的状态,演奏成为他所爱的壮举。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就是把演奏作为一个人生实践去做的。这样的实践方式越来越让他受益,导致他在音乐上走得更远更远,而那是许多人没法做到的,因为那已经成为哲学和精神的探寻了。对我而言,考尔荃就是“无”的境界。
问:如果我们在做艺术作品时运用创造性思维,那“无思”则意味着思想对一切的未知完全打开。而那些很擅长进入自发即兴状态的了不起的爵士乐手们,或许可以把这种实践的方式和视觉艺术家们分享。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创造对他们意味着发现,而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程式。
这正是我作为艺术家的立场,也是不少其他艺术家今天的做法。一切基于一个意愿就够了。你的手,脑,眼不必紧系于思想,并时时提醒说:这儿放上红色,那儿放上蓝色,这儿画一根直线,那儿画个圈。不,要让创作不再是你头脑中的东西,而是一个出自内心深处的东西,潜意识中所流露出来的感觉。当我的思想中不再有“我是个视觉艺术的创造者”时,我就进入了“无”之境。我会想到考尔荃,这可不是指作品上的像,这无关作品的样子,而是关于没有答案的探询。这也与听众无涉。这便是让自己置身于无的境界和置身于娱乐界的不同--娱乐是完全跟观众走的,当然,我知道了不起的表演者能兼顾两边。
问:你允许观众进入你作品。即使在美术馆中你也让观众进入体验并与作品互动,由观众来完善这个作品吧。
对我而言,体验妙不可言,它才是我作品的要点。在我的霹雳舞作品中,我只是提供场地,是观者和舞者在上面做出行为,而这才是艺术作品生命所在,是奇妙之所在--在未知之处。这就像爵士音乐家创造了16或32首酒吧里的曲子一样,然后在32个酒吧中每个人都去自由发挥,最后汇总来时,已经延伸到64个酒吧了。 这音乐开始提供的就是结构而已。然而在结构的区域内却可以产生这么多东西—奇妙之处就在这里。
我在创作作品时照这个样子做已经好些年了,我的第一批雕塑和非洲和亚洲的崇拜有关。我采用仪式的方式,还有互动的方式做作品,这样人们就可以用上这个作品。当人们用上之时,这些雕塑就成为很有力度的东西了。这导致我去做可以让观众有体验的艺术作品,观众与之互动,不过他们不要把个人化的和自我的意图放进去。
问:能说说你如何在不同文化和传统之间架设桥梁,或融合它们?你的艺术是如何成为文化交流的实践行为的?
如今文化似乎变得更可塑了。这部分来自于这个世界投射的印象在不断改变,部分基于交流技术的发达。人们现在已不仅是寻求获得财物,他们会寻找思想,改变,群落,希望,尊重等等。人所关心的这些东西对做艺术项目时是非常重要的。我作为一个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美国黑人男性,在做艺术时当然会表露我所来自的文化,以此为立足点再进入另一个文化。这就对每个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作交流了,借助能用的,人们熟悉的东西。美国的波普文化,特别是美国黑人的流行文化,迅速地被全球的年轻文化群体吸收,而成为共享的语汇,借此可以很方便地交流。当我把自己的文化和不同的文化连接时,我是想把它们放在一起,然后看能从中生长出什么来:是否能做一些什么不是嘴上说的联结,而是实际上的联结?我觉得存在着一种充实在天地宇宙间的振动频率,即使无需见面也能把我们连接在一起。通常,我们在想、我们在感觉,这和其他人是处于同一层面中的,即使我们在肉体的层面是分开着的。我想我的许多作品是基于这个想法的试验,通过试验来看看,这个作品是否有效?比如看看匈牙利人是如何看待霹雳舞的(或是我如何能在那里找到霹雳舞)?日本人是如何通过佛教的法会和美国黑人发生联系的,他们之间是否会有连接?
问: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你去日本曾参与的项目和做下的作品吧。
我在2003年去日本时和一座禅寺联系上了。我想做一个磬的“合唱”节目。那座禅寺的主持对这个主意很是喜欢,让我们用他们的寺庙和他们存有的磬。他们的磬有些非常大,有些非常古老,有一两百年以上!这个作品其实早在去日本前就开始构思了,就始于我在美国北加州禅修中心参加的你们那个“开悟之会”项目之时。我是看到了Ann Carlson那时在给禅堂安排表演时用了磬所受的启发。我那会儿还跟Yvonne Rand 花了很多时间谈这个事。我到日本后,我把Hip Hop(80年代美国开始流行的黑人街头文化-译者注)的银饰行头(项链,手镯,挂链)溶解了做了两个佛教法会上用的磬,就像家庭的佛龛中用的那种。溶解这些东西等于是把当代的Hip Hop文化和年轻人文化中那种叮铃当啷的玩艺儿作了淬火提炼。要做出那些磬,融化银是必经的过程,我还在东京的一个小店中组成个小组来做磬。我的录像对此只是个单纯的记录,没有什么体验性的东西在其中。
然而,这些磬内保存了什么,这东西会比体验更为长久,非常可能比我们的生命更加长久。这些磬保存着附着于它的故事和经验,它们就加入进来,就成为很有气场的东西。那些在日本做在日本用的磬,被寺院中的僧人和居士敲响, 那些经验使得这些磬成为储存记忆的容器。所以磬不仅只是用具或体验的见证,它们某种程度也随境变迁转化,人类一直都存在这样的器物。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做这作品的主要部分:想法存于作品内部,然后让其视觉化或听觉化。我想如果你能感觉到这作品的意图,它在效果上就能超越视觉的体验。这便是作品的魅力,影响力,它让我们继续前行。
问:你能描述一下这个“磬的合唱”是如何在日本的寺庙中表演的。
我们所有的磬-寺庙存有和我们后来做的-大小共有16个,然后有16人参加,分四组,每组围成一圈。每人有一个磬。第一圈的第一人开始敲第一下,然后第二人接着敲一下,如此往下传,每一个成员可以在自己认为恰当的时候和方式来敲,这样一圈做完传下一圈。这是个比较松的方式,因此每个成员没有跟不上的情况。其中最有力的部分是每个敲磬者当下的创造力。起先许多人认为即兴是很抽象的,他们可做不来。日本的参与者会说,我们做不到即兴。日本人通常是太严格太受管制了。但后来这个即兴的作品却被做得很好,他们全都毫无困难地做到了即兴。
由于我们这个行为作品是在寺庙里做,因此在开始时参与者先在寺院主持的带领下坐禅15分钟,于是每个人都在很开放的心态中进入作品。 你若是在录像带上只看参与者的面部表情的话,你可看不出他们什么时候在坐禅,什么时候已经是进入表演。每个人都非常放松,只在倾听。我事先就对他们说明,你只需知道你右边坐着的人何时敲了磬,但你敲的时间完全由你自己来定。所以他们都闭着眼睛,全心倾听,去感应自己应该什么时候敲响自己的磬。敲响不意味着档住什么,而是让某些东西进入。这不是缺席,不是独自,而是和一群人一起。每个人不是关在他们自我的小空间里。从体验而言,这让16个参与者达到了打坐冥想的状态,唯一把所有人连接起来的是倾听和声音……那是个周六,除去磬发出的声音,就只有外面的雨声,这真的是非常棒。后来,参与者没有人从艺术的角度来谈这个作品。
问:许多人想到打坐就是安静沉默,从外部世界移开,独自相处,可你谈到打坐说的是缓慢或行动,静和闹。
我认为,打坐的目的不是叫人要被什么感动了,实际是“在那里”而已,是叫人放下对自我的感觉。这就是“当下”之意。我们要操控世界的习性已经根深蒂固,看看我们现在生活着的世界的现状,过度的资讯,虚幻化的现实,人们过于起劲地用电子的方式做一切事情了。是啊,这是更快了,但同时却是疏离,你不必把自己放进去的。我们把互相联络的关系变成了像电子游戏似的:点击,裁剪,粘贴,前后移动,短信,电邮,手机,所有这些数码的手段……它们叫人疏离。鲜活的体验变成了越来越是一个腔调。这个腔调和我们生命用的是不同的步子,不同的回应。结果你必须在虚幻和真实的区域之间找平衡才行。
问: 你能说说这“磬的合唱”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又如何能对你的艺术创作有益?
在做这件作品过程中,我想,在编排上的每件事都已经落实在恰当的地方了。你知道,我就是这样坐着跟那个寺院主持说话的,用的是日语,他的很多回答我根本听不懂,但我能感到有非常明确的心念在引导着我。我因此想到,我为何来这里,所有这些最终会怎么样发生—就像我和那个主持坐着说话,他在说重要性什么的,而这个事件能顺利做成吗?这么想的时候,或许我是皈依了佛教的缘故,我油然感到自己所说的,所感到的是如此的舒服顺畅,这是我过去经手事情时从未有过的。
现在我真是在做和分类形态有关的事:为什么一件作品必须是声音的方式,音乐的方式,或者雕塑、素描、油画的方式?我所要试的是能置身某处,而作品最终是难以言传的,不是用一种两种分类可以去定义的,而是两者皆具:什么是实验性的形式,对作品而言它是实验性的,对于观众应该也是,那不是一方去迁就另一方,一个人去迁就另一个人,那该是一种频率,把每个人吸引到一起才是吧?我不知道如何为此定义,但知道这会是一个更大范围的体验-是很恢宏的体验时刻,我也不知道然后会是什么样子。眼下我还是被局限着,就像被局限在我这会儿的描述方式中,我也局限在如何把这个做出来的有限的知识里。

厄尼斯托·普荷(Ernesto Pujol)
西方当代艺术中的佛教影响 (三):厄尼斯托·普荷
厄尼斯托·普荷(Ernesto Pujol 1957-) 美国著名当代艺术家,以从事观念艺术和通过艺术项目推行教育为创作特色。他出生古巴哈瓦那,在移居美国之前,分别在波多黎哥,西班牙生活过。无论在哪个国家学习艺术或者哲学,他都热切地追求精神上的开悟。他从学校毕业后进了美国南部的一所修道院做了四年修士,后来重新回到社会做艺术家,并欣然皈依了佛教。因为他通过比较,感到东方佛教比西方基督教更能让人得到精神的开悟。一直以来,他的艺术的实践都放在如何启发人,达到开悟解脱。他的作品大部分是行为艺术,选一个特殊的地点,让参与者用完全静默的方式,或不动,或走动,来静静体会个体的存在,然后在这种体悟中让自己对自身的存在尽量开放出来--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被囚禁在观念和陈见中,从来没有也不会如何真的面对自己。他把自己称为是“社会编舞者”-设计行为艺术的项目帮助人了解自己。 他的艺术创作在90年代后期被艺术界注意。1997年他是第二届南非圣约翰内斯堡双年展的美国代表艺术家,一直以来,他受到许多基金会的嘉奖和赞助。
普荷的作品选登:



普荷访谈
(采访者为芝加哥艺术学院美术馆策展人玛丽女士,访谈译自《当代艺术中的佛教思想》)
问: 艺术家的生活和僧人有何相似?艺术家的实践和僧人的实践有何相似?
我不认识多少艺术家像僧人那样生活。不过我在1980年的夏天从艺术学校毕业后就到米匹肯修道院去做了修士。那是在南卡罗林那州,查尔斯顿市附近的一座小小的隐士修道院,在时涨时落的考珀河的河岸边上。那是罗马天主教会珍视的与世隔绝的生活,那确是地处美国南部沼泽地的中心地带,在殖民地时期是由黑奴耕种的稻田,最后这地方在亨瑞和露丝的手中成了很艺术化的意大利人的产业,他们后来把这产业委托给了修道院僧人们管理。那里的生活非常严苛,要把自己全部奉献给沉思冥想,以期在冥想中获得升华。僧人们被称为冥想者,而真正说来,他们是通过冥想要进入纯精神的层面。
谈我自己还真没什么可说的,不过,那几年特殊的生活让我尝到了一无所有,完全孤独的严苛修行,遵循的是圣伯纳迪克的修行法规,[San Benedetto da Norcia 480–543 意大利人,是天主教在5世纪的一位圣徒,建立了严格的隐修、苦修的修道院制度,写下了“圣伯纳迪克修行法规”(the Rule of Saint Benedict)成为西方后世修道制度的法则,他因此被认为是西方修道院的建立者。其地位颇近似于中国禅宗丛林制度的建立者唐代的百丈禅师。是百丈禅师首次为中国的寺院建立了修行生活的“百丈清规”-译者注] 在农田中耕作,学习先贤们留下的著作法典和中世纪的神学,从事仪式性的礼拜祈祷。我们在午夜时分就起床,在主堂中颂唱圣经“诗篇”,等候朝阳的升起,作为赎罪和新生的象征,当整个世界在沉睡,在罪行中时,我们却做着精神的守护。然后修士们一起吃饭,工作,然而保持着完全的禁语。我们的生活被净化成不视觉化的,不具名的了。我们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过去圣徒的名字,穿着僧袍和僧帽,把自己的身体从自己的视线和别人视线中藏起来。我们这些人处在一个隐修的团体中,却彼此并不相知。修道院应该是处于世界末端,在天堂和人世的中间地带。
四年循规蹈矩的生活后,我在1985年夏天到纽约去继续自己艺术家的生涯,拿着修道院发给我的,来自罗马教廷的特拉普会隐修士的证书。现在我冷静回顾,我的修道院训练为的是破除旧我,原来那个从世俗生活中进入修道院的人,渐渐转变到空,成为一个深邃沉黑的虚无,但并无精神上的开悟,有的只是盲目的信念:上帝的创造力终将会来处理一切,会在你死后重新塑造你。
我还能记得在修道院中自己的旧我死去的那一刻。在做了一年的圣职自愿者,两年的见习修士之后,其间做了大量低贱的劳作,以克服自我的骄慢之后,在一个寒冷的雨天下午,我从田里回隐修处,身上沾着鸡屎,疲惫不堪,突然间仿佛像被电击中一样,我顿时感到自我消失了,我不再是那个三年前进入修道院时的同一个人了。我最终摆脱了自我的束缚,在经历的所有哀伤中,崭新的自在自由从中升起。我当时由衷感到我该在修道院中了此终身的。然而,很意外的,这个获得新生的人又回到了世俗人间。或许,这才是所有这些体验的目的所在:在修行中获得动力,到这个世界中去做艺术家。去修道院当修士需要很大的勇气,而成为一个艺术家也一样需要很大的勇气。
问:你到外面的世界重新开始时,你是从纽约的慈善机构为流浪汉们工作开始的,这样一种和社区打交道的方式,你视为艺术的实践吗?
在见习修士的斗室中睡木板床,过了一无所有但纯净的生活之后,我去流浪收容所睡在满是臭虫的帆布床上,倒没觉得这是在做以表演为名,以记录我行动过程为名的艺术作品什么的。不过,我非常清楚,即使这不算是一个新的训练,这却是一个根本性的再教育--相对于我在过去学校中的教育方式而言,相对于在物质层面上和当代社会以及执著的想法分开而言。可以说,我的做法属于现代化早期的事,好像当年梵高着迷地为矿工们和种土豆的农夫们去做牧师那样--虽然他后来是悲剧性地用自我毁灭来结束的。我相信在现代主义的某个时期开始,我们让自己离开了沉浸其中的现实社会的汪洋大海,而转移到跟社会作巧妙周旋了,结果导致了都是观念的象征性表演而已,后来还有政治正确的风格。我要的却是真实。
古巴革命的暴动毁坏了我们家那样的无辜家庭。我的父母那时还未年老,工作非常勤奋,对我们非常保护,一直对我这么说,一切会好的。他们的话在不自觉和无意中与我对现实的感受是有抵触的。而我小的时候,当然看不到父母在内心深处所受的苦。所以从孩提时起,无论在我个人生活的经历中还是从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都为了能够面对现实而获得真实的感受而挣扎:寻求完全的解脱,既为自己也为别人。因此我一旦追寻精神的体验,我就想知道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贫困-精神和肉体的。所以我选择去田里躬耕,而不是坐在课堂里读书,我相信社会在活生生地改变着,而艺术的理论却要渐渐破产的。
问:你现在的实践性作品是要减缓这个世界的苦痛吗?
我是试图通过提供一个舞台性的时刻让人在其中全心行走的方式对一群人表达一个话题。我是很用心地去营造一个冥想的环境,欢迎人们进入并渐渐打开他们自己,我提供通常是有历史争论的地点或是受人争议的环境。[普荷有一批行为作品是让自愿者在某些选定的场合默默行走,通过全心行走的方式,体会到个体当下的“存在”这样的切身体验,因为当代生活让人的注意力全部移到外部去了。普荷希望动用人的行、住、坐、卧这类最简单的方式让人开始关注内在—译者注] 我最近的一个艺术项目叫做“成为土地”(2002-03)那是肯萨斯州的赛林纳艺术中心支持的项目,基于上世纪的作家维拉.凯瑟[WillaCather 1873-1947 美国女小说家,作品多次获奖—译者注]作品中的主题:人们如何在土地上居住并过度耕种,后来耕种者需面临的经济的压力。还基于《沉默的鸟》这样的书,[美国一本很受欢迎的写鸟类的散文集-译者注] 那是诗化的视觉散文,关于遗弃、美、孤独。
我不得不一直去修正我过去学来的东西。埋首于罗马天主教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文献,其中向人呈现的是,灵性的追求被歪曲成了赎罪的异常狂热。上帝在痛苦,而这痛苦只有通过我们精神上的受难才可以释放缓解;上帝在愤怒以致要结束这个世界--就像圣母显灵所警告我们的那样,因此信仰的大众赶紧把基督放在十字架上去宽慰上帝,让上帝为此难过悲悯,并把他要毁灭我们的神圣旨意收回去。
我做的艺术不是关于受难的,而是像佛陀说的那样,是关于解脱的。如果人生是苦,那么艺术,就像精神本体,应该指向解脱。因而,我追求度众生的菩萨道,通过由行走的肉身所遭受的感觉指向解脱的法门。我做的艺术是综合的实践,不只是多手段多媒体的那种方式,而是融合艺术和信仰的那种方式。
问:涉足社会大众的一些事务需要持续的坚持。很多时候,这种有涉社群的项目,社群会把它自身的需要强加给艺术家,或者强加给审美性。如此,你何以在创作继续保持谦卑?
当我要做一个以社会大众,以指定地点为项目时,我一定得再回到我的修行之地,那是自我批评的过程,新的作品得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我力图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谦卑到不做任何设防的人,完全赤裸裸地,一无所求地出现在一个社区的大众前,等待、期待着被重新充满。这个过程需要庄重和谦卑的力量去平衡社区大众的和美学的需要,运用艺术家的判断,形式上所受的训练以及风格等所有这些。这样做事要求的是对自己的实践方式有信念,坚信有超越了我们,超越了形态的更宏大的东西在。在禅修者的情况中,那是存在于心念起伏的无尽汪洋中,经过起起落落,最终归于涅磐。对艺术家而言,这或许正是艺术作品的目的:让真相呈现,使社区大众能接纳真实,以期转变他们自己,转变美术馆,转变我们自己。
艺术是先知,是聆听来自大众的信息,并把这个信息强化,而不必照顾如何被听。先知向来不大受欢迎,因为其使命常常是要对社会和它的系统作批评,先知谦谨地提出的观点是会被违背或被压抑的,因为当事人怕失去自己威信。我喜欢艺术家是文化工作者这个定义,因为这定义把艺术家的形象和谦卑合在一起。在全球资本化时,谦卑早就失去了价值,谦卑的人被视为无能,和善被可悲地认为是软弱。但是,当代艺术家需要为自己重新获得谦卑,以期能够恢复社会有史以来的那种合理处。我所信奉的从事艺术的方式只在能包含这样谦卑的方式中,力图避免智性上的傲慢和思想上的自以为是。这和人所周知的加尔文教(新教)和许许多多基督徒及佛教徒所推崇的最高德行一致,那些来自60,70年代的前卫艺术家也是这样的态度。那类傲慢自大的态度压根而违背了从事艺术是为社会服务这个初衷的。
问:你能否说说或者比较一下基督教僧侣的思路-这常常受人审查-和禅“当下”的思路?
罗马天主教的秘籍谈论的是当下时刻的神圣性:要像马上就要临死般地全心地活在对完美无缺的慈爱对超凡入圣的热切向往中。当佛教说到全神贯注,并去意识自己的呼吸时,也多少有这个意思。没有什么比注意到每一次呼吸更为当下了,僧人和艺术家相似处是,都需要全神贯注,并不断地探问深入进问题之中,比如有关解脱,有关如何在当下解脱,或者是些小的问题但连接着重大的本质根源。这样去实践要求的是,必须放弃认为僧人或艺术家是可以给出答案的人,这里要学会的是公开地说出“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谦卑但明智地承认无知的态度,然而这个方式导致的是……“不过,让我们来一起发现答案”。我献身于求真,但比求真更重要的是让自己谦卑下来,通过谦卑,人的感受会变得澄澈清晰深邃。
我目前已经皈依了佛教。我觉得自己似乎早就是个佛教徒了,虽然我没有得到这样的称谓。实际上我的精神生活曾一度慢慢中止,我感到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有许多制度化的东西,而那些东西注定是要毁坏的。基于宇宙间成、住、坏、空的自然律,没有东西是保存得住的。但一直以来我只是自己私下这么去想而已,就像我没法拿这些到艺术界去谈论一样,艺术界把一切信念都当成攻击的对象。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一个写作的朋友很郑重地向我推荐了一些佛教书籍,我一读之下,简直如饥似渴,我把自己的身心全扑了上去。其情形是,这些年来我所认可的,我所生活的就是这些东西,我找到了自己的家。
问:是这些让你重新回到艺术的?
从事艺术并非不像禅的修行,把你的思想空掉,去掉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尤其在指定地点做那种不保存的作品时—我再说一遍—是你的内在本性和解脱之间的一个隐秘对话向外开放了。这是自古以来的修行方式:不知结果会如何,但非常耐心地信任这个过程,把自己向未知开放。
我尊重和欢迎这种从事艺术的方式:不停地愿意付出一切,并愿意面对外界的支持乃至是外界的敌意、艺术界伤人的批评去做。这是痛苦的,不过若说这么做仅是为了能让自己变得皮实,其实不对,因为那些筑高墙似的自我保护,会让自己变得愤世嫉俗和疲惫不堪。从某种角度说,你该做的是不设防,即使受伤也不设防,因为就是这样的不设防才会有容量,有容乃大,这便让你向新事物开放,真正的创造力才有可能出现。不过,这并不真是毫无准备的赤条条的人,这是因为愿意才让自己不设防的,这个愿意来自过去的训练。一个小和尚也许看着不起眼,毫无地位:弱小,无害,愚笨,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但是这个谦卑的地位是他自己愿意去做的,因为这是深究事相的出发点。这就是我作为艺术家所选择的方式,跟出家人没多少不同。
所以我尽管在纽约住了十几年了,我已经有了足够的精神保护,让自己的心神纯净。实在说这并不是叫人很舒服的生活,因为纽约的生活一直在考验人,纽约因地处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置身其中自恋般地打造出的形象是,要新崭崭的,轻松愉快的,可以分心的,逗人高兴的。作为一个佛教徒,我要让自己面对令人失望的浅薄的艺术现场-我曾天真地期待它是充满人性温暖的,是让艺术和社会之间有充分对话的,是属于一个有批评角度的文化传承的,那都是我涉猎不深之故。有时,我是太出世了,不过我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方式。
我们眼下的这个艺术界,急切地追求成名之欲望使其变得很无人性,特别是在美国现代化发达的商业操作推动下,就像流行杂志和电影拍摄去追捧波洛克以及后来的沃霍尔所做的那样。如今,对人的关怀被做成了是文化上一些成就而已,而不是出于真心去全力以赴达到彼岸。这种对文化成就的曲解导致了不健康的,过度的竞争,这在毁坏艺术的群体,丧失了做艺术应该是深入的文化实践的意义。
问:那么,对你而言,从事艺术是一个精神的跋涉了?
精神灵性是处于资本主义之外的,不存在精神有所成就这样的东西。但精神和艺术却属于我们人类的最高层次的表达。它们都具有连接我们基本感知和思想的能力,乃至能对一些昏沉的人振聋发聩。最好的艺术和精神灵性是能让人在当下解脱的。对我来说,艺术是开悟,是思想进化中形式上和文化上的一种表达,这就是叫人开悟,叫人在那个时刻抓住开悟的时机,然后解脱。理想地说,艺术正确的实践方式应该像许多高僧大德们在精神的真修实证时所得到的结果一样。
扩展阅读
艺术档案 > 大史记 > 艺术思潮 > 西方当代艺术中的佛教思想:森万里子
www/39/2012-08/723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