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国各地现代艺术小组的陆续解散,以及各类艺术杂志的相继停办,政府和舆论对当代艺术的强烈排斥,让已经逐渐适应自由环境的中国艺术家在茫然中不知所措。但艺术家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态度没有改变,圆明园画家村成为散落的艺术家继续寻梦的乐园。
1990年,是方力钧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从安稳的环境突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现实生活中。大学毕业后,从学校进入社会,所面对的生活压力和经济困窘。从这一年开始,方力钧的作品呈现出关注自我意识的表达。
元旦,被迫于一天内搬迁至挂甲屯农民院落。
方力钧自述: 大学毕业后第一个寒冷的元旦,一亩园的房子到期了;房东极其愤慨,因为我违反了协定;第一,我曾经答应他们只使用外屋一间房,只一个人居住;可现在,我不但使用了里屋、还弄来了个显然不令他们喜欢的人同住;并且,我还偷偷使用了他们闲置的电褥子,并且烧坏了它(也险些烧死自己,但我没敢这样告诉房东);我无话可说;我根本不记得曾有过使用一个或两个屋子讨论;我偷偷地试探老于,是否可以先搬回北大,如果让房东觉得找回了些面子,也许还可以多混几天,甚至熬过这个冬季。这个房子里虽然没有暖气,虽然也并未生火,可借了两边邻居家的余温,还始终比外面温暖;更重要的是,我已经认为这是我的家了。在满世界冰天雪地的此时尤其如此。但于天宏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家伙拒绝了我的胆怯的要求;当房东第二天再来而且再次看到老于时,他们平静但坚决地告诉我,明天,也就是1990年的元旦,我必须结清剩余的钱,并且搬出这所房子。
我年青,好身体,火气旺,却如此不可思议的老实;我付清了余款,几乎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一大早跑去周围的村子找房;天气如此寒冷,又是大节日,居然在一天之内,找到了一所农家院落。在北大西门的挂甲屯;那儿本来有两个村子,漏斗桥和挂甲屯,现在己混成一体了。一个挺大的院子,一个很大的屋子,角落里堆满了木头之类的杂物;大屋子的西头,有一件十几平米的小房子,房东告诉我,70 元的月租,只是里面的那间小房,至于那间大房,只可以通过,不可以使用。顾不了许多,付了定金,急急忙忙跑到北大总务处租车房,租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记得来回跑了四趟,搬完了家里的一切。尽管天气奇寒,我的绵衣裤里面,都已湿透了。
无论如何,我有了新家。不管多么不像家,毕竟不是露宿街头。但我的新家却把于天宏吓坏了,一个若大的房子,四处漏风,地上堆着农民房东的拉圾宝贝;租用的那间小房,地面凹凸不平,没有床、没有暖气,甚至没有一个蜂窝煤炉子。
老于来这边看了看对我说:“我要搬回学校了,宿舍里有暖气,这儿太冷了。”我没有回答他。他是对的,只是我实在顾不得说话,这个新家,距离可以睡人,还有太大的距离;我需要几块砖头,好把床板垫起;也许还需要找到块塑料布放在褥子与床板之间,好挡住外面的寒风。
1月5日,好友老魏来信。
力钧先生:
来片收悉,甚是感动,但我又怕你更加感动,让我妒嫉。因为我在离开北京的那天起,就把你做为雷锋叔叔的形象一样永远永远的埋藏在心里。你的诚挚的心曾很感动过我,可惜我们已经分离,但曾经感受过的一切系着所有善良人的心,所以,请别在意,请别过意不去,这没什么,因为我常知道你的消息:“力钧辞职,过很逍遥,活得很健康。”“糟啦,我又伤了力钧先生”等等等等,可你却终于没有我的消息,怪哉?因为到处都可能有我的消息,我像一棵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只要活着都将为祖国为人民发光、发热,贡献力量。
二月本人去北京,你在吗?很希望很希望见到你,更像看看你一亩地中长了些什么东西,请备好清茶等我,再见!
用心祝
好!
好!
好!
老魏
1990 年1 月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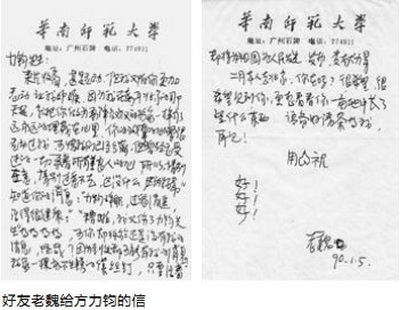
与刘炜、魏冰等一起至邯郸陶瓷厂,制作陶艺。
方力钧自述:冬天的时候再次去邯郸,还有我们班的刘炜和魏冰,他们分配到一个台湾人开的工艺美术厂。老板让他们出去做点陶瓷回来,说你们留一半,一半给我,差费由老板支付。我帮刘炜和魏兵安排做陶瓷。老板给了 3000 块钱,3000 块钱如果是按照正式手续来做的话,是做不了什么的。于是只好偷,跟作贼一样的做陶瓷,几个人租了一间房子,然后跑到陶瓷厂把泥偷回来,画的白摊也是偷来的。烧的过程也是偷着弄的,最后从厂里往外运,也是偷着干。就等于把这 3000 块钱除了租房之外都变成伙食费了。每天就是吃吃喝喝,最后把这些偷来的东西全部运回来。
与刘炜交往日密,筹划作品创作及展览。

穷困至极。在于天宏、陈红协助下,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园、宿舍内贩卖明信片。
方力钧自述:一次,像往常一样到外文局林朴处蹭饭,遇到了美院的老校友,正在批发单位出版的贺年卡;我进了一些,跑到北大学生会去卖,只卖出了一部分,又同于天宏跑去宿舍卖,还是没卖完;老于不关心最终实现的利润,他有不菲的北大教师工资,不可能从我的角度想我的处境。
陈红在清华教书。也许是为了我当时的苦难所感动,或者仅仅是觉得好玩;我轻易地说服了她,同我合伙出售剩余的名信片。因为她是老师,还是班主任,可以自由出入各个宿舍,对学生来讲又完全值得信赖。我们的业绩出乎意料的好,出于感激,我主动提出将收到的菜票全部归到她的收入里,要知道,在我们没有这个生意之前,我总是仗义地在她那儿吃了一顿又一顿;她老实不客气地接受了;很快我们都发现,她的收入,要远远多于我的。在学校里,菜票经常比现金更流通。当时我们俩儿一定各有心思,我这边儿一面后悔,一面想将来混饭的时候多了些资本;而她那边儿,却坚决不肯收这部分了。
张林海到方力钧挂甲屯工作室。
方力钧自述:我们搬的地方叫挂甲屯,那是我最贫困的一段时间。
张林海从天津来找我,一开始知道我是在一亩园住,后来搬家了,他居然还在那一带打听到我搬到挂甲屯了。当时正在画素描,兜里只有 30 块钱,每天不出门就是画画,有一个电热器,就是学校画模特儿时用的电散热器,我必须仔细去规划,每天买半斤面丸子,面丸子是 2 块 5 一斤,买半斤就是 1 块 2 毛 5,一袋面丸子大概要吃两顿,中午或晚上有一顿是去长征那里吃半斤水饺,这半斤水饺就可以算是正餐,早上晚上吃几个丸子就算了,晚上去北大,找于天宏他们混点啤酒什么的,或者混个夜宵。兜里只有 30 块钱,每天的花消至少是 2 块 5。
张林海来时我正在画画,心里就咯噔一下,心里开始盘算,怎么办啊? 30 块钱,是这段时间仅有的生活费,要是两个人出去基本上就把这 30 块钱花完了,就没戏了。于是一边盘算一边画素描,那张素描画糊了。当然与他的到来有直接关系。我一边想着他的事,一边往上涂铅笔丝。家里有一瓶二锅头,时间长了,基本上没什么酒味了,我说你先喝点酒,他就倒一点酒就喝,突然叫喊:这是什么味啊?我说你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他说你先画吧。最后张林海有点不耐烦了,说出去吃点东西吧。我说等一会请你吃饭,心里却在想,到底该怎么办?这时林海就开始在旁边嘟囔了,什么意思啊,老方啊,我大老远跑来的,我都饿的要死了,你要是不请我吃饭你就直接说,我自己出去吃。或者咱们出去吃我请你也行。最后我说:林海,咱们是好朋友,你觉得吃个饭重要,还是我搞事业重要?张林海气得无话可言。我还在画画,一转眼已经从上午混到快晚饭了,我是一边扯皮一边拖延时间。冬天很冷,他看着我的电暖气上面有几个小丸子,但我自己也不舍得吃,去假惺惺地劝他吃。一瘸一瘸的。找了那么长时间才找到我这儿,一直耗到晚饭的时候,实在没办法打发他,看来不请他吃饭是过不去了。最后跑出去到长征饺子馆,买了一斤饺子,还买点花生米和啤酒。
裴姐借住挂甲屯工作室。
方力钧自述:很快,我便遇到了令我哭笑不得的一件事,裴姐来找我说自己有点钱,但不敢乱花,六、七千块钱在银行存了死期,然后说要到我的画室借宿。我有一只电暖炉,一个小屋子,都交给了她,自已在外屋搭了地铺,好在还多了只很薄的暖袋,靠着年轻的火力,将就着睡。白天到小屋里,就着电暖气没早没晚地画那两幅整开纸的素描。
张志与莫保平闹纠纷,康木解围。
方力钧自述:这时候还有几个朋友在,也有在外企工作的。人家都可怜我们,同情我们,在外企工作的平常偷一点东西,什么可乐啊、罐头之类的,就做个 Party,我这边请了康木、张志、莫保平,还有裴丹凤。这时候张志就把二锅头起开了,自己先倒半杯喝了,喝了之后又倒了半杯,在我们没注意的时候他已经喝多了。然后坐在女孩旁边,就开始撒娇装傻往人家身上靠,因为大家都很熟,女的跟他还很客气,但一会儿就过分了,女孩只好躲他,他再往人家身上靠,女孩就再挪。挪着挪着,就影响到旁边的人,旁边的人也得挪。然后下边的人还得挪。这样下来大家就变成转圈了。这时候他的酒劲上来了,不过瘾就开始动手,一动手女孩就叫唤,就从坐的地方蹦起来,然后张志就骂,你个婊子,我挨你怎么了?我碰碰你就好象是怎么样了。话出口非常难听,这时一帮人不干了,好不容易有女朋友来了,本来挺高兴得事,你一个人这样一搞,大家都不高兴,于是所有的人都站在女方立场上谴责张志。最厉害的是莫保平,两个人就动手打,玻璃也碎了。还没吃的瓶瓶罐罐盆盆碗碗全都弄翻了,霹雳啪啦乱打一痛,这个用拳头那个用脚,两人又各自去找东西。最后是这个人举着菜刀,那个人举着棍子,女孩吓哭了。两个人相持着,我们抱着这个抱着那个不敢松手,不知道他们要闹到什么程度。
正在无奈间,却听康木不轻不重的说一声,“张志家着火了 !”在场的人一下子全动了,张志第一个往前院跑去,其它的人全跟上来,我心想康木太牛了,用这种方法解围了。等到大家赶到前院,果不其然一切如常;既然来了,张志掏出钥匙打开门,才露一点缝,一股呛人的烟钻出来,张志一急,手里用劲,门才打开,屋里浓烟处火苗一闪,沿着墙壁上的布一下子着起来,本来在人群后面的康木一个箭步址下屋里的白布,三下五除二就在屋里跺灭了。大家一阵唏嘘,很快就感到寒冷;赶紧回到饭局,现场己惨不忍睹 ; 还没有来得及享用的一切,被踩得稀巴烂,窗上玻璃也碎了,寒冷的风吹进来像往屋里扔刀子一般,东拼西凑的杯子、盘子也损坏了不少 ; 真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大家看着一片狼籍,也无心骂娘,各回各家罢了。第二天很早被冻醒了,玻璃碎了还没来得及换;玻璃杯里的残啤酒也冻成了冰块。
从于天宏等的生活照片中获得大量创作素材,开始黑白油画《第一组》的创作。
《像野狗一样生活 1963—2008方力钧文献档案展》 (卢迎华 主编,视界艺术出版社,2009 年 4月第1版 P108):
卢:你提到 1990 年开始黑白油画第一组的创作,是从于天宏等人的生活造型获得大部分创作素材,谈一谈这一组油画,第一组。
方:第一组……第一组就是到圆明园最早的工作就是这组油画,这组油画就一直持续到去辅仁大学,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吧,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
卢 :这组油画用了一年多时间?
方:对,一共七幅,用了一年多,搬了无数次的家。那个时候我有一点像妄想狂一样的,因为受到某种刺激或者冲击,去创作作品,每天感觉好像所有艺术家,所有的作家啊都在拼命地工作,自己的压力特别大,因为你本身创作的欲望就强,然后现场你又看到了那么多的东西,然后你又突然之间有点儿“开天目”一样的这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全部都加起来,那几年的时间基本就是一个工作狂的状态。
又回到了技术问题,你用什么样的技术方法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我又回到了最基本的,素描的第二组,也就是这个油画第一组的预备,还是用铅笔,纸上的。预备好了之后又变成画油画,我就想怎么样可以把技术的难度降到最低,我想就用黑白颜色就好了,这样你就不用画冷色啊、反光色啊、色彩关系啊什么之类的,它之所以是黑白,就是因为当时一个是把技术难度降低,另外一个我觉得当时的心里状态用黑白来表现是最好的,正好能够吻合,就是用黑白的来画。


至大连,同田彬、杨茂源一起临摹七十幅安格尔的商品画及坦克部队军用教学图。
方力钧自述:杨茂源在大连催促我们。他在那边儿找到了两笔生意 ;对我们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我同田彬轻装上路。也没有旅行包,临走时找到一个满是洞的手提塑料袋,幸亏还有胶带,就一小块一小块地将几十个洞粘起来,试一试,还结实,放了些零碎,直奔海运售票站。
在大连码头,杨茂源等人在台阶上排开 ;左边那个叫老六,右边那个叫潘强;老六头上太阳穴处,不知何故贴了十字形白膏药,茂源长头发,皱的麻西装,脚下一双大牛皮鞋,老六和潘强留着小平头;正是盛夏,三人一律戴着黑太阳镜,一副黑帮打手的作派。摆足了派头,大摇大摆地挤上了公共汽车。
活儿有两种;一是种给坦克部队画教学用的坦克结构图;一是种给号称画商的人画光屁股的安格尔。部队派了一辆军用大卡车,接到了驻地。此时的心情与大学三年级军训时完全不同;明知是人家有求于我们,心里总觉得怕。领导明白我们的心情,就此打住 ;反倒加倍关怀我们。
我们每日同团营领导一起用餐,质量及规格不是普通士兵所能相比;每当去厕所碰到一般士兵,总觉得内疚。生活在兵营里,除了跟领导们喝口酒,再就是到操场上玩玩双杠;其它时间只有画图,进度自然不慢。我们没有幻灯机、投影仪,甚至没有比例尺,所有描绘全凭感觉目测;画到一半,心里早腻烦了;又被这儿一颗螺丝这儿一颗帽钉搞的头晕脑涨;睁只眼闭只眼交了差。部队不比地方;领导看了,相当满意。当即付了钱。又问我们还有什么要求;茂源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试探说,想到下面实战训练的部队去打炮。政委竞当即写了信,介绍我们去黄龙尾。
茂源满脸严肃地介绍说;黄龙尾是专门军训的半岛,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法进入;所以,那儿的海里海参特别多,我们得带着麻袋去。等麻袋拿来了,茂源端详了良久,说一个不够,应再多一个。并正重其事地教我们:抓到海参,扔到岸上,千万得用最大力气使劲往地下摔,要不然,好不容易抓一麻袋海参,却都化成水,漏了。
部队派了勤务兵陪着我们;怕实战演习的部队不明情况,冷淡了我们。一路上勤务兵比我们更兴奋,比我们更渴望放几炮。一看到前线首长看信的表情,我们就知道事情不妙。首长显然强压了心头的怒火,叫自己的勤务兵安排我们住下和晚餐。第二天,陪同来的勤务兵向我们灰溜溜地道别,说是领导指挥他赶紧返回部队。
我们又混了一天;白天部队打炮的时候,我们到旁边海岸,试图摸到海参。等部队演习完了,士兵们集体下海洗澡的时候,我们也跟着跑去,还是没有海参。第二天,我们扔了麻袋,甩着手,沿着簇簇荆棘类植物点缀的丘岭土路,嘻嘻哈哈,像三个流浪汉,重回了茂源在海边的工作室。( 后来部队的同志反映,教员在讲解坦克结构时,常发现图上缺少关键的零部件,大为头疼。)
那七十多幅光屁股安格尔是个苦差事,田彬没有经过系统的写实训练,基本上是个废人;我和茂源咬着牙,一边儿填颜色一边算时间,好歹按日子把画弄完了。留给茂源,由他去最后完成这笔生意,我们回北京等他汇钱。
《田彬访谈》 (2009 年 8月4日,北京,访谈人:刘璟、陶寒辰): 杨茂源当时在大连,有一次写信说他在那边接了一笔画画的活,让我和方力钧去干,挣点钱。那是 1990 年春天,我和老方穿着拖鞋和裤衩就去了,去了之后发现是画行画,古典油画之类的,就画了几张。杨茂源当时还接了一个活,给部队画教学挂图,我们就跑到一个岛上的坦克学校,觉得在岛上挺好玩的。在岛上边玩边画了几天,一人赚了500 块钱。当时就觉得腰包里有钱了。杨茂源当时在大连师范学院美术系当老师,他的学校在海边,我们就和杨茂源在海边租了一个旧的老洋楼,每天去玩在海里游泳,所以方力钧画游泳是因为那时游泳是大家最主要的活动。


夏,协助徐冰老师至金山岭长城进行拓印长城工作。

继续素描和最初的油画作品创作。
7月,回北京,与田彬一起租用圆明园内养鸡场旁一农家院落做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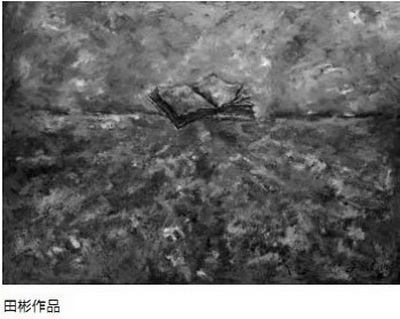
方力钧自述: 我和田彬租了一个小院;就离我们曾极其厌恶的养鸡场几米远的地方。我们背对养鸡场,其实除了随风飘来的鸡屎的味道,这是一个堪称惬意的小院,一排三间房,我们各选了东西两边;中间过去是火房,兼做饭和烧火炕,早已废弃不用,火炕也已经拆了;窗上并没有玻璃,我们用高丽纸糊了,反倒比玻璃窗更有味道。
院子里有各种条样的虫子,尤其是品种繁多的蜘蛛;每当画画厌烦或累了,就在院子里点数或色彩班澜或灰头灰脑的小虫子。
福海周边的河叉、水坑还有很多,或芦苇或荷叶地生长着许多种水里植物;水很清,能看见许多的鱼;那些鱼又招来许多水鸟;很少有游人到那地方;为数不多的几个钓鱼者的存在好像故意为了衬托那种诗意。
我早己预感到要不断地搬家,将大部分的行李都塞到于天宏宿舍的床底下,为此,老于在宿舍里没少挨骂。在院儿里捡了几块干净的砖头,将床板垫起,隔开地下潮气;一床被褥,那些没画完的画,一张国画用的毡子,一卷糊窗户时买的高丽纸。这几乎是全部家当了。
除了在湖边散步,每天涂抹些中国水墨画是最大的消遣。我身边始终保留了冯梦龙的《三言二拍》和《笑史》。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只盼天明各自飞’之类的乡村俚语正好打发困顿无奈;也在原书纸上,不断地画些对奕图,修行图之类;常常是弃了水和墨的意思,一味地在纸上找起木刻金石和简练的味道来;时间久了,倒也积攒了不少。
院子的东北角成一半圆型,对着养鸡场三角型的两层门房;院子的西南角有一废弃的屋子,被硬纸板。三层板之类连窗带门钉死了;那屋子伸入到邻居家的院子里,邻居家的院子里,堆了些有用没用的木头,也闲置着。
晚上,一只猫悲哀地在废房方向叫着;声音很像一个年轻妇人的哀泣,明知是只猫,但还是吓的一晚上不敢到院儿里起夜。
当同样的哀泣声重复到第三次的时候,隔着间房的田彬压着声音叫我 :‘老方,有人在废房子上哭。’
‘没有,是猫叫’
‘不可能是猫叫,猫不可能总是在一个地方、在一种天气里叫。你忘了?前两次也是这样天气’
‘别瞎想了,是只猫。’
‘不可能。如果是猫,咱们的狗和前院的狗会有反映。’
我把身子缩在窗户以下的位置。窗外是黑的,屋里亮着灯,中间隔了一层窗户纸。
‘老方,你看一下;到底是人还是猫 ?’田彬不依不饶地动员我。
此时,我连站起身关灯的胆量也没有;不要说探出头去观察外面了。
第二天,我和田彬急不可待地将窗户上的烂板子们扯了一地,并打开了那间废弃了的小屋 ;里面一片阴暗,几束强光透过窗缝从西边钻进来;慢慢地,看清了墙壁上原来贴了些几年前的名星招贴,那些美丽的明星甜美、职业地冲着光束里飞舞的尘埃,和层层麻麻的新的破的蜘蛛网笑着。围绕着墙根,一个个鼠洞口磨的油光发亮。
借了阳光的勇气,我们无所畏惧这个莫明其妙的房间;现在,阳光将要逝去,恐惧来,我们以更快的速度用拆烂了的纸板、三层板、塑料布将门窗堵起来,否则,我们岂不是同那忧怨的女人同处一室 ?
田彬访谈 (2009 年 8月4日,北京,访谈人:刘璟、陶寒辰):
问:您在方力钧之前就搬到那边(圆明园)去过了?
田 :我当时在那住过,北大西门外。去圆明园可能是 1989 年春夏的时候,当时有工艺美院的康木、张念,他们在圆明园里租了个小院,我们就和杨茂源、方力钧一块儿去圆明园玩,偶然就发现一个后来叫福缘门的地方,那里的房子都是空的,很大,大家就开玩笑说将来毕业到这儿来租个房子画画挺好的。方力钧当时四年级。
问:也就是说方力钧在毕业前就准备好来圆明园了?
田:对,大家就是说毕业以后在这里租一个房子,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因为看到牟森、张念他们租的一个屋子很舒服,环境也很好,就开玩笑的说要来。等到真毕业的时候,方力钧就到北大这边来,因为他女朋友也在北大。
1989 年冬天,方力钧很快在一亩园租了一个小屋子,筒子楼。我那个时候就回陕西了,杨茂源就毕业回大连了。
等到我 1990 年春天来北京的时候,方力钧已经在一亩园住了一个冬天了。来了之后我们俩又到圆明园,当时他一亩园的房子已经不租了,他就乱混到肖昱还是北大于天宏那里到处蹭住。我来了之后我就说干脆咱在圆明园租一个院子,找了一个很破的院子,里面全是荒草都没人住。农民替我们收拾收拾,100 块钱租给我们。
问 :房子有多大?
田:房子不大,一个小院三间房,两间偏房中间一个厅。那个时候没有工作室的概念,也就是可以画画可以住。方力钧在那一块就开始画一系列的水墨,就是后来画的人物,那个时候画的水墨就和他后来画的油画一样了。用高丽纸画的光头人物。
当时我们两个人只有一个铺盖卷,大概能睡觉基本上没有任何东西,只有房东给我们找的一个床板。当时就买了一些高丽纸,还有墨水,用一些很简单的工具画了第一批有光头形象的画。那是大家到处去找朋友的照片,觉得好玩的就挑出来,也因为没有材料就用水墨。这些都是根据照片画的。
一段不明不白的爱情。
方力钧自述: 人家给我介绍女朋友,住在一起,居然没有性关系,只有一个单人床,自己没有收入,追求这个女孩的男同学还不时跑来骚扰一下,表示气愤和抗议。这个女孩又特别认真,把她爸爸从老家接过来,就是要看一下男朋友。自己打肿脸充胖子,在外面借钱买烧鸡买酒,请她爸爸在这个小屋里吃一顿,老人特别好,看着我当时的那个样子什么也没说。那是 90 年亚运会期间。
她每天要到亚运会做翻译,亚运会开始的时候她要去值班,住在亚运会。我骑着自行车在美院那边瞎转悠。突然有一天,骑自行车在街上,心里一顿,发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正经事情做。就这样混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必须得把目前的这个僵局打破。结果我回去就把那些东西拿上,把门锁上,带着钥匙走了。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小屋,再也没跟这个女孩见过面。
因无力支付房租,投奔在职业高中任教的肖昱家中。
方力钧自述: 我不可能得到从容地追逐自已的梦想机会。当我再度陷入困境,肖昱收留了我。他当时分配在一三二中学教书,不宽裕,但是稳定。更幸运的是他拥有两间平房;假如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也许那根本不应称作房子,简易地用砖头砌起,四面露风,房顶露雨,也不隔音,旁边紧挨着比这两间房大的多的公共厕所。
但我还是当即搬了过来。一样的从北大租了三轮车;所不同的是,现在我只需一车一次就搬完了,不尽的迁移,令我没选择地抛下一切可以抛弃的物品,只剩一个床板、一床被褥、几件衣服、那几幅搬来搬去尚未完成的作品。同样地用两层砖头将床板垫起;同样地偷偷地为了使用电炉子改到电表;但我得到了一种保证:肖昱不可能看着我一天一斤面丸子苦撑着。
乐趣随处都有。我找了一个白色的玻璃瓶子,每发现一种未曾见到的虫子,便抓了来放进去,不几天便积了十来种。
到了冬天,买了塑料布,将窗户、门上的各处都封好了。将电表摆弄的说停就停,说走就走,说倒着走也便倒着走 ;都是老套路。
把电炉子插了电,六平米的小屋暖洋洋的;早晨爬起来,穿着衬衣就可以画画了。大概过了半个月光景,我感到有点头痛,时有时无,也并不很厉害;再过一个星期,头像要裂开样的疼;我问肖昱,他也不知所以然。两人只好大冷天里打开窗了,换换空气,不料果然好了。于是,这头疼便周期性发做,每一个星期,头感到巨疼,不得已打开窗户,好了;下个星期照旧如此。隔壁是一对青年教师。每天早晨六点多钟,一家人在我窗后的院子里洗脸涮牙;孩子上小学一年级的光景,两口子一边鼓励孩子坚强勇敢地战胜寒冷,一边教他算术或英文。
每天听到这家人亲切温暖习以为常的一切,总会令我感动和愤怒。感动是因为在如此寒冷恶劣的环境下的和谐和亲情。愤怒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冠冕堂皇,却对这世界的主体,人的需求充耳不闻;而这主体,也觉得一切均属正常。
到了夏天,地下的小虫们活跃起来,潮气也越来越大;房子不时漏水,我们只好用塑料布左一块右一块地接或堵,地下放满了各种容器,大小轻重缓急不同的水滴打在不同质地的容器上,发出一种堪称悦耳的共鸣。假如不是身居其中,也许我会有心情慢慢地听,然后细细地记述那种美妙呢。
气味也很糟糕,厕所的味道和在潮气里,和缓却从不间断地渗进来;只是我早已习惯了养鸡场的味道,没有旁人提醒,是不会自己发现的。
两块砖头垫起的床板不足以隔绝地下的潮气,我的肩膀很快出了大麻烦,有时,手臂居然没有力气举起画笔。那时候不到 30 岁,拿着铅笔画素描,举起手的时候,铅笔从手里掉下来了,想抓都抓不住了。再举胳膊举不起来,当时吓坏了,觉得自己还不到 30 岁,胳膊怎么就抬不起来了呢,心里特别害怕。还好,后来朱惠平从丹麦回来,我就拉着他去以前住的洗澡堂子拔火罐,跟师傅说肩膀有毛病。师傅给拔火罐,用蒸桑拿,经过一段时间拔火罐治疗,情况逐步好转。
《肖昱访谈》 (2009 年 8月26日,北京宋庄肖昱工作室,访谈人:刘璟、陶寒辰、杨琳琳)一个冬天我在街上碰见他,还是特兴奋的样子。他心里有事别人看不出来,他老是精神饱满的,自行车骑得倍儿快,我们俩就一边骑车一边说话。他说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学校,他说我在找房子搬家要临时周转一下,我就把钥匙给他了。他很聪明,很快就找到了地方,哈哈。然后我就住了差不多不到一年,我当时的房子是单位临建的,很小,有两间屋有一个小仓库一个小过道,他住里间我住外间,屋子都很潮,基本打得地铺。


此前后共两年左右为经济上最困难时期。众多师友予以极大帮助:和平出版社的包露滋等老师;中央美院曲桂林老师、吕胜中夫妇、陈文骥夫妇;师兄林朴;栗宪庭先生及廖雯;北京大学于天宏、黄岫如、刘建民、张薇等;清华大学陈红;师弟高惠君、同乡王华、小红,肖昱、杨茂源等等。
方力钧自述: 那时候主要是混饭,第一个是栗宪庭老师家,那时候跟栗老师来往特别频繁,栗老师家里总有年轻的艺术家。经常是进去之后一个也不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年轻人坐在那里,问你找谁?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这个家里的主人。栗老师就下面条,经常把自己吃的一点钱都没有,然后还要去管这些人,家里通常不知道住多少人,没地方住的就搭地铺住,炕上、沙发上也住,地上随便铺点东西也能住人。
第二是美院,美院混饭混的最多的是吕胜中和陈文骥两家,吕老师特别的热心肠,人特别好,师母也是,经常去吕老师家里混饭,不是吃饭的时候,师母一看我来了也下厨房给做饭,再就是陈文骥老师,还有马晓光,他们两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基本就是掐着点去混饭的,过一段时间就闪出来,或者是略微晚点进门的时候,先喊还没吃饭呢,饿了,然后人家就赶紧做饭,然后去中国画研究院,就是现在的国家画院去找师哥林朴,他也是这样一个人,比如说画画,没有画板,他就从画院里直接拿画板,给我抬着坐公共汽车送到一亩园。最早画画的那个画板就是他给我抬过来的。每一次去直接带我到朝鲜烤肉馆大吃一顿,或者去他家(他的父母都在外文局),我们就在那边吃。美院有一些师弟比较熟了,也到那里去蹭饭。经常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有我们中专的师弟高惠君、王殿森等人。
那时候也不是故意的,好象就是有这个才能,把混饭的时间安排的很好。这个节奏很像是一个探望的过程,而不像是蹭饭的过程,不太容易把别人弄的狼狈不堪,也许有的人早就看得出来,但是也不好明说,混饭就混饭吧。
《方力钧:你不是“光头泼皮”》 (彭苏采访《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1月):我从北大租了三轮车,开始了不断搬家的生活。四处蹭饭,常到北大,找于天宏他们,北大的朋友也是最多的,他们就打点饭和菜送到宿舍里给我吃。然后又去了中国画研究院,有人带着我吃烤肉,算是打牙祭吧。我那时又穷又臭,他们也没嫌过我,还有中央美院有个地下学习班,学生科的老师帮我安排课程,收入 100 元,刚好管租房。另外还有和平美术社的一帮编辑给我分活做,勉强赚点钱,反正一圈子人相处时间长了,我找他们蹭饭时,他们总以为我是想他们了,我也的确是想他们了,关于蹭饭,我挺佩服自己的。
邀请老康来圆明园工作室,老康提出热量理论。
方力钧自述: 老康的工作室被取缔,他被放出来之后有一段时间很惨。跑到东边红庙去住,平常他的性格特别好,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性格中的那种爽朗和乐观全都不见了,变得非常小心,我给他打电话,说老康你到圆明园来玩吧,然后他就清清嗓子,想半天才说:老方啊,情况是这样的,我寄宿在这个朋友家里面,他们两口子呢,有时候做饭有时候在外面吃,有时候情绪好有时候情绪不好,有时候饭量大有时候饭量小,有时候他们两个人感情挺好有时候他们俩吵架。他们饭量好,我就少吃一点,两个人做的多的时候,我就多吃一点,然后他们两个人如果在外面吃的话呢,那么可能我就没吃的。他们两个人如果要说在外面吃,心情又好,可能就叫上我一起吃。如果我去圆明园的话,你必须能够保证,就是说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得到的热量,肯定要大于我去你那个地方付出的这个热量。
这个人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不论到谁家先看垃圾筒,如果这个垃圾筒里面有还能吃的东西,他就趁你不注意时把它捡起来吃了。如果这个垃圾筒里面被清干净了,他就打开冰箱,只要是那些盘子里子还有东西,不管是干了还是时间长了,他会拿出来,说你还吃不吃?如果你说不吃了,他就吃掉。如果你要正式请他吃一顿饭,对他简直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好友李进芳因斗殴杀人被判死缓,在狱中袭击狱警后被判处死刑。
方力钧自述: 我们中专有一个师弟叫李进芳,保定人。毕业之后也经常来往,我到圆明园的时候他还写信,还到圆明园来看我。有一段时间见不着了,后来从保定听说到他的一些情况:大概是为了弟弟打抱不平,跑到人家家里去打人,结果失手,在人家家门口把那个孩子用刀捅死了。判了死缓,平时要戴着脚镣和手镣这些东西,很难再监狱里感到舒服,然后他的脾气又发了。
他趁着监狱管理人员没有防备的时候,拿着手镣子就砸在这个人的脸上,可能是把这个人的眼睛砸伤了。于是罪上加罪,被执行死刑。
同时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