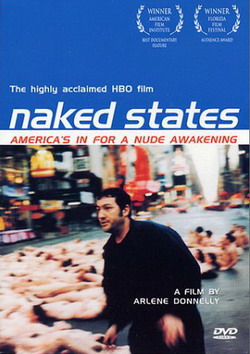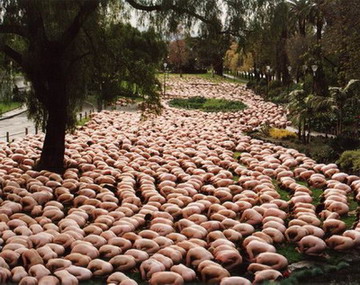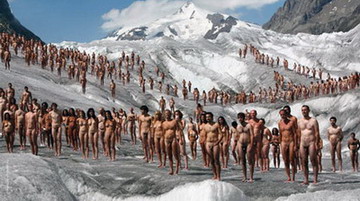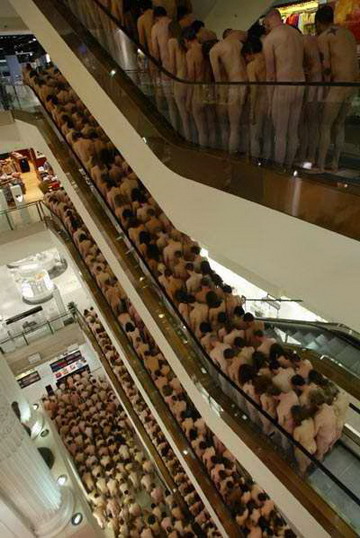Contemporary Chinese Ink Painting: Worthy of Being Loved
当代水墨:值得爱恋的所在
撰文:李若晴 Li Ruoqing
选自《画廊》2008年第二期
As an essential portion in the circl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ink painting experiment resorted to the concept of occidental contemporary 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lthough this move has helped to break the dominating status of traditional ink painting, however, as regards the domestic circumst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e should seek for new breakthrough. To be more specific, we should turn our eyes to the “everyday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on the basis of reality. The 1980s and 1990s witnessed the flourish of “ink painting innovation”, which emphasized the ink painting technique, but now it is time to rest. We should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promotion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material. Since the 1990s, Art Gallery Magazine ha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ink painting, thus, we have chosen five artists—Liu Qinghe, Liu Jinan, Wu Yi, Huang Yihan and Wei Qingji, and organized the 2008 Art Gallery Magazine Contemporary Brush Ink Nomination Exhibition and the 2nd Mayland Guanghzhou Galleries Forum. We sincerely hope that, to some extent, this exhibition is able to reflect the trend of contemporary ink painting and serve as an important motivation of its development.
编者按:水墨性话语的现代转换是当前一个广受关注的文化问题,水墨实验作为一股强劲的艺术潮流,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中的重要现象。对于当代水墨艺术的研究和收藏,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画廊》杂志通过组织学术争论与专刊介绍水墨艺术家等形式,对当代水墨艺术给予了充分关注。当前,中国当代艺术正遭遇全球化语境和随之而来的市场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以积极的立场来应对当代水墨的现状和未来。有鉴于此,《画廊》杂志特举办“2008年《画廊》杂志当代水墨提名展暨美林湖第二届广州画廊论坛:当代水墨与艺术市场”。我们希冀通过这一展览和相关论坛,能有效地促进批评家与艺术家的对话与交流,并通过这种对话与交流来推动当代水墨艺术的发展。
2001年,具有阶段性总结意义的“中国水墨实验二十年”大展在广东美术馆成功举办。这标志着中国当代水墨画坛真正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艺术格局,水墨实验正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一次大展并未能使水墨实验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更上一个台阶,反而给人一种盛极而衰的感觉。历史似乎与正在苦苦探求中国水墨艺术现代化的人们开了一个玩笑:当我们为踏上现代化之路而暗暗自喜时,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却因为高速发展与世界一体化的缘故,迅速进入后现代主义阶段。当代水墨也因此不得不陷入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尴尬与无奈,因为水墨艺术突破、重构的对象是中国传统艺术,本是一种单一性、原发性的思维,而当代艺术并不需要设定对象和命题,而且具有多重判别标准,其涉及的范畴也漫无边界。
正是在这样的迷局中,转眼七、八年过去了,和同期火得一塌糊涂的当代艺术相比,当代水墨虽然不至于“淡出鸟来”,但也可谓波澜不惊,以致有些人士要慨叹“良辰美景奈何天”。诚然,水墨作品在近几年艺术市场中的低迷状态,与外部因素委实有一定关系,但“解铃还须系铃人”,最终的出路仍然应由中国水墨艺术家寻觅。水墨实验从一开始就是以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为参照系,虽然对打破传统水墨一统天下的局面起到很大作用,但无论从国内现实出发,还是从国际大环境出发,水墨艺术都应有新的思想转换。具体而言,就是应该就现实问题有的放矢,并关注当代人群的生存状态。我想,兴起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强调水墨技术突破的那一类水墨创新,是时候结束其历史任务了。当前更需要提倡的,是让传统的媒材发出时代的新声。这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改变。在当前多元共存与价值观念普遍混乱的格局中,只有对旧有的信仰作有效的重新思考,才有可能获得思想上的根本转型,也才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艺术风格。仅仅靠在图式上的零敲碎打、搞点小变化,是不可能有太大突破的。中西绘画史上的例子一再说明了这一点。不难想像,一种艺术样式,如果缺乏一股强大的思想精神作为底蕴,那么除了偶尔闪耀几点匠人的才智之外,终归是因缺少隽永之趣而无法打动观者的。
每逢一种运动陷于低潮时,不免有打退堂鼓的,但也有坚持下来并使之发扬光大的。虽然迄今为止,相较之师学传统的水墨画家和从事前卫艺术的艺术家而言,集结在“当代水墨”旗帜之下的艺术家人数仍然相当有限,但在过去七八年里,水墨艺术实验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与新成绩,却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参加本次展览的艺术家刘进安、黄一瀚、刘庆和、武艺、魏青吉,都亲身参与了近二十多年来水墨实验的全过程。在当前的水墨迷局中,他们是难得的清醒者,而他们的作品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墨艺术的发展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具有艺术史上典型个案研究的重要性,我敢预言,如果一百年后的人们书写当前的这一段艺术史的话,他们绝对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从拙朴与粗犷的太行山人的象征性表现到影像叠合的迷幻空间,刘进安的作品实现了寓情山林与现实表达之间的融合,在一个新的精神时空中将自然与现代社会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境域。他的作品既不完全是对于传统自然观的追思,也不是对于都市生活的直接表现,而是介于两者的临界点。这也使其在形态上往往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他摒除个体细微形貌和独自特征,以单元呈列的形式着力于描绘都市人群的整体架构,从而表达出与自然内在底蕴有着某种暗合的精神寓意。可以说,刘进安作品的最大魅力在于形象的体量感与蕴涵其间的蓬勃生命力。他的作品以大山般雄浑的人物、树木的形象充满画面,云团般笔墨堆积叠加而形成的笔墨动势,将历史文化寻根的英雄主义渲染得倍显苍凉。这也是固守人类精神家园的一种方式,刘进安以这种方式展现了民族的精魂,并给久处都市藩篱中的人们以极大的震撼。应该看到,民族文化特质进入当代的可能性,在刘进安的水墨心路历程中已经得以印证。
黄一瀚的作品体现出积极的入世态度。他的作品直接关注现实以及现实对感官所产生的刺激和感召力,以此他对传统水墨作出了明确的挑战,并力图解决水墨媒材与现实社会的关联问题。在他看来,这个世界越来越人工化,越来越网络化,亦即越来越非人化、卡通化和玩具化,人在玩具中和玩具在人之中变得日益让人难以辨认,游戏与人生界限日渐模糊。这种平面化、缺乏精神维度的生活并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退化,相反,它却是对上一代或上几代人过于沉重的政治精神负载的一种解放。有理由相信,这一代人是最少束缚,最具潜力的一代。但是,如果完全脱离了理想主义情怀以及终极关怀意识这些人类原本赖以延存的精神支柱,人类世界是否预示着某些危机?黄一瀚对这些问题都有过深入的思考,但他的作品却只是将这种现象以触目惊心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他的作品绝不仅仅限于一种艺术媒材或类别,他最执着于表达的是对当下世界的一个系统看法和一种明确观念。
在刘庆和的水墨图式中,水墨的淋漓渗化营造出具有个性张力的空间意蕴和结构意蕴。在没有割舍与传统笔墨范式的联系的前提下,他化解了传统的笔墨范式,从中寻找出与当下体验契合的因素。在色墨情绪性发挥和人物形体结构保持相对严谨的均衡之中,作品的人物形象得以浮现并与背景环境相得益彰,从而也使得古典式的感伤情愫有效地介入到现实生活当中,渲染出一幅幅人类“现代性”精神失语的生存图景。画中寂寥无奈的人物形象与阴云密布的空间结构,既可以视为都市人群抑郁、焦灼的个体体验,也可以视为一个时代寓言般的启示。刘庆和以一种不加修饰也不加评说的视角自然呈现身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情态,但又不是那种隐逸者冷眼旁观的态度。积极的入世情怀、现实形象与心理形象相结合的方式,使他摒除了水墨人物画所常见的要么淡出当下体验、孤芳自赏,要么肤浅地图解生活场景作脸谱式演说的弊病,从而为水墨人物进入当代提供了有资可鉴的案例。
发展到现在被称作“现代逸品”的水墨作品,武艺显然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从他早期笔墨极度奔放、浓烈,勾皴点染不拘成法,情感肆意宣泄,内省阴郁强烈的新笔墨趣味图式到中期抛弃笔墨程式,以黑灰交织的调子建造的版画效果语言进入到近期重申笔墨趣味,以灰色、亚光的墨色加上散淡率意的笔法,心性极其平和自然地构筑出一个具有解构意味的精神“栖逸”的图景。在无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对“现代性”的质疑,一类水墨艺术家表现出对自然的依恋情感,追忆清风明月,寻觅鸟语花香,以较多延续传统文脉的方式体现对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神与人性的索源。然而,一个艺术家几乎无法拒绝时代强加给他的文化情绪和艺术态度,并且也只有直面这种现实场景才有可能探求到向前拓进的有效途径。武艺的艺术态度并不是如古旧文人般逃逸到独自的狭小圈子中去,而是在平和地关注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保持着一种适当的距离。
魏青吉的作品淡化或模糊了当代与传统的矛盾性,他转向对个体内心世界的探求和对当下生存状态的体验。作为70年代出生的青年艺术家,魏青吉的作品展现了一种开放、宽广的文化视野。他在水墨作品中,轻松自如地运用一些非水墨工具和材料来诉说个体生命和生活体验。就水墨话语空间的开放性和无边性而言,他无疑是走得较远的一名艺术家。他近来的创作接近于“标示符号”,他想用简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当然这种思考是双关而有趣的。各种图像符号,经过魏青吉富有创造性的揉和、改造和重建,使得观者在目睹熟悉的材料被重新组合和编织之时,既体会到具有特殊背景知识的阅读愉悦,又有一种新鲜感。魏青吉作品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让观者会心一笑之余,唤起对于日常生活的思考和记忆。写实与抽象两种风格从容地共存一体,朴实稚拙与曼拂轻纱构成如梦如幻的凝望关系,无法挥去的情趣交缠着无限幻想与写意的可能。那种瞬间飞逝的惊艳之美,仿佛可以触摸也可以对话。
我们所爱恋的水墨,不是故纸与碑刻,不是宣言与画符,而是将现实生活与情感体验,以丰富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动人气息。现实体验的某个瞬间,某种无法诉诸语言的情愫,才是水墨值得爱恋的所在。我们有理由相信,水墨性话语作为当下感受的载体之一,完全具有容纳当下经验和拓宽视野的文化功能。当前,中国当代艺术正遭遇全球化语境和随之而来的市场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以积极的立场来应对水墨实验的现状和未来。我们也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去鼓励批评家与艺术家的对话与交流,并通过这种对话与交流来推动当代水墨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