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三月巴塞尔香港艺术展、春季以来从香港到纽约一系列春拍、以及五六月开幕的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雕塑计划—明斯特、巴塞尔艺术展等密集的全球艺术循环之后,《艺术新闻/中文版》启动了“提问2017”的系列讨论。在欧美政治社会与经济变局对艺术世界的影响不断加深、全球艺术网络亦在继续延伸、数字沟通让时间差几近消失、中国当代艺术的“有效性”遭受新质疑的现在,我们将采访多位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的亲历者,让他们在身处的变化中,说出自己的看法、问题与观察。今天,接受我们“提问”的是香港M+视觉文化博物馆高级策展人皮力。
采访、撰文/武漠
2017年是皮力赴港工作的第5个年头,5年中,除去机构策展人身份所带来的新任务,香港与内地的距离感、持续性的阅读和写作也为更清晰的思想变化提供了可能性。在他看来,2016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并不是断裂性的,而在这之后,艺术界还能为社会提供些什么?皮力强烈推荐他最近正在阅读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书评集《在鲸腹中》,并在访谈中多次提到这本书给他带来的最大启发:“要学会偶尔转过身去,而这往往需要更大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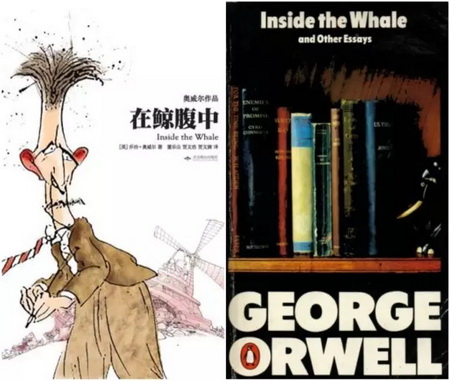
▲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书评集《在鲸腹中》中英文版
2016年以后,知识界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过去三十年间,我们没有共享基本的学术规范,没有共享基本的对历史的看法和描述,没有共享基本的人的信条,这些因素导致了我们的批评失效:赞美听起来像奉承,批判听起来像人身攻击——因为我们不分享最基本的共识。”
在2012年赴任香港 M+ 视觉文化博物馆高级策展人以前,皮力在中国当代艺术界的身份始终是多元的——策展人、艺评家、艺术教育者、画廊人,他曾笑言“艺术界能做的工作几乎都做过了”。

▲ 2005年,皮力与 Waling Boer 合作建立非营利 U 空间,图为邱黯雄在 U 空间的展览
中国当代艺术崛起的最初阶段,行业各环节的缺失决定了无论个人抑或机构,都很难不肩负起多重责任。2005年,皮力与同是策展人出身的 Waling Boers 共同创办了非营利机构 U 空间(Universal Studios-Beijing),利用这一最早入驻北京草场地艺术区的空间,两位策展人帮助年轻艺术家们实现并展示了多个媒介新颖、观念出位的实验性项目。
在当时,非营利艺术空间的定义尚然模糊,前景也不甚明朗,如何在这种环境中自给自足,某种程度上是比全盘依靠国外基金会支持、整日埋首于文书申请更富挑战性的工作——这是 U 空间最终于2007年转型为商业性画廊博而励(Boers-Li)的因由,但它依然尝试着为学术理想和艺术实验保留一席之地,这一目标不但在物理上体现于博而励在2010年迁至798艺术区后划分出的1号与2号展厅,也如基因一般被诸如“Out of the Box”、“决绝——一个抽象艺术群展”这类艺术史梳理性质的展览所携带。


▲ 2011年4月在博而励画廊举行的“决绝——一个抽象艺术群展”现场及海报
2012年,皮力接受香港 M+ 视觉文化博物馆的任命,依照香港非营利机构的人员要求,他辞去在中央美术学院和博而励画廊的职务,画廊的股份也最终于2015年3月全部完成出售。在 M+,皮力的主要工作包括在希克藏品的基础上完善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描述与研究,2016年2月23日至4月5日,由他策划的“M+ 希克藏品: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展览在香港举行。目前他正在策划 M+ 的开幕大展等。

▲ 由皮力策展的“M+ 希克藏品: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展览现场,图片来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 香港 M+ 视觉文化博物馆高级策展人皮力
《艺术新闻/中文版》专访︱皮力
Q:谈谈你来香港五年之后思想和方法上最大的变化?
A:从思想上来说,我突然对我们此前经常提及的自由主义产生了特别大的怀疑。如果与中国的大环境保持一定距离,再来看待这件事,自由主义在中国实际上已成为了新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二者相互勾结,结果自由主义更大程度上强调私有财产的合法化,却很难在中国导向社会制度的公正、公平。私有财产受保护造就了中国城市中的广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有他们对平等、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但今天中国的很多意见是以社交媒体为平台展开的,其中中产阶级的意见不可避免地占据主流,而更底层的人是失语的。这一现状造就了中产阶级的虚妄感,社交媒体的传播力度又使得他们很容易被情绪带着走,最终一种肤浅的情绪化表演反而会掩盖具体问题的讨论。
艺术界的人总觉得自己已经跻身于中产阶级,已经处于社会的中上层,但实际上这种地位岌岌可危,制度稍有不公正就很容易使他们滑落到边缘上来——我当然不是说为底层发声应当成为艺术创作的唯一方向,但我们应当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可能因漠视而犯下的错误。
在 M+,我的身份是一个机构策展人。如此一来,我的展览观众群体不再仅限于艺术界内部,而是市民大众,这导致我之前所有的策展方法论、艺术方法论、我关注问题的视角都要相应发生变化,这是与我原来在北京做展览、做画廊最根本性的不同——之前做展览基本上是在为中产阶级精英服务,而在公立机构中,则要服务到更广泛多元的观众群体,最基本的一点:这种转变要求我在展览实际操作层面上,把所有信息处理得更简洁、清楚、明确,而不是使用圈子里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术语。

▲ 香港 M+ 视觉文化博物馆,图片来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Q:以我的了解,你对自由主义的怀疑应该不是从2016年之后才开始的。
A:在我2015年那篇《后奥运时代中国艺术的困境》当中其实已经有所体现了。2008年之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同时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在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分裂性的事件,导致精英界对国家的自信开始丧失,而在民间,民族主义的情绪则开始上升,这种情绪和2016年促成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的情绪别无二致。2016年发生的种种事件不是断裂的,在某种程度上是2008年一系列隐形因素所导致的显性结果。
这就又引出我正在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如何阐释中国当代艺术?此前我们的方法都是把中国当代艺术视作隔绝的个体,在此框架中强调它的差异性——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经验等等,都是如此。这导致我们在与西方谈论中国当代艺术时,潜意识里会使用另外一种标准去看待它。但作为机构策展人,从去年的希克藏品展,到我当前正在筹备的 M+ 开馆展,都促使我采用一种新的视角将中国当代艺术与同时代的国际艺术间那种微妙的关联呈现出来,在缺乏明显交流的表象下,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艺术是有内在同步性和关联性的。


▲ 由皮力策展的“M+ 希克藏品: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展览现场,图片来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Q:在这种同步性和关联性当中,巧合的成分是否占得更多?
A:并不是。如果你去读克里斯汀·卡里尔(Christian Caryl)写的《历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异变革及其阴影》,这种同步性被勾勒得相当明确:19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抬头是同时发生的,而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全球政治右转也是同时发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1980年代的张培力与1970年代的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黄永砯和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等艺术家,他们虽然相互隔绝,但却在创作上最终走到了同一个点,此中的同步性很有意思,这就需要并且值得我们用写作、展览、实物、作品等方式去进行研究。
这些都不是此前所谓“中国经验”能够解决的问题,而需要大量的艺术史及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这恰恰是我现在最感兴趣的问题。以前我们提到跟国际间的关系都倾向于交流,但在交流中分享彼此差异性、特殊性的同时却很容易忽略,我们实际上还面对着一些人类共同的问题,这便是产生同步性的源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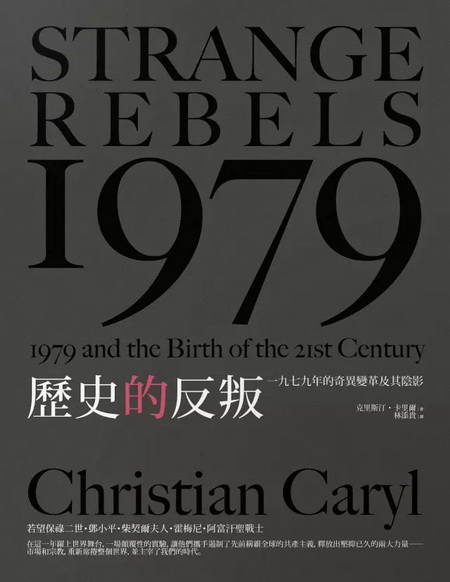
▲ 克里斯汀·卡里尔《历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异变革及其阴影》
Q: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从1990年代“去西方中心化”的讨论开始,我们总在试图改变“中心”,或者成为“中心”,但“中心”失效之后接踵而至的反而是失焦,有种浑身力气不知道打哪的感觉。
A:1980年代,当代艺术界有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主流的假想敌,我们总是想要去推翻这个假想敌,共同目标之下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很多事情;1990年代,我们开始急切地想要融入到国际当中去;到2000年以后,随着市场的崛起,我们开始觉得中国人也可以说不,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系统,市场和收藏家等等,这三个阶段其实都是共同的抗争精神和共同的乐观主义精神掩盖了我们之间的差异。
2008年,随着奥运会的举办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知识界与艺术界都出现了分裂,我们忽然发现:过去30年间,我们没有共享基本的学术规范,没有共享基本的对历史的看法和描述,没有共享基本的人的信条,这些因素导致了我们的批评失效:赞美听起来像奉承,批判听起来像人身攻击——因为我们不分享最基本的共识。阅读1980年代的艺术文献,给人最大的感觉是:共同的敌人把我们团结在一起,而此中的分裂从来未经整合。2016年以后,这将成为知识界最大的困境,我们怎样才能重建一些基础的共识?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布鲁斯·瑙曼《好男孩坏男孩》,图片来源:上海外滩美术馆

▲ 张培力《水——辞海标准版》,1991年,图片来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Q:的确这种共识的缺乏会导向不少具体层面的议题,比如你曾经多次强调过的展览文本规范和学术写作问题。
A:展览规范的问题体现在:我们不知道展览是给谁看的,明确了对象是谁,很多问题就不存在了。举个例子,在 M+ 的展览筹备过程中,策展部门和教育部门经常会反复多次讨论展览标签或展览各类文本信息的遣词造句,我们知道展览的观众是谁,因此展览的文本需要照顾到他们的知识背景和阅读习惯,其背后的支撑则是我们大量的观众研究。
中国艺术界的写作有个糟糕的积习:引文、文献综述与参考书目都极为失矩。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应当知晓谁做过这个问题的研究?他的基本观点为何?而这些认知需要融合到最终呈现的文本当中。目前的情况是大家都处于自说自话状态,你辛苦做出来的研究别人可能已经早就做过了,这就导致中国的很多知识生产最后是转化率极低甚至是无效的,它并没有成为一种公众知识。
Q:另一个层面是艺术的越来越小圈子化,除了知识生产公共化之外,在实践操作层面是否有其他打破这类封闭性格局的可能性?
A:我觉得三亚的华宇艺术论坛是一种可能性。这一代青年学者能不能开始有共享的学术经验?在共同的主题下,我们对某个术语、某种方法的内涵和外延能否达成共识?今年论坛的主题会关注社会主义、学院主义和民间这三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和转换,分开来看,这三者都不算是新问题,但我想把它们拉到同一个场域中来讨论是有必要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同行正在关注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环节的缺失,现在中国的私人美术馆已经有很多,但大部分都没有常驻策展人。从我的角度来看,私人美术馆一直还没有树立起“要为什么人”的标准,结果就难免变成自己家的大客厅。我们需要来重新思考:对象是什么?当对象确定之后,所有实践就是围绕这个对象去实现的。
比如广东时代美术馆、上海外滩美术馆,它们的定位虽有差异,但展览策略都很明确:广东时代美术馆是通过展览来梳理其所处区域的艺术实践,而外滩美术馆则倾向于做国际性的、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艺术家的小型个展,那么与展览相配套的公众教育项目、营销策略等等也会很明确。美术馆对社会的价值不仅仅是引进国际艺术家大展,而是除此之外能够令公众无法抗拒的更多东西,那就是对艺术史的梳理、公共教育项目的实施等,中国的美术馆有必要在这些方面多多留意。

▲ 2016年华宇艺术论坛现场
Q:2016年后,以你的角度来看,艺术界需要警惕什么?还可以做些什么?
A: 2016年之后,最令我忧虑的是我们曾经相信的自由主义的全线崩溃,自由主义已经无法抵御今天的保守主义,它所蕴含的普世价值既无法提供新的话语,也很难再产生对抗性。艺术理论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如今年轻艺术家的背景越来越扁平化,他们的技术和知识构成和国际水平几乎是零距离的,但我们的艺术理论却不知道该如何去把握他们的创作,对这些创作作何阐释才是有效的,这是当前艺术理论的困境,也是我下一步重点关注的工作方向。
我最近在读奥威尔的《在鲸腹中》,他谈到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中所表现出的过人之处:“(米勒)既不推动世界进程向前发展,也不企图使之逆转,然而,他绝对不漠视历史的进程。我应该说,他相信西方文明即将毁灭,他的这一信念比大多数‘革命’作家更坚定,不过他并没有感到有人召唤他去宣告。当‘罗马在燃烧’时,他却在闲逛,而不像绝大多数人那样面对熊熊烈火惊慌失措。”
我想艺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的不是去提供未来虚无缥缈的可能性,我们还是要展开对当下现实更深入的理解和研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需要对时代的政治困境和精神迷茫做出直接反应,偶尔有一点“闲逛”的精神,转过身去,保持距离,反而有可能产出更有质量的创作。
过去的一年暴露了知识界内部的分歧,但这种分歧并不可怕,当我们再次团结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共享一种经验,但有各自不同的处理方法。此外,不要孤立地看待中国的问题,中国是1979年以来整个世界政经发展脉络中的一环,而非置身事外。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的工作是强调中国艺术和国际的相关性。中国当代艺术界只有将自身视作整个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时,才有可能发展出共享的经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的争论、批评、赞美才是有意义的。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