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当代美术家》2015年第六期

▲ 弗雷德:《艺术与物性》,张晓剑、沈语冰译,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3年.
文︱张晓剑
借写作此文的机会,我想先简要回顾一下自己的翻译之路。也许,在旁人看来,一个求学者讲述自己平淡的翻译经历是岔开了论题,言不及义,但对本人而言,这样的回顾,不仅是追忆那些影响自己品性、决定人生道路的人和事,也是重新梳理自己对翻译的认识:从翻译中找到自己的道路,乃至从翻译中体味学问之道。最后部分,将着重讨论翻译与研究西方当代艺术批评的意义。
一、
1995年,当我怀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懵懂的热爱,踏入浙江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的时候,不曾想到将来有一天会从事西方现当代艺术史的翻译与研究。那个时候的大学,还没有什么基金、课题,专业的藩篱还不是那么明显,老师和学生们大多处于自由阅读的状态。几年下来,我的兴趣已经偏离入学时的意向,逐渐着迷于西方文学和西方哲学。从希腊悲剧到现代主义文学,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一个不像老庄和唐诗宋词那般亲切,但充满深刻洞见、闪耀智性光彩的异质的精神领域,让我这个来自农村的求学者好奇不已:原来我们可以那样看待人生和世界!如今回想,当时对西方文化的热情,也许源于超越偏狭视野、更完整地把握世界的内在冲动,这种冲动一直延续至今,让我时常提醒自己要保持心智的开放。
考硕士的时候,选择了我以为可以兼顾艺术体验与思辨论理的美学专业。就学第一年,正逢沈语冰老师远赴英国剑桥大学访学。从事海德格尔研究的孙周兴老师给我们上课,其中一门研讨课,他让我们翻译海德格尔的《尼采》(印象中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与强力意志”那一章),同学们参照英译本,他则用德文版给我们校正。我至今依然记得十来位同学围坐一桌,每人轮流逐句翻译的情景。一个学期下来,进展缓慢,没有读完一章;但我自认为大有收益,了解了翻译的一些常识,对句式的转换、译文的前后勾连有了初步认识。
应该是2002年,沈老师从英国回来,浙大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里传说:他做了满满数十本外文笔记,现在阅读英文的速度比中文还快。我和同学们赶到沈老师家里,一边浏览着他狭小书房里成堆的英文著作和复印件,一边听他神情激昂地讲述访学体会。我清晰地记得,沈老师当时就说:西方有太多知名艺术批评家的著作,没有进入到国内的理论视野,我们有很多事情可做。

▲ 拉里·贝尔(Larry Bell)《无题》1964.
正是这种意识,促使他耗费巨大心血写出了煌煌大作《20世纪艺术批评》。我有幸读到此书的校样,成为它的第一批读者。其“前言”信息量巨大,所提到的很多批评家名字,对于当时还热衷于西方美学、西方文艺理论的我来说,是陌生和新奇的。注释里出现的天量第一手外文文献,还有书末的参考资料,透露了他的勃勃雄心以及实现这雄心而下的苦功;其“导论:什么是现代主义”更是纵横捭阖、气势如虹,理论能力与写作才华令人惊羡,让当时的我叹为观止并产生无法望其项背的恐惧。我知道,一个新的世界,正在眼前慢慢呈展开来。

▲ 弗兰克·斯特拉的特型画 "Ctesiphon I" 1968
2004年,我硕士毕业后到温州师范学院(现温州大学)美术学院工作,自此完全转向美术史与美术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之后几年,沈老师果然投入到西方艺术批评的翻译中,2009年,他翻译的弗莱《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格林伯格《艺术与文化》出版,特别是《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其优美的文辞、详尽的注释,为困顿中的我树立了批评理论翻译的典范。也是在这一年,沈老师组织编译《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让我翻译了其中几篇文章。次年,我考入浙江大学攻读沈老师的博士,更专注于西方现当代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研究。此后三年时间里,我同沈老师合作翻译了迈克尔·弗雷德的《艺术与物性》、蒂埃利·德·迪弗的《杜尚之后的康德》(此书还有我师弟陶铮参与),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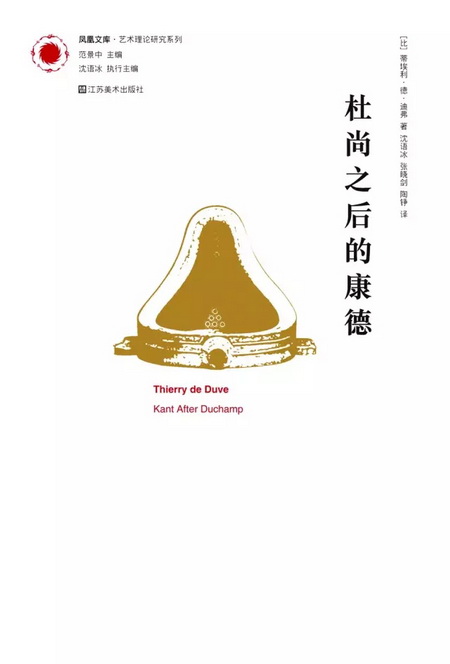
▲ 德迪弗:《杜尚之后的康德》,沈语冰、张晓剑、陶铮译,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4年.
我想,我之所以走上翻译与研究之路,完全得益于老师们作为榜样的感召。优秀的老师,不太需要自我标榜、自我描述(尽管这是一个处处“标榜”的媒体时代、眼球时代),他们以踏踏实实的翻译,以苦心孤诣的成果,向人们 “自行显示”他们个人对于知识的激情,对于学术的倾心投入和精益求精。他们的人格,也就在那种身体力行中自然呈现出来,感召着后来者。如今回想,能够遇到予以翻译启蒙的孙老师、引导我研究之路的沈老师,是我最大的幸运。
二、
回首过往,我感到自己心智的成长,有赖于中译西方文学、西方哲学、西方艺术史名著的滋养甚多。早年,对于穿梭于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译者,我总抱有一种神秘感、崇敬感,还有知恩图报的感激之情——因为他们是带来异域信息的文化使者,也是有可能丰富本土语言和本土思想的“播火者”。现在,自己也算是做了一点翻译工作,对译事的神秘感已经不复存在,但对优秀译者的崇敬则更为增加,出于“同情”的感谢也更为诚挚。
许多年前,大概是2000年底,我在《读书》上读到刘小枫教授写的《“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纪念罗念生先生逝世十周年》一文。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一剧中,已经戳瞎眼睛的俄狄浦斯称赞陪伴自己流放的女儿安提戈涅:“这女孩儿的眼睛既为她自己又为我看路。”刘教授以“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来类比罗念生先生的翻译工作。当时还是文艺青年的我,被刘教授烛幽显微的文笔深深打动,对翻译事业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优秀的译者就是替广大读者探路、看路的眼睛!
现在我明白,译者真要起到“看路”(而非误导)的作用,首先须具有过硬的目录学功夫,其次是敏锐的问题意识,再次是综合修养,有此三者,方有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判断何者重要的能力。
以前读到沈老师《20世纪艺术批评》《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美术卷》里提起的批评名著时,我总产生极大的困惑:这么多杰出的艺术批评著作,国内怎么还没有人翻译?!环顾国内图书市场,到处是通识类的美术史译著,那种低层次的重复令人心痛。客观分析,那当然是因为出版社过于考虑市场,刻意用通俗易懂的通识译著去迎合正在蓬勃兴起的艺术教育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在做了一点现当代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翻译后,我终于明白,专业的史学著作、批评著作,就算被人意识到重要性,相比于通识性的教材,也实在是太难翻译了!现当代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因为更加强调理论的运用、追求学科的交叉,所以除了要求外文和母语功夫、艺术史常识,还需要相当强的理论消化能力、宽广的知识背景。很多人避而远之也就可想而知了。
古人云,绝知此事要躬行。翻译之不易,每位译者亲身经历过后都会深有感触。我知道很多人因为体会到了翻译的烦难而放弃了翻译,改去从事更为便捷的工作——这毕竟是一个时时计算“成本-收益”的年代。不过,翻译又确实是研究西方学问的基本功,是进入西学的最起始但也最核心的途径。经由翻译,必定提高文本细读之功力,对于原作者叙述的起承转合、论证的展开逻辑都能加以最深切的体会,相当于贴着作者的思路进行了一次重演。同时,这也是磨砺耐心的工作:文中疑难的反复推敲,注释文本的一一落实,译文风格的精雕细琢,都需要耐住性子不断的推进。《艺术与物性》从2009年底开始翻译到2013年初出版,《杜尚之后的康德》的翻译从2011年延续到2014年,先是经过通读、初译、核校、查检疑难、全文通读加工的程序,再译者互校,关键文本或段落更是多次来回倒腾,交稿后又校译至少三次,每次都做改进,下的笨功夫难以计量,耗去的精力可谓巨大。真是“译无止境”!

▲ 贾德《无题》1991.
手头正好在读范景中老师为新译沃尔夫林《美术史的基本概念:后期艺术风格发展的问题》所写的“中译本札记”,其中谈到翻译容易出错、吃力不讨好的现象,读来让人心有戚戚焉。范老师还就此做了极为精彩的升华阐发,读来极为令人动容,值得大段摘录:
任何从事严肃翻译的人都知道,翻译之难,何止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简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一个翻译者踏踏实实地伏案迻写,风雨莫及,红尘不到,寂寞之心到底却不是灰心;他不仅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而且身为传递火种者,还总能获得极高的报偿,这就是,深知人必犯错,并由此而领略最优美的学习方式:通过犯错来学习,摆脱掉惧怕犯错的可怜愿望。更重要的是,这报偿还可能潜移默化他的生活,让他绝不恋生,而誓在求知;让他视学问永生无止,视人生明日将逝。
范老师将翻译中的犯错视为学习的必由之途,并将此视为直面人性弱点进而克服我们人这种“有死者”的有限性的一个阶梯。大部分译者未必明确具备这样宏伟的愿望,但他们甘于冷板凳孜孜以求,多多少少都因为体认到超越个人有限生命之上的某种价值。
译事烦难,但译中有道!
三、
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艺术运动此起彼伏,艺术批评和理论也不断更新。人们往往认为,对于时间距离过近的艺术现象、艺术批评,其价值难以确定,因此不该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但是,历史总是在时间的展开中被塑形,而且当下的艺术和批评,本身也在微妙地影响着过往的历史的形状。
T.S.艾略特在那篇广为人知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
产生一件新艺术作品,成为一个事件,以前的全部艺术作品就同时遭逢了一个新事件。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
作为趣味上的古典主义者,艾略特所说的“新的作品”显然有他自己的高标准,不过,我们也能在一种泛化的意义上将现代、当代的一些典范之作视为艾略特意义上的“新的作品”,比如杜尚的《泉》。《泉》的出现(1917年)以及它在1960年代激起的理论讨论、艺术影响,可以说改变了我们对艺术史的理解 。德·迪弗的《杜尚之后的康德》就从多个角度(美学的、艺术史的、艺术理论的等等),对《泉》做了极为深入的阐发,连管装颜料也呈现出全新的历史意义。坦率说,翻译此书,本身就是一次不断突破原有偏见的智识之旅。

▲ 杜尚:泉,斯蒂格利茨1917年摄
从哲学解释学来说,艺术作品的意义是在时间中不断生成的。时间作为伟大的主角,可以起到“过滤”和“激发”的双重作用,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
对一个文本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这不仅是指新的错误源泉不断被消除,以致真正的意义从一切混杂的东西被过滤出来,而且也指新的理解源泉不断产生,使得意想不到的意义关系展现出来。
在当代的解释处境中,过往的艺术会与我们呈现新的意义关系,其早先未曾被我们所重视的方面会凸显出来。伽达默尔这里主要偏重于作品的内容,但我们可以推广开来理解。仅举一例,到了20世纪,由于抽象艺术的出现及对其的接受,人们开始欣赏原始艺术;而在19世纪的进步主义观念中,原始艺术本来是最落后的。夏皮罗《抽象艺术的性质》(载夏皮罗《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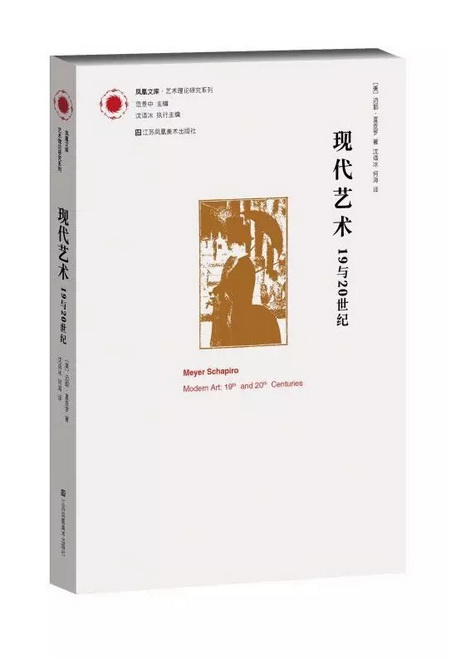
▲ 夏皮罗:《现代艺术》,沈语冰、何海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
类似的情形还可以从我的研究对象迈克尔·弗雷德那里可以看到。在1967年的《艺术与物性》这篇批评文章中,弗雷德对当时出现的极简艺术展开了分析。他敏锐地察觉到,极简艺术常常使用“场面调度”般的展览设计来激发观众的体验。在他看来,这是过分地诉诸观众,导致了“剧场性”,败坏了艺术本当具有的自主性。正是从对极简艺术的批判中,他捕捉到一个核心问题:艺术与观者之间的关系。
当1960年代后期投身法国艺术史研究后,他意识到在18世纪中后期的法国批评家狄德罗那里,就已经存在对于绘画与观者之间的理论认识。经过梳理,弗雷德提出:从法国18世纪中期的夏尔丹至19世纪60年代的马奈,具有抱负的法国绘画为保证画面的品质和说服力,通过力求塑造观者不在画前的虚构,贯彻着克服“剧场性”的独有关切。他由此写出了《专注性与剧场性:狄德罗时代的绘画与观众》、《库尔贝的现实主义》、《马奈的现代主义》,构成他所理解的“现代主义前史”三部曲。
更明确的说,弗雷德是从极简艺术那里获得启示、产生问题意识,从而追溯法国绘画历史中的“剧场性”和“反剧场性”的传统。研究者乔纳森•哈里斯(Jonathan Harris)由此认为,在弗雷德那里,艺术史是“逆向写成”的。
由此,我们会发现当代艺术、当代批评理论具有的潜力——它们可能调整我们理解艺术作品、艺术家的角度,甚至重新塑造艺术史的形状。正是鉴于此,身处当代中国的我们,有意识地翻译、研究西方当代艺术批评与理论,不仅能丰富我们看待西方艺术史的视角,也能调整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和当代)艺术史的眼光,改善我们阐释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我认为,理解西方当代艺术,理解用以说明那些艺术的批评话语,是让中国艺术和批评真正进入“当代”的基本保障。而对西方当代批评理论的翻译与研究,就是主动置身于“当代”的一个学术动作,是避免自说自话而建设性地进入当代艺术交往的开端。
作者介绍:
张晓剑,浙江大学博士,温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当代艺术批评与理论的研究。译有《艺术与物性》、《杜尚之后的康德》等,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新美术》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主持国家社科青年项目1项。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