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媒介不存在
文/W.T.J. 米切尔︱译/周诗岩
“视觉媒介”是一种口语表达方式,用来指电视、电影、摄影、绘画等。但是这非常不准确,容易误导。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检视,一切所谓的视觉媒介,都会涉及到其他感官(特别是触觉和听觉)。从感官情态的角度来看,所有媒介都是“混合媒介”。这显而易见的情况提出了两个问题:(1)为什么我们坚持谈论某些媒介,就好像它们是完全视觉化的?这仅仅是对谈论视觉宰制问题的一种速记吗?如果是的话,“宰制”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定量问题(意味着比听觉或触觉更多的视觉信息)?还是一个知觉定性的问题,一个观察者、听者、观众和听众反馈他们如何感受事物的问题?(2)我们为什么这么介意我们称之为“视觉媒介”的那些东西?为什么非要理清这种称呼上的混乱?这种混乱有何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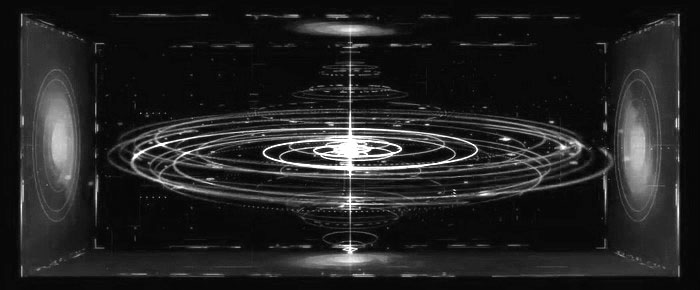
首先,让我来澄清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有种不可救药的说话习惯就好像真的存在视觉媒介,然而视觉媒介并不存在。这可能吗?当然,我的这一断言只消用一个反例就可以驳斥。所以,让我预测一下通常的质疑,这类质疑往往会列举纯粹的或专门的视觉媒介。这样,我们首先要排除整个大众媒体的舞台(电视、电影、广播),就像排除表演性的媒介(舞蹈、戏剧)。从亚里士多德对戏剧结合lexis, melos, and opsis(语词,音乐和景观)这三种秩序的观察,到巴尔特在符号学领域对“图像/音乐/文本”这种分界所做的考察,媒介的混合特征一直是核心假设。无论是从内在于这些媒介的感觉元素和符号元素来看,还是从外部混杂的受众构成来看,就这些古老和现代的媒介而言,任何纯粹性的概念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反驳说无声电影是一种“纯粹视觉的”媒介,我们只需要提醒自己一个简单的电影史事实:默片总是伴随着音乐和演讲,而且电影文本通常已经通过手写或打印的文字刻写在电影中了。字幕、幕间字幕、演讲和音乐伴奏让默片根本不可能“沉默”。
如果我们正在寻找纯视觉媒介的最佳案例,绘画就好像是显而易见的候选对象。毕竟,它是艺术史的权威认定的媒介,居于中心地位。在一段被文学化思考污染的早期历史之后,我们确实有一个关于净化的典范故事:绘画从语言、叙事、寓言、具象甚至是可命名对象的再现中解放出来,以“纯粹的光学性”[pure opticality]为特征,探索所谓的“纯绘画”。这场论争,最著名的论点由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散布,并且时常在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那里有所回响:他们坚持媒介的纯洁性和特异性,拒绝杂交的形式和混合媒介,拒绝任何像“剧场”形式这样居于“各类艺术之间”的或者修辞性的注定会让艺术沦为不真和次等审美状态的东西。这是现代主义最耳熟也最陈腐的神话之一,现在是时候让它去一边儿歇着了。事实上,即使就它最纯粹、最单一的光学效果而言,现代主义绘画也总是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所说的“画词”。这些词不是历史绘画或诗意景观或神话或宗教寓言的那些词,而是理论的、理想主义的和批判哲学的话语。这一批评话语对于理解现代主义绘画的重要作用,就像圣经或历史或经典对于理解传统叙事绘画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后者,一个站在圭多·雷尼[Guido Reni]的《临刑前一天的贝阿特丽丝·桑西》前面的人,就会像马克·吐温这类未受教的不知主题和故事的观者那样,只能断定这幅图画描绘的是一个患感冒或者快要流鼻血的年轻女孩。如果没有前者,未受教的观众会(也确实)把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画看成“除了墙纸啥也不是”。

有些人会反对说,让绘画的欣赏和理解成为可能的那种“词”并不在绘画中,不像奥维德的词存在于克罗德•洛林[Claude Lorrain]作品对它的图解中。你可能是对的,区分语言进入绘画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但这不是我写此文的目的。我目前的任务只是表明,我们习惯称之为“纯粹视觉的”绘画,例证了一种媒介的纯视觉使用根本不是纯视觉的。至于要确切地说明语言如何进入这些纯物体的感知的问题,将不得不另作探讨。
可以假设语言被绝对驱逐的绘画吗?我不否认这是现代主义绘画一种特有的欲望,仪式性地拒绝为图画贴上标题就是其症状。对观众来说,“无题”是一种神秘挑战。假设有那么一刻,观众可以观画而不诉诸言语,可以看而不诉诸(哪怕默默地内在地)默念的联想、判断和评论。那还剩下什么?嗯,显而易见剩下一件事,那就是观察到一幅画是一个手工制作的物件。这件事很重要,它将画区别于摄影媒介,在后者那里,那种机械产品的样貌通常都很显著。(我暂时撇开一个事实,即画家可以出色地仿制出光面照片那样的机械外观,而摄影师用恰当的技术也能模仿画家的绘画性表面和轮廓的模糊感。)但是,如果不承认有种非视觉的感受在其物质存在的每个细节上被编码、展现和暗示,那么绘画作为一种手工造物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呢?(罗伯特·莫里斯根据严格的时间和空间目标的程序用手沾着石墨粉末在纸上涂绘,而这些程序就充分记录在纸面下方空白处手写的文本中,他的这一《失明时刻的素描》[Blind Time Drawings]系列作品作为强有力的案例,字面上直白地反映出素描的非视觉特性)。游戏中的非视觉感受当然是指触觉,在某些绘画中(当强调“操控”、厚涂、绘画的物质性时)触觉非常突出,而在另一种绘画中(当光滑的表面和清晰透明的形式产生出足以烘托画家不可见之手工活动的神奇效果时)触觉则隐退在后台。无论哪种方式,对绘画背后的理论或者其中的故事或寓言一无所知的人,至少需要理解这是一幅画,一个手工制成的物品,理解它是手工生产的一种痕迹,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画笔或手触摸一张画布时留下的痕迹。看画即是看触摸,看艺术家的手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严格禁止触摸画布本身。
顺便说一下,这一论点并不是要把纯粹视觉性这个概念寄托在历史的垃圾箱里。而是要指出,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现代主义绘画的纯粹视觉特征是一个神话,问题的关键仍在于评估这个纯视觉特性实际发挥的历史作用,以及它为何会被提升为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概念。视觉媒介的净化作用究竟是什么?什么已被污染的形式遭到攻击?这种攻击是以什么形式的感觉卫生学和(如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说的)“可感再分配”的名义?
2.jpg)
▲Jackson Pollock
其他在艺术史上获得关注的媒介似乎不太有可能保持一种纯视觉状况。建筑,所有媒介中最不纯粹的一种,在一种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中包含了所有其他的艺术。它通常甚至不被任何集中的注意力“观看”,而是如同本雅明所指出的那样,在某种分神的状态被感知。建筑主要不是关乎看,而是关乎驻留和栖居。雕塑显然是一种触觉的艺术,谈论它的纯视觉性似乎显得多余。可事实上,它也是一种所谓的视觉媒介,因为对于盲人而言它有一种直接的可及性。摄影,这个艺术史全部媒介清单中的新品种,典型地被语言穿透——正如从巴尔特到维克多·伯金[Victor Burgin]这些理论家所展示的那样——很难想象把它称作纯粹的视觉媒介是什么意思。它的特殊作用在于乔尔·斯奈德[Joel Snyder]所说的“想象不可见的事物”——为我们展现我们用“肉眼”(即快速的身体运动、事物性的反应、普通的和日常的观看)没有或不能看到的东西,这使得它很难被视为任何直观意义上的视觉媒介。如果我们有不可思议的敏锐眼力或者关注事物的不同习惯,这种摄影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为一种将我们未看见或不可见的东西翻译成看起来像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的手段。
从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史观点看来,似乎很明显,近半个世纪已经断然破坏了任何关于纯视觉艺术的概念。装置、混合媒体、行为表演艺术、概念艺术、特定场地艺术、极简主义,以及经常被提到的对图画再现的回归,这些使得纯粹视觉性的概念成为一个在后视镜中渐渐隐退的幻景。对于今天的艺术史家来说,最安全的结论就是:纯视觉艺术作品的概念只是暂时的反常现象,是对更为持久的混合与杂交媒介传统的一次偏离。
当然,这个论点可以走更远,以至于似乎能把自己击败。我们可以反对说,除非有基本的、纯粹的、不同的媒体先行进入这种混合,否则怎么会有任何混合媒介或多媒介的产物?如果所有的媒介总已经是混合的媒介,那么混合媒介的概念就完全不重要了,因为它不会从任何纯粹要素性的情况中区分出任何特定的混合。我认为,在这里,我们必须抓住这两个极端共同构成的难题,承认一旦宣称“没有视觉媒介”,其必然的推论结果就是所有媒介都是混合媒介。也就是说,媒介和中介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各类感官、知觉和符号元素的某种混合。同样没有纯粹的听觉媒介、触觉媒介或嗅觉媒介。然而,这一结论并不会导致我们无法将一种媒介与另一种媒介区分开来。(相反)它使得对混合的更加精确的区分成为可能。如果说所有的媒介都是混合媒介,那它们并非以相同的方式混合,并非具有相同的元素比例。一种媒介,正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是一种“物质社会实践”,而不是由某些基本的物质性(绘画、石头、金属)或技艺或技术所支配的特定本质。材料和技术进入某种媒介,但同时技能、习惯、社会空间、机构和市场也进入这种媒介。因而,“媒介特异性”的概念从来都不是从一个单一的、基本的本质衍生出来的。它更像烹饪中与烹饪食谱相关的特异性(以及复合的奇异性):许多成分,按特定比例以特定顺序特定比例组合,以特定的方式搅拌在一起,并且在特定温度下以特定的时长烹饪。简言之,我们可以确定,没有“视觉媒介”,所有媒介都是混合媒介,并且这种确认不会丧失媒介特异性的概念。
关于感官和媒介,马歇尔·麦克卢汉很久以前在为不同媒介设定不同的“感觉比率”时就看到了这一点。作为一种速记,麦克卢汉乐于使用诸如“视觉”和“触觉”媒介这类术语,但是他令人意外的断言(通常被遗忘或忽略)表示:电视(通常被视为范例性的视觉媒介)实际上是一种触觉媒介:“电视图像……是一种触觉的延伸”,与印刷的语词相比,在麦克卢汉看来,电视是所有媒介中最区隔于视觉感知的。然而,麦克卢汉更重要的工作,绝对不满足于用相互区隔的、具体化的感官通道来识别特定的媒介,而是对特定媒介的各种特定混合进行评估。他可以称这些媒介为感觉器官的“延伸”,但重要的是要记住,他也把这些延伸看作“截肢”,而且不断强调被中介的(被调节的)感知所具有的动态的、互动的特征。他那著名的断言,即电力使得“感觉神经系统”的延伸(和截肢)成为可能,实际上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共通感”这一概念之扩展版本的论据,它将个体内部存在的一个协调的(或错乱的)感觉 “共通体”,向外推至为一个全球扩展的社会共同体的条件,或者说“地球村”的条件。
这样一来,媒介特异性成了一个远比诸如“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具体化的感觉标签更为复杂的问题。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植根于实践、经验、传统和技术创造中的特定感觉比率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注意,媒介不只是感官的延伸,以及感官比率的校准。它们也是象征或者符号的操作者,是意指作用的复合体。如果从符号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媒介,使用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基本的三元区分,即图标[icon]、索引[index]和象征[symbol](亦即由相似性构成的符号,由因果关系或者“既有关联”构成的符号,以及由某种规则所控制的习俗符号),我们也会发现不存在处于某种“纯粹状态”中的符号。没有纯粹的图标、索引或象征。每一个图标或图像,在我们为之命名的时候,每一索引成分,在我们询问它是如何被制造的时候,都具有了一个象征的维度。而每一个象征性的表达,就拼音字母中的单个字母而言,都必须与同一个字母的其他所有写法足够相似,以便具有可重复性,成为一个可重复使用的代码。就此而言,象征符号有赖于图标符号。麦克卢汉的作为 “感官比率”的媒介概念,需要用一个“符号比率”的概念来补充,意即各种意指-作用的特定的混合,这两方面最终使得媒介成为其所是。电影,由此,不仅关乎景象和声音的比率,而且关乎图像和语词的比率,以及其他诸如语音、乐音和噪音等可区分的参数之间的比率。
1.jpg)
▲阿比·瓦尔堡在佛罗伦萨的工作室,1898
所谓“没有视觉媒介”的断言实际上不过是一场开局,以便据此寻求一种新的媒介分类[media taxonomy]概念。这个断言希望抛弃“视觉”或“口头”媒介这些固化的刻板分类,然后针对媒介类型,开创一种立足于更微妙也更深刻的差异性的考察。关于这一分类学的全面考察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下面仅依序列出几点基本的发现。首先,我们需要同时在经验的和现象学的层面并根据其逻辑关系对感觉要素或符号要素做更深入的分析。敏锐的读者不会忽视已作为媒介之基本要素显现出来的两个三位一体结构:其一是黑格尔所谓的“理论性的感觉”——视觉、听觉和触觉,它们是任何感官调解过程的主要构造块;其二是皮尔士的意指-作用三元结构。无论探讨的是什么类型的感官/符号“比率”,都至少是这六个变量的复合体。
另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比率”本身的问题。感觉或符号的比率是什么意思?麦克卢汉从未真正推进过这个问题,但他似乎通过这个词已经说明了几件事。首先,存在着支配/从属关系的概念,一种数学比率中的“分子/分母”关系的切实实现。再者,一种感觉似乎在激活或导致另一种感觉,最显著的就是通感现象,但远为普遍的情况是,比如,书面语词直接吸引视觉,但立即激活听觉(在默读中),随后产生触觉上或视觉上的空间扩张的印象——或者带动其他的所谓“次级理论化的”感觉,例如味觉和嗅觉。其三,存在着一个与“比率”密切相关的被我称之为“嵌套”的现象,在“嵌套”中,一种媒介作为另一种媒介的内容从后者中显现出来(众所周知,在《电视台风云》[Network,1976]《益智游戏》[Quiz Show,1994]、《迷惑》[Bamboozled,2000]和《摇尾狗》[Wag the Dog,1998]这类电影里面,电视,被当作电影的内容)。
麦克卢汉的格言,“一种媒介的内容总是先前的某种媒介”,示意了这种嵌套现象,只不过,他不甚恰当地把这一现象限定为一个历史序列。事实上,完全有可能是新近的媒介(电视)作为先前媒介(电影)的内容出现。甚至有可能,一个纯属推测性的未来媒介,一些尚未实现的技术可能性(如远程传输或物质转移)作为先前媒介的内容出现(我认为大卫·克罗伯格的《苍蝇》是这种幻想的经典案例,但是《星际迷航》几乎每一集都出现的那个仪式性的要求“传送我,史考提”,却让这一纯粹虚构的媒介显得几乎就像步行穿过一道门那样稀松平常)。在这方面,我们的原则应该是:任何媒介都可以嵌套在另一个媒介中,这也包括一个媒介被嵌套在它自身之中——亦即我在别处以“元图像”的名义讨论过的那种自我指涉形式,这种形式对于叙事学的框取理论[theories of enframing]至关重要。
其四,有一种我称之为“编织”的现象,当一个感觉通道或符号功能与另一个感觉通道或符号功能几乎无缝地编织在一起时,“编织”现象就产生了,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电影中的声音同步技术。电影理论家们用“缝合”的概念来描述将分离的镜头拼接成看似连续的叙述的方法。任何时候当声音和景象在电影的展示中融合,“缝合”的方法就在起作用。当然,编织或缝合可以被拆开,可以将一个间隙或阻隔引入感觉/符号比率,这使我们有了第五种可能性:在平行轨道上移动的各种符号和各种感觉,它们永远不会相遇,而是被严格分离,留给读者/观察者/旁观者“越轨” [ jumping the tracks]的任务,以便主观地将其连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实验电影探索了声音和画面的不同步,而文学体裁,如图画诗[ekphrastic poetry],则在我们粗率地称之为“口头”媒介的形态中激发了视觉艺术。艺格赋词[Ekphrasis]是视觉表征的口头表达——通常是对视觉艺术作品进行诗意描述(荷马对阿喀琉斯的盾牌的描述是典范的例子)。然而,艺格赋词的关键在于,除非通过语言媒介,否则“其他”媒介,视觉的、书写的或塑性的物体,从来都不会变得可见或者具体。我们可以把艺格赋词称作一种没有接触或缝合的嵌套形式,这是一种在两个严格分离的感觉轨道和符号轨道之间保持距离的行动,一个需要在读者的头脑中完成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共通感[sensus communis]而言,诗歌仍然是最微妙、最灵活的重要媒介,不管有多少叫人惊奇的多媒体创作被设计出来攻击我们的集体感知。
没有视觉媒介,应该把这个短语从我们的词汇中撤销,或者对它彻底重新定义。如果对此还有一丝疑问,那就让我再扼要地谈一谈非中介的视觉本身,即眼力这种“纯视觉”领域及其对周遭世界的观看。如果视觉本身不是一种视觉媒介呢?如果,像贡布里希很久以前所说的那样,“天真之眼”,这一纯粹的未经训导的光学器官,实际上是瞎的呢。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懒惰的思想,而是一种在如此分析视觉过程时建立起的坚定的原则。古代的光学理论把视觉当作一种完全触觉性的和物质性的过程,它是一种“视觉火流“,一种在眼睛和物体之间来回流转的幻象[eidola]。众所周知,笛卡尔在用拄着两根拐杖的盲人打比方的时候,把观看类比为触摸。(见编者按下方图片)他认为,我们应该把视觉理解为触觉的一种更为精细、微妙和延展的形式,就像盲人拥有非常灵敏的拐杖,能够帮他延伸几米。伯克利主教的《视觉新理论》认为,视觉并非一个纯粹光学的过程,而是关涉某种“视觉语言”,这种语言需要协调眼睛的印象和触感的印象,以便构建连贯而稳定的视界。伯克利的理论建基于白内障手术的经验性结果,手术结果显示,恢复视力之后的盲人在很长时间里仍然无法识别物体,直到他们通过触觉对视觉印象进行了广泛的协调。这些结果已被当代神经科学所证实,最著名的案例是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对“视而不见”这整个问题的重新审视,这个对恢复视力所做的研究揭示了在长期失明之后学习如何去看是多么困难。自然的视觉本身就是眼睛和触感的一种编织和嵌套过程。
一旦进入视觉领域中的情绪、情感、和主体间遭遇的地带——即“凝视”和视觉驱力的地带——视觉的感觉比率就变得更为复杂。在这里,我们(从比如萨特那里)了解到凝视(即被看的感觉)通常不是由他者目光或任何可见物体所激发,而是由不可见的空间(空洞、黑暗的窗户)激发,甚至更强烈地由声音激发——比如让旅行者感到惊恐的嘎吱作响的甲板,或者召唤出阿尔都塞式主体的一声“嘿,你!”。拉康进一步将这个问题复杂化,他甚至否定了笛卡尔式的“线与光”的触觉性模型,取而代之以流体和溢出的模型,在其中,图画——比方说——有待被饮吸而不是看见,绘画就像羽毛的蜕落和污物的涂抹,而眼睛的主要功能是溢出眼泪,或者——在所谓“嫉羡”[Invidia]或邪恶之眼的情况下——吮吸乳母的乳房直至干涸。没有纯粹的视觉媒介,因为没有纯粹的视觉感知,没有那种可以完全脱离首要感觉器官的“眼睛”。
为什么这一切这么重要?为什么要对“视觉媒介”这样一个尽管不准确却似乎能指出世界上某种通行的事物类别的表达方式吹毛求疵呢?这难道不像有人反对把面包、蛋糕和饼干都放在“烘培食品”的标签下吗?实际上,不,这更像是反对仅仅因为它们碰巧都被放进了烤箱里,就把面包、蛋糕、鸡肉、乳蛋饼和豆焖肉归入“烘焙食品”的分类中。“视觉媒体”这个短语的问题在于,它给人一种错觉,就好像有了把某类事物挑选成“你可以放入烤箱的东西”那样的一致性。写作、印刷、绘画、手势、眨眼、点头,还有连环漫画都成了“视觉媒介”,这几乎等于什么也没说。所以我的建议是把这个短语暂时放入引号内,用“所谓的”打头,以便对其进行重新的考察。事实上,这正是我认为视觉文化这一新兴领域在其最佳时刻的全部任务。视觉文化是一个拒绝将“视觉”视为理所当然的研究领域,它坚持对视觉过程进行问题化、理论化、批判和历史化。它可不只是把一个未经审查的“视觉”概念拴上一个稍微更具反思性的文化概念——亦即作为文化研究之“景观”翅膀的视觉文化。视觉文化更为重要的特征在于,这类议题需要抵制各种纯粹的文化主义解释,并且对这些抵制做一番考察,探究视觉之自然的性质——光学、视觉技术的复杂性、观看行为的硬件和软件。
不久前,汤姆·克罗[Tom Crow]以牺牲视觉文化为代价,他建议把视觉文化和艺术史之间的关系,看作诸如“新世纪”治愈系、“心理研究”或“精神文化”这些流行风尚和哲学之间的关系。这不仅看起来有点刻薄,而且还夸大了像艺术史这样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的谱系,将它与哲学的古代世系进行比较。不过克罗的评论如果只是想警告视觉文化,让它不要沦为一个赶时髦的伪科学,甚至更糟,沦为一个配有信笺、办公室和秘书的世故的官僚化学院科系,那他的话可能还是有所助益的。幸运的是,我们身边有足够多纪律严明的人(我想到了米克·巴尔[Mieke Bal]、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和吉姆·埃尔金斯[Jim Elkins]),他们致力于让事情变得没那么容易,好让我们有望不落入和占星术或炼金术等同的智力水平。
对“视觉媒介”这一概念的突破,无疑是一种对我们自己更加严苛的方式。它带来两个积极的益处。如我已经指出的,它在感官和符号比率的基础上开启了一种更微妙的媒介分类学。但最具奠基性意义的是,它把“视觉”置于分析的焦点,而不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基础概念。除此之外,它鼓励我们去追问:“视觉”为何以及如何作为一个被物化的概念变得如此强大?从马丁·杰伊[Martin Jay]的“低垂之眼”[down-cast eyes],追溯到德波的“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福柯的“视界政体”[scopic regimes]、维利里奥的“监视”[surveillance],和鲍德里亚的“拟像”[ simulacra], “视觉”如何获得它作为“至高”感觉的地位?以及它如何获得另一种同等重要的作用——作为万能的替罪羊?像所有的物恋对象一样,眼睛和凝视都同时被过高和过低的估价了,也都同时遭遇偶像化和妖魔化。视觉文化,就其最大贡献而言,提供了一条超越这些“视觉战争”的道路,将我们引向更具生产力的批判空间,在其中,我们将研究视觉与其他感觉之间复杂的编织和嵌套关系,将艺术的历史重新开放给广阔的图像和视觉实践领域——此即瓦尔堡式的艺术史工作所预见的景象。由此,对于冒犯性的眼睛,我们能够找到比单纯挑剔它更值得做的事情。正因为没有视觉媒介,我们才需要视觉文化的概念。
文章来源:译自 W.T.J. Mitchell, “There Are No Visual Media”,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4, no.2(2005):257-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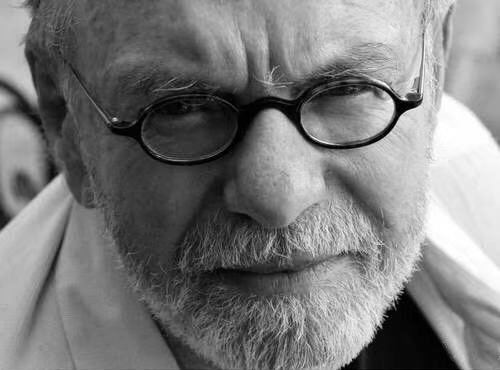
W.J.T.米切尔(W.J.T.Mitchell)出生于1942年,本科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1968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博士学位,此后十年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英语系。自1977年起,米切尔教授在芝加哥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与艺术史系任教至今。作为当代西方著名学者、艺术批评家和理论家,米切尔教授的研究领域为18世纪至今的文学、视觉艺术、媒介历史与理论,尤其致力于探索文化与图像学中视觉表征和语言再现之间的关系。1992年发表于《艺术论坛》的《图像转向》(The Pictorial Turn)一文中,米切尔肯定了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归纳的“语言学转向”的重要性,并前瞻性地指出,我们需要某种与其相类似的“图像转向”,可谓是英美学界最早提出应以图像导向的方式推进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之一。在随后出版的《图像理论》(Picture Theory)(1994)一书中,米切尔对此予以了详细论述,也正是在这本专著中,米切尔阐释了著名的“元绘画”(metapictures)理论。与1986年出版的专著《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 )和2005年出版的文集《图像需要什么?》(What Do Pictures Want?)一起,它们共同构筑了米切尔图像理论与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本文译自2005年米切尔于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发表的There Are No Visual Media,当技术的发展赋予我们身边的媒介以更多的可观可闻可感,我们应该意识到身边的视觉媒介(电视、电影、摄影、绘画等)更多的综合感知,而这种意识究竟是一次肇始,还是一次回归呢?这些媒介是如何共存的呢,是内部弥合而外部独立的吗?当我们期望获得一种解释,我们是否已经在为此预定了一项元假设呢?声光电热力到底是在逐渐入侵曾经所谓的纯粹视觉性,还是此乃一场旷日持久的混合与杂交媒介传统的活力剧场?对于冒犯性的眼睛,单纯挑剔它似乎无济于事,因为开拓,或者说是解放的力量,早已经潜藏其中。以上是2020年6月16日校译稿。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